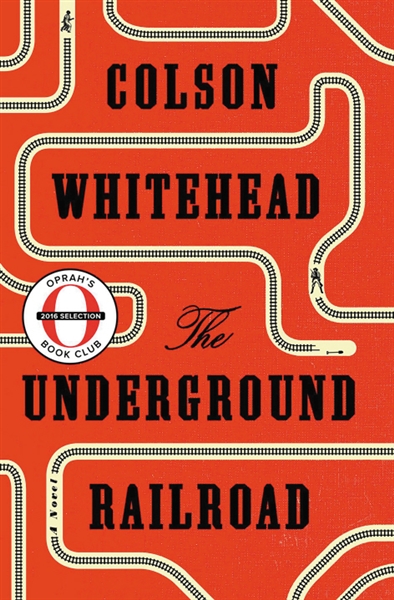
《地下铁道》
身为黑人作家,怀特黑德认为自己并非非裔的代表,也不是什么“治愈者”,他希望外界更关注自己的作品,而非肤色。他的创作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被《哈佛杂志》称为“文学变色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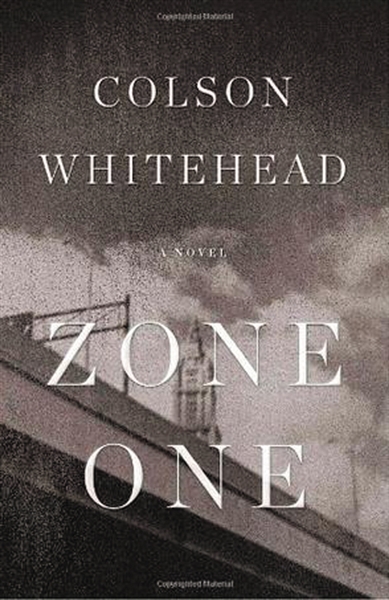
《第一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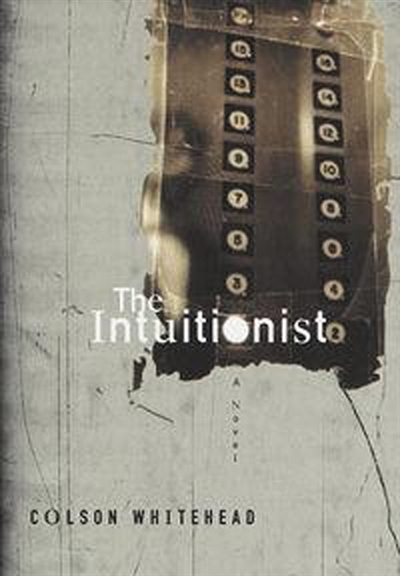
《直觉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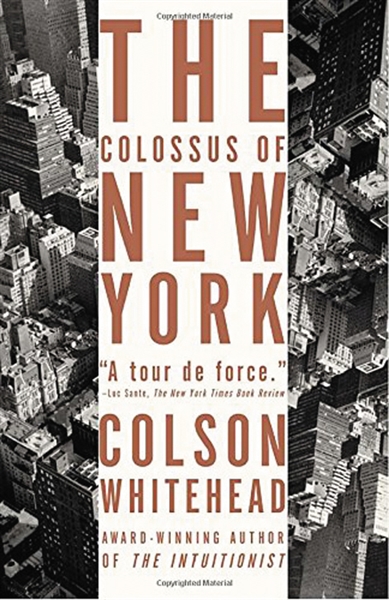
《纽约巨像》
想要探寻一个写作者的秘密,或许不只是听他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在书里写下什么。
18年间,怀特黑德创作了8部作品,其中6本虚构,2本非虚构。除了自传性质的《萨格港》之外,其余的小说都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光怪陆离,却浑然一体。从《直觉主义者》里寓意社会阶层不断向上提升的升降机,到《第一区》中暴露假面具下真实自我的末日僵尸,《地下铁道》并不是怀特黑德第一次探寻种族和人性。
也许正因为之前的触及都反响平平,这次的怀特黑德选择了正面直击。因为创造的地下空间得以把历史的时间和场景重置,以1932年至1972年间令人闻之色变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为蓝本的设置,被它在《地下铁道》中提前了将近一个世纪。
它们发生在科拉从佐治亚种植园逃出的第一站,南卡罗来纳。她本以为那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貌似进步的政府,致力于提升黑人地位的各种社会公共项目——科拉还在那里第一次乘坐了升降机,这个最早出现在《直觉主义者》里的意象,竟然被怀特黑德再次放置在科拉的逃亡故事里。“它的魔力每次都能让科拉既快活又害怕”,那是方圆数百里唯一的一部升降机,这座12层的格里芬大楼是南卡罗来纳的骄傲,背后却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目的。
通过挖坟搜集黑人尸体做研究的年轻外科医生史蒂文斯,微笑地向科拉解释,“南卡罗来纳正在开展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卫生项目,向老百姓普及新的手术方法,通过切断妇女体内的管道来阻止胎儿生成。”不仅如此,在医院的有色人病区,梅毒项目和很多研究和实验都在开展,“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弄清楚一种疾病是怎样传播的,通过哪些渠道感染的,这样我们才能着手治疗。”
这些表面高尚的白人,越是表示友好,越是令人心惊。你好像在他们身上看见了《第一区》中让怀特黑德30年来始终着迷的僵尸,“他们好像生活中的人,突然一下撕掉了假面具,露出面具下真实的自我,内心的怪物跑出来了。”
升降机、僵尸、铁道,这看似毫无关联的想象,在怀特黑德的笔下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产生了隐秘的联结。不难想象,这将是一段充满启迪的旅程,我们不妨跟随怀特黑德一起,去挖掘那些隐藏在“地下”的故事和秘密。
平静的语调来自奴隶口述
新京报:《地下铁道》共12个章节:6章讲州,从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印第安纳到北方;6章讲人,从阿贾里、里奇韦、史蒂文斯、埃塞尔、西泽到梅布尔,州和人的章节相互交叉,整本书的结构为什么这样设定?
怀特黑德:我最先开始有了设定州的想法,不同的州代表美国(在奴隶制问题上)不同的选择。那些相对较短的传记章节,我把第一章给了阿贾里(科拉的外祖母),她从西非被掳走,一次又一次被卖,横渡大西洋,是之后奴役生活的肇始。关于史蒂文斯医生的章节,因为超出了科拉的经验,她并不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所以我需要一些篇幅给史蒂文斯医生,这样可以详细说明他们在黑人身上做的那些医学实验。
关于各个州的部分,我基本保持原样。但是人物部分,我在写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考量:到底要把一章给马丁还是埃塞尔,选择写西泽还是小可爱。因为这是个很长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得决定梅布尔(科拉的母亲)这个人物到底要放在最后,还是开场,或者中间。因为被置于不同的位置,读者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
新京报:佐治亚种植园中的暴力和惩罚都十分恐怖骇人,但你选择用平静克制的语调描绘这番地狱图景,为什么?
怀特黑德:我另一本关于僵尸的书《第一区》中,所有暴力的行为都非常戏剧化。但是在这本书里,如果你读过奴隶们的口述,就会发现他们在描述那种暴力的惩罚时,把它们看成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事实。因为他们每天都看到这些,不会想着再去修饰它。那种平静的语调,是我从那些奴隶口述中得到的。他们会把所有可怕的、奸诈的、骇人的事情都用平静的方式讲出来,我的叙述就借鉴了那种声调。
唯一的信仰,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新京报:你在小说里把“地下铁道”实体化,变成了真实存在。可是,为了防止猎捕者抓到,“地下铁道”难道不应该是灵活的线路吗?如果铁轨、蒸汽机车、联络员都确有其事,那不是等着被猎捕者抓吗?
怀特黑德:把地下铁道变成真实存在的世界,这当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幻想。这是书里的现实,真实的生活中不会这么做。但人们在弗吉尼亚或者北卡罗来纳的“地下铁道”,路线确实是设定好的。这意味着,如果一个新人来,那可能得去找到那个特定的农场或河岸。所以,即便没有轨道,也仍然是有设定好的真实线路,一个人把他们送到下一个人,现实历史中的路线也不是任意的。
新京报:塑造的这些人物中,你最喜欢谁?他或她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怀特黑德:我想,还是科拉。但其实我并不这么想问题,每个人物身上都有自己有趣的面向。当然,因为科拉是主角,所以我花了最多时间陪她。我对书的最后30页其实很骄傲,觉得那是我有史以来写过的最好章节,因为我给了科拉一个很好的归宿,带她到了她可以到达的地方。
因为书写于两年前,所以你必须去想象,接近两百年前当时那个种植园里科拉的坚毅和力量。对我来说,科拉的两个场景最吸引我:一个是她捍卫自己的领土,为了拿回她的地,砸烂了布莱克的狗屋;另一个就是她想要保护切斯特,那个孩子。她以前也见过孩子被打,其他人之前也见过孩子们被打,但这一次只有她站出来了。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个时刻很重要,给了我她这个人物的特征,让我更清晰地把握住了她是谁。
新京报:你觉得是什么支撑着科拉一直逃向北方,无论一路经历了多少磨难?
怀特黑德:科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信徒,她在北卡罗来纳跟着埃赛尔学《圣经》。可是《圣经》既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又能用来谴责人对人的奴役,它是个开放的文本。
科拉的唯一信仰,就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是北方,可以是纽约,可以是加拿大。当她第一次离开,她不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然后她到了南卡罗来纳,那里看上去不错,但是显然并不是那样的。印第安纳的瓦伦丁农场看上去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实际上也危险重重。所以她并不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一个安全的地方是什么样的,现实让她一次次感到挫败。
不熟悉美国奴隶制,也能引起共鸣
新京报:《地下铁道》中,奴隶制下几乎没有人是自由的,无论是种植园主,还是猎奴者,都受制于整个制度。像科拉这样的个人,在其中要如何抗争?
怀特黑德:确实,种植园里没有人是自由的。黑人生下的孩子,不被当作婴儿,不过是另一个摘棉花的奴隶,为主人赚更多的钱;猎奴者里奇韦是自由的,但他同样也是这个制度的奴隶,他停不下来,充当秩序的化身;里奇韦的父亲是个铁匠,但是他也得打造拴奴隶用的铁链,还有把棉花运往市场的马车需要的铁轮圈,盖房子需要的钉子。
每个人都被制度牵绊。一个在报纸上写逃犯信息的记者,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你怎么抗争?通过修一条铁路,或者最终一场战争。很多人死了,制度就终结了。美国南部需要靠棉花带来钱,就是奴隶制的经济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战争,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这些。
新京报:毕竟中国读者对于“地下铁道”的历史,奴隶制和种族问题都还是有一段距离。你觉得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最吸引他们的地方会是什么?
怀特黑德:我倒没有特定地思考过中国读者的理解问题。这本书被翻译成40种语言,介绍到数十个国家,我猜想无论读者是否熟悉美国的奴隶制,都会引起共鸣。因为大部分国家都经历过被压制的历史,只是形式不同,可能是皇室和平民,也可能是贵族和仆役。无论奴隶、平民或是仆役,他们都是没有权力的。我用美国的奴隶制来讲述,但其实讲的是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