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伽马
(约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探险家。1497年7月,受葡萄牙国王派遣,率船从里斯本出发,绕好望角,经莫桑比克等地,于1498年5月到达印度。同年秋离开印度,于次年9月回到里斯本。此后又两次到达印度,并被任命为印度总督。
瓦斯科·达伽马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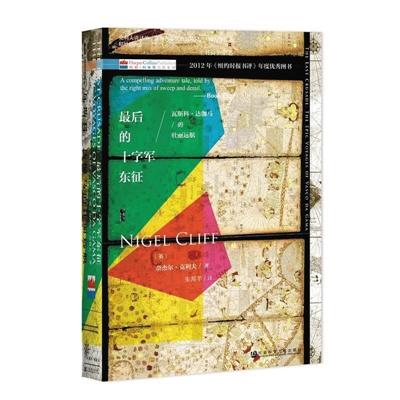
《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
作者:(英)柰杰尔·克利夫
译者:朱邦芊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8月
一部关于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航海探险的著作,揭示了达伽马航行在宗教斗争中所具有的转折点意义。
率领船队第一次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的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是“航海大发现”中与麦哲伦、哥伦布齐名的三大航海家之一。达伽马的远洋航行,使世界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相互联系的整体,促进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飞速发展。达伽马也成为近代工业化早期荷兰人和英格兰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怀揣发财与统治野心的欧洲冒险家走出国门,将征服与殖民活动带至亚非拉地区。
英国历史学家柰杰尔·克利夫,在利用新发现的达伽马日记,以及伦敦大英图书馆、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海德堡大学图书馆等欧洲多地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著作《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瓦斯科·达伽马的壮丽远航》,讲述达伽马通往东方的航行经历。
有别于诸多历史叙述中过分凸显这次航行的商业与殖民性质,克利夫将其放置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之中,呈现出中世纪波澜壮阔的十字军东征对亚欧大陆历史与文明进程的重要影响。
十字军东征
宗教热情与劫掠相结合
在正式讲述达伽马的东方航海经历之前,克利夫用大量笔墨还原了欧洲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这也是航海活动的时代背景。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发源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叙利亚草原地区,都将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圣地,都宣称上帝的终极启示是自己所独有。而且,两者都以传播为使命,力图把自己的教义传播给被它们视为异端的没有信仰之人。由此导致东方与西方长期在两河流域对峙冲突。
伊斯兰教、基督教之间为什么会如此水火不相容?答案要从二者共同的源头古犹太教中寻找。犹太教不仅是契约当事人在神的保护下彼此缔结契约,建立兄弟关系,更是在先知摩西的见证下,以色列民族与神本身建立契约缔结。为了捍卫以色列与神缔结的契约,必须发动针对其他民族的圣战。后起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信奉单一全能神方面延续了犹太教的特点,继承了犹太教关于圣战的信念。信仰层面的不兼容,使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文明在世俗力量的此起彼伏中,均以占领耶路撒冷为目的。
在克利夫看来,现代欧洲的概念不仅源于地理疆界,也不仅由于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抗击伊斯兰教入侵的共同目标,给予欧洲各民族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凝聚力,形成了现代的欧洲。除信仰方面的内在原因之外,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也别有用心地唆使世俗武装力量向东方进攻。
如果说,十字军东征是“黑暗时代”之后的欧洲骑士军团,对曾经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帝国的反戈,这一远征为何源于以比利牛斯山脉为屏障的伊比利亚半岛?作者告诉我们,在中世纪蛮族入侵的“黑暗时代”,整个欧洲坠入低谷,西班牙却充满生机。大批的学者、商人、手工业者为了躲避战乱灾害,纷纷来到这里,促进了伊比利亚半岛商贸与文化的空前繁荣。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在这里交融,共同统治着这片区域。两者在争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都将对方视为必须予以征服的敌人,建构出自身的社会团结与宗教使命感。因此,反击伊斯兰教的战斗始于伊比利亚半岛,目标直指耶路撒冷。
除宗教层面的敌对因素外,国土的狭小也使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选择了以攻为守的进取方式。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结束后,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在教宗的调停下,划定分界线,约定了对新发现殖民地的归属权。葡萄牙承认西班牙水手在西部发现的所有土地均归西班牙所有,而西班牙则承认葡萄牙在东部的陆地所有权。两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推行其信仰和统治权的激烈竞赛。
相较于西班牙,葡萄牙的国土面积狭小,国家实力有限。尽管葡萄牙国王若昂下令砍伐了很大一部分王室森林,用来制造船舰,但他不得不向西班牙、英格兰和日耳曼派遣特使,租下他们的高桅帆船。在年轻王子恩里克的带领下,葡萄牙的殖民者沿着海岸线航行,攻克了北非部分国家和地方。作者揭示出这场以传播宗教为旗帜的野蛮入侵实质。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不仅得到了教会的默许,甚至得到了教宗煞费苦心炮制的诏书,授权葡萄牙人攻击、征服和镇压任何异教徒统治的区域。
在作者看来,葡萄牙人航海的目的是以基督之名让人皈依和征服他人。宗教热情与劫掠相结合,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了一场致命的打击。
无尽深渊
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竞赛
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中世纪,贯穿欧亚大陆商贸往来的必经通道是君士坦丁堡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在穆罕穆德二世的率领下,跨越海峡,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一番烧杀抢掠之后,将这个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更名为伊斯坦布尔,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面对伊斯兰教势力在东方的突起,葡萄牙的殖民者将目光从非洲转向遥远的东方。年轻的国王曼努埃尔坚信,葡萄牙的探险事业有神的相助。这源于一种信念:葡萄牙作为一个诞生于十字军东征的国家,有义务与伊斯兰战斗到底。在此背后,东方的香料、丝绸、陶器等奢侈品令长期遭受战乱的欧洲人垂涎三尺。对他们而言,东方是一片遍地黄金,淌着奶与蜜的肥沃土地。
中世纪时期,受基督教会的影响,欧洲人认为大地是平的,海洋尽头是无底深渊,向西航行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中世纪晚期的技术与知识颠覆了这一观念,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1406年,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西方得到迅速传播。该书颠覆了中世纪基督教地理学家认为地球上绝大部分是陆地的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人关于地球的概念。冒险家们根据新的地理学知识,判断大洋彼岸东方诸国的精确方位,设计最合理的航行路线。
然而,面对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扼守住欧亚大陆的必经陆路通道,欧洲的殖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避开与伊斯兰国家的正面冲突,绕道前往东方的想法孕育而出。曼努埃尔开始物色远洋航行的合适统帅人选。在彼时,远洋航行不仅意味着生死未卜,更意味着要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一段不短的时间。这使得没有纯正皇室血统的达伽马进入葡萄牙的宫廷视野,成为此次航行的担纲者。他组建了一支忠实可靠的队伍,任务是抵达印度,争取盟友和财富,以便葡萄牙能够入侵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地带,直捣耶路撒冷。
达伽马穿越大西洋的远洋航行,意味着葡萄牙走向海外扩张之路。与哥伦布最终锒铛入狱、孤独而死的不幸遭遇不同,达伽马于1497年7月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先后完成了三次航行。历尽艰险,却成功穿越了大西洋,到达印度。1499年夏,达伽马返回了葡萄牙里斯本,得到国王曼努埃尔派遣的贵族护送,并得到世袭贵族头衔。他被任命为王室议会成员和印度海军上将,享有在印度殖民地的司法、税收等大量特权。带着国王赋予的权威,达伽马开始了第二次前往印度的航行。这一次,他获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欧洲在印度的第一个殖民地。
对达伽马而言,在印度的殖民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彻底驱逐穆斯林,使国王曼努埃尔成为耶路撒冷之王,才是具有圣战狂热信念和钢铁般意志的达伽马的目标所在。这一计划的不断付诸实施意味着时间、人力与财富的持续投入,葡萄牙在东方越陷越深。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为了维系庞大的海外商贸路线,不得不在各个交通要道屯置大量兵力与管理者,导致一笔沉重的财政支出。在作者看来,尽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都展示出伟大的神的荣耀,并对贫病苦难施以援手,但穷兵黩武的征服主义是两者共同的阴暗面。
本书前言透露了长期困扰作者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宗教战争的爆发会影响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倒放电影式的追溯,该书向我们呈现出一个被大多数历史叙述遮蔽的实质。在一个被理性主宰的现代社会中,非理性的幽暗一面并未走远。那些冠以神圣信仰之名发起的战争,通常关乎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与领袖人物的傲慢与自负,而无关信仰本身。
□胡悦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