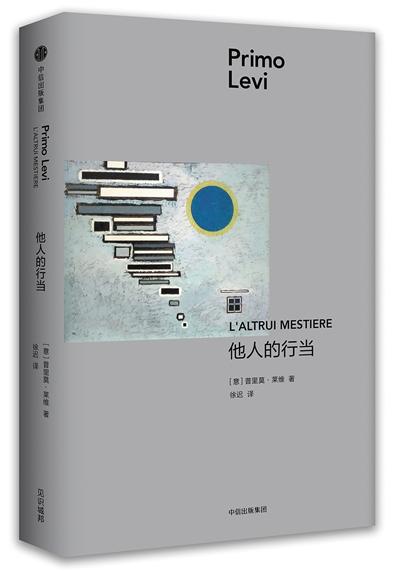
《他人的行当》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徐迟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收录了普里莫·莱维1969年至1985年所写的43篇散文。莱维审视了自己的行当——作家与化学家,更关注“他人的行当”。

《扳手》
作者:(意)普里莫·莱维
译者:杨晓琼
版本: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
聚焦普通人生命经验的小说集,写工人、童年、无关大屠杀的事。
普里莫·莱维是我近年阅读的一个兴奋点,对于他的任何作品我都抱有一种好奇和期待,当我翻开《他人的行当》亦是如此。《他人的行当》在莱维的著作中非常特殊,大概是他唯一完整丢开集中营梦魇的作品。我们知道,当莱维在纳粹集中营凭借化学家的身份侥幸逃生,历尽艰险回到都灵家中,当他重新拿起笔,一种为纳粹暴行死难者代言的见证者心态,就一直主导和左右着莱维的全部创作生涯。
当他写下《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若非此时,何时?》和《元素周期表》等一系列有关纳粹暴行的作品之后,也许有一丝厌倦了,也许他在想把纳粹、暴行、野蛮什么的统统抛诸脑后,写点别的,只要不去触及纳粹或者苦难。结果我们发现,纳粹集中营的确不是世界的全部,绕满电网的高墙只是圈起了一个人类的噩梦,在它之外之上仍然有广袤的世界,而且更明亮更通透,也许也更美好,尽管某种严酷的法则依然隐藏其中。
正如他在《他人的行当》序言末尾所点明的:“我希望我已经将这个我一直以来抱持的观念传达给读者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斥着问题和危险,但绝非是无趣的。”
对他人行当的“侵犯”
在《他人的行当》里,莱维甩开纳粹集中营对他旺盛想象力的禁锢,任凭自己的好奇心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神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尽情遨游:有时是一只蝴蝶引发的联想(《蝴蝶》),有时是对甲虫的探究(《甲虫》),有时是对一只空瓶子的胡思乱想(《一瓶阳光》),有时是对在《海狸六号》深海探测船上所待的三十小时的描述(《卡斯特罗六号上的三十小时》),有时是对故乡人行道上铺路石的一种“科学”的分析。
在另一些文章里,回忆突然握住了莱维的笔,让他对自己几乎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除了数次并非自愿的暂离之外)作一番深情的打量,“我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就如同我栖息在我的皮肤里。虽然我见过更美丽、更丰腴、更强健、更如同画卷的躯体,但要是与之交换的话,我总觉得是不自然的。”(《我的房子》);或者对外祖父在老罗马街上的一家布料店展开细致的描摹,“那是一间狭长而阴森、只有一扇窗的屋子,它垂直于街道,甚至比街面还低一些”(《外祖父的店》)。
尽管莱维打定主意,在这本书里要远离集中营,甚至要弱化自己的作家身份——“我的化学家生涯,如此悠长的化学家生涯,让我很难把我自己看作一个真正舞文弄墨的人。”但是在经过几十年漫长的写作生涯之后,莱维已经很难轻易抹去自己身上的作家标签,在书中直接论及小说和写作的文章就有六七篇之多。
这些文章多是经验之谈,文论通常的生硬辨析让位给一种灵活的叙述和贴切的比喻,《书写小说》是我较喜欢的一篇,在文中,莱维比较了非虚构写作和小说创作的区别,如果非虚构写作是“随着一条线索挖掘近期或是远期的记忆,把样本一一安排好,为其编目,然后举起一台差不多像是思维相机的东西开始照相”,那么小说创作则完全不同,“你不再脚踏实地,而是满载着开拓者的情绪——恐惧和热情,驾着一台以帆布、细绳和胶合板搭成的双翼飞机在空中翱翔。再好些的,则坐在被切断系泊线的热气球中。”
《他人的行当》总的来说是一部天马行空的作品,用莱维的话说,就是“对他人行当的侵犯,是在私人猎区中的偷猎,是对动物学、天文学和语言学无边际的疆土的突袭”。也就是说,哪怕在这些随笔里,莱维也享受了一回坐在被切断系泊线的热气球上自由翱翔的感觉。莱维细致理性的行文,给这些文章披上了一层“科普文章”的外衣,但是莱维并未系统学习过这些学科,他的用意也不在于给某些高深的科学知识做普及工作,而是试图弭平科学和文学世界之间非常荒谬的罅隙,“若是有宽阔眼界的话,它们之间偶尔是存在共同的魅力的”。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则是一种叙述的愉悦,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叙述的愉悦也就是魅力本身,也就是叙述本身的目的,在更高的层次上,它们合二为一。
句子溢出无法抑制的快感
莱维在《他人的行当》中有意去书写对一般小说家而言非常冷门或者非常微小的题材,固然是因为他强烈的好奇心的驱使,但也隐藏着某种作为作家的自信——瞧,任何貌似不可能的题材,我都可以把它处理成有魅力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判断,这本在各个学科领域四处出击的作品,主要不是科普读物,而是一部有着内在野心的文学随笔集。这本书的主要魅力来自于莱维细致入微的描述、形象的比喻,以及句子本身溢出的无法抑制的快感。
在《蝴蝶》一文中,莱维这样描写蝴蝶:“在它们短暂的生命之中,它们改变着自己的外形,呈现出比鲤鱼和野兔丰富得多的身姿;它们奔跑、飞翔、跳跃、游泳,几乎已经能够适应任何一个星球上的环境。在它们那仅有一毫米的大脑里,储藏着职工、陶艺家、投毒犯、诱捕者和乳母的技艺。”
在《看不见的世界》一文中,他这样描写苍蝇:“它的翅膀仿佛无数血管在透明的、泛出虹彩的薄膜中形成的精细迷宫。它的眼睛好像奇迹般规整的深红花窗。它的脚宛如脚爪的兵工厂,不仅长着刚毛,足垫还包含了滑行软垫、泡沫状软垫和钉状软垫。”
蝴蝶和苍蝇,这两种在日常生活中分别代表着美丽和丑陋的物种,在莱维的笔下都变得生动无比,就文字的感觉而言,这是两段精彩的描述,甚至后者更胜一筹。因此文学或者说文字的美学和描写对象物的美丑不是一回事,对一位美人的描述很可能是臃肿呆板的,对恶心之物的描写反而有可能是精彩无比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观念的高下,更重要的是显出作家真正的才华之所在。莱维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他人的行当》中,精彩的文字的舞蹈比比皆是,撇开题材、主题和观念,这些就足以构成一名一流作家的基本质地。我们看到的仿佛是一位巧匠拿着简单的针线,编织出任何想要的图画,它们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引人赞叹。
《他人的行当》尽管写得精致、妙趣横生,但是,和我之前看过的他的另三部作品——《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元素周期表》和《这是不是个人》——相比,还是相对较弱。在我看来,问题正是出在莱维写作此书时极力避开的集中营主题,这使整本《他人的行当》失去了一个重要支点,并不是说一流文学就必须要写集中营题材,而是至少要有一个类似的重要题材。
题材的重要性永远不可小觑
美国诗人杰克·吉伯特在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谈一九六五年美国诗坛》里明确写道:“假使诗要伟大,内容必须是重要的。”这句话堪称至理名言,如今不少作家抱持“小中见大”的理念,心安理得地书写个人化的题材,并试图从中找到通向永恒的捷径,但通向永恒的路一定有一道窄门在把守,通过的人一定是少数。
也就是说,题材的重要性永远不可小觑。莱维的文笔有一种天才般的轻逸和灵动,但只有当它和纳粹集中营题材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轻逸才是一种完全的优点,它和题材的沉重相互刺激相得益彰,把彼此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当莱维在《他人的行当》中主动规避了集中营题材,他文笔的轻逸也就失去了牢固的附着物,真的变得有点轻飘起来。当幽默中少了一点生活的苦涩,变成纯粹的笑话时,读者至少笑得没那么会心了。
话说回来,莱维有本钱这么挥霍一下——他已经写了那么多重要作品,偶尔轻松一下不会降低他作为大作家的成色,只是《他人的行当》并不像有些评论说的那样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构成对比——“一个是最苦痛的莱维,一个是最快乐的莱维”。
《他人的行当》中有关文学的几篇文章,莱维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也多写得摇曳生姿,颇为好看。但从中我们亦能看到莱维的某种不足,就是他的阅读量并不大,当然我马上要补充说,一流的小说家和诗人,的确不需要很大的阅读量作支撑——他只要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经验,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天才地运用文字的能力,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小说家或者一流的诗人。但是当他试图涉足评论,甚至像莱维那样更多地以自身的经验和精彩的比喻和描述涉足评论,较少的阅读量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和障碍。
《隐晦的作品》是《他人的行当》里另一个明显的软肋,此文透露出莱维对于所谓“明晰的文风”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追求:“让希望读懂他的人理解他是一个作家的本职工作。这是他的行当,写作也是一种公共服务,绝对不能让一个愿意阅读的读者失望。”这样的论断是有失偏颇的,且不说读者本身是有层次之分的,有些人看来再明晰不过的诗文,在另一些读者看来则完全有可能是晦暗不明的,而且严格说来,写作也不完全是一种公共服务。写作者为什么只能向公众说话呢?他完全可以和自己的内心或者自己秘密的对话者展开对话,同时又自然而然地获得某种公共性,在现代派作品里有大量此类作品。
作为莱维的忠实拥趸,我更愿意回到他最好的那些作品中去,也就是回到《元素周期表》《这是不是人》和《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去,莱维大作家的地位最终是由这几部最好的作品奠定的。
□凌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