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1918年12月7日生于上海,30岁时移居香港。作品有《酒徒》《对倒》《寺内》《打错了》《岛与半岛》《他有一把锋利的小刀》《模型·邮票·陶瓷》等。其中《酒徒》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与《对倒》一起曾启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出电影《2046》《花样年华》。

刘以鬯的《酒徒》和《对倒》分别启发了王家卫的电影《2046》和《花样年华》。图为两部电影中梁朝伟饰演的报社编辑周慕云。

刘以鬯的《酒徒》和《对倒》分别启发了王家卫的电影《2046》和《花样年华》。图为两部电影中梁朝伟饰演的报社编辑周慕云。

《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拍摄了《刘以鬯:1918》。图为刘以鬯在当年用的原稿纸上,亲自抄下《酒徒》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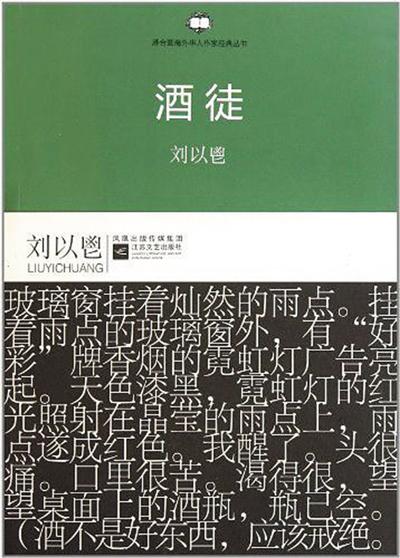
《酒徒》
作者:刘以鬯
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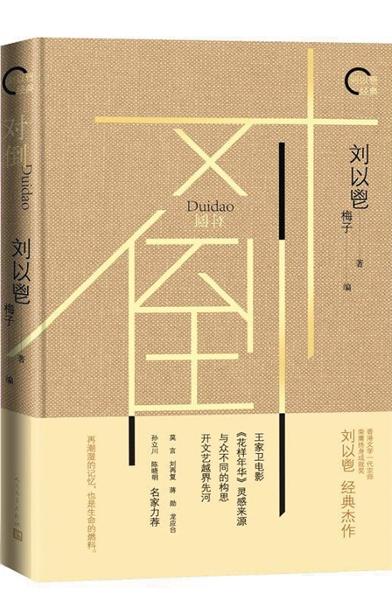
《对倒》
作者:刘以鬯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6月
文坛凋敝,前辈逐一仙游,这一次,是百岁刘以鬯。
还记得两年前,《他们在岛屿写作》在香港大学举办发布会,纪录片《1918》的主人公,98岁的刘以鬯坐在台下,他因重听发言不便,请岭南大学黄淑娴教授代为致词,台上的白先勇、洛夫(已于今年3月离世)、林文月,另外几部电影的主角,算起来都是他的后辈,他们的侃侃而谈,刘先生未必听得到,却仍以亲身莅临的方式,作为对文学的支持与致意。
刘以鬯的文字,世人最熟知是《酒徒》与《对倒》,分别启发了《2046》和《花样年华》的创作。王家卫亦以《酒徒》中的一句“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悼念宗师,在这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序言最末,他自白,“这些年来,为了生活我一直在娱乐别人,如今也想娱乐自己了”。
娱己 香港狐步舞
1963年写《酒徒》之际,刘以鬯已年逾四旬,经历了从出生地上海,迁往抗战大后方重庆,又只身南下香港,半生飘零,以写作者的创作生命来说,算不上年轻了。
用他自己的话说,《酒徒》是“写一个因处于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当现实主义已道不尽世界的光怪陆离,刘以鬯借现代小说技巧,表达对社会生活的慨叹。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写稿机器老刘抑郁不得志借酒消愁,行文中,酒醉的潜意识与酒醒的显意识穿插行进,“海是蓝色的大缸,风拂过,海水做久别重逢的寒暄”、“太多的大厦有凌乱的感觉,保守派仍偏爱小夜曲”、“生的火焰需要一把扇子,第三只眼睛曾见过剪落的发屑”……梦呓式的长句与断章,贯穿全文的“酒不是好东西”、“我喝了一口酒”、“我醉了”,推杯换盏间的自问自答,流连女人怀抱的欢愉与失落,老刘极力自救又不断沉沦,充满实验性的文字殿堂下,是良心的拷问与喷涌而出的诗意。
读《酒徒》,难免会想起上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以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手法,呈现夜夜笙歌的十里洋场,这座“地域上的天堂”里,狐步舞、爵士乐、霓虹灯的流光溢彩之下,都市人敏感复杂的内心。
受穆时英启蒙的刘以鬯,则把这场纸醉金迷的角逐游戏搬迁到香港,愈繁荣愈堕落,有过之而无不及,虚实之间,生活是苦闷的,内心是压抑的,人性是扭曲的,当金钱泯没良心,严肃文学无人问津,职业作家为稻粱谋,只能麻痹社会意识与自我认知,酒与性成为救命稻草,病态成为嘲讽。
所以,总有人给“老刘——刘以鬯——周慕云”画上一串等号,而作家的实际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举个例子,刘以鬯更偏爱的另一部作品《对倒》,出自集邮术语,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写的是一个怀缅过去的老人和一个憧憬未来的少女,两条不会交汇的生命线,在城市游走的轨迹和内心世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小说1972年在《星岛晚报》连载,因为门槛太高,读者有限,到11万字便终止,更直到90年代才有成书机会——不同于梁朝伟所饰演的、被赋予无数浪漫想象的周慕云,刘以鬯没有那些风花雪月,他只是以一支笔与时代博弈,沉痛许多,却从未消沉,是娱己,也是反省,曲高和寡亦无妨,他的战线拉得更长,也将其视作使命。
娱人 痛并快乐着
周慕云未必是刘以鬯,苏丽珍黄昏里一身旗袍去买的云吞面,倒是有迹可循。
赴港后家财散尽,刘以鬯本能地想到卖文为生,试探性地写一篇千字稿件寄出,即获10元稿费,彼时物价几何?三毫钱一碗云吞面,一篇稿费可买30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最高峰期一天写十三个专栏,洋洋逾万字,足以应付温饱,每天起身即动笔,假如写得顺利,就包车去一间间报馆送稿,然后携夫人外出食饭,便已十分快乐。
蔡澜也在文章中回忆,南下文人圈子,聚会喜欢打打小麻将,有时打到中途,报馆来电催稿,刘以鬯就叫他这个小弟弟搬来一张小桌子,拿出稿纸,等人发牌时,“就把它当成缝纫机,不断地织出文字来”。
这些挤出闲暇编织出来的文字,被刘以鬯毫不客气地称作“目的只在换取稿费的垃圾”,要知道,他一生坚守文字为业,不靠拢任何机构过活,除了是写作者,他还是副刊编辑,他采取挤之战略,见缝插针地在文字商品中铺入精心挑选的严肃文学,向读者举荐台静农、端木蕻良的作品,又积极发掘新人,也斯、西西之辈,都受过其提携。据说,他常常趁老板不注意,把年轻作家的纯文艺作品放在看相占卜的旁边,或趁老板心情好,直接放在瞩目的位置,总之,洒下传播的种子,能飘多远飘多远。
苦不苦?1985年,近退休之际,中国新闻社邀他办《香港文学》,理应卸下娱人重担的他,却欣然接受,更至主动辞掉所有报刊专栏,一办15年,留下了近200期的丰绩。
以退为进,如履薄冰,承前启后,对以文字为信仰的刘以鬯来说,想必是痛并快乐着。
晚
年
希望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回到纪录片《1918》,刘以鬯的晚年生活,日常仍保持出门散步的习惯,家楼下是商场,他每天要出巡一番,被搀扶着也好,坐着轮椅也罢,看名店橱窗,观途人风景,日日摄取新鲜,是写作者的自觉。95岁时受访,问及有何心愿,他的答案仍是“希望继续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为什么?“那是不需要鼓励的,只要喜欢,就会用各种方式去走这一条路”。
刘以鬯的这一条路,迢迢百年,娱己娱人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一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