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9月20日,利比亚班加西,被北约炸毁的卡扎菲的坦克成为儿童的玩具。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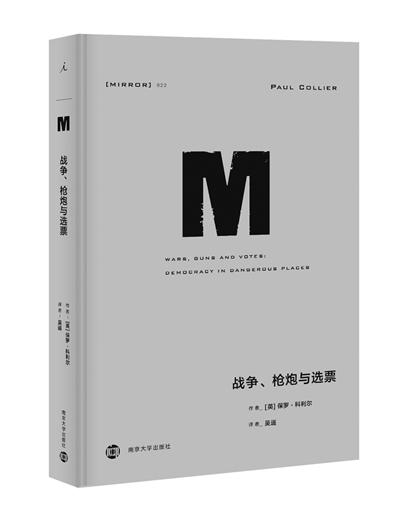
《战争、枪炮与选票》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
译者:吴遥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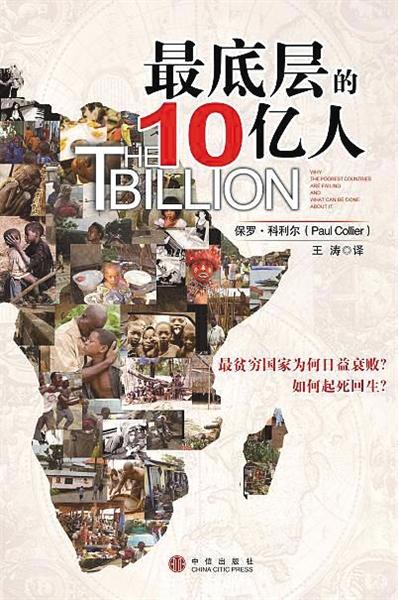
《最底层的10亿人》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
译者:王涛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08年7月
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是研究非洲问题的一流专家,他曾在《最底层的10亿人》一书中把脉非洲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非洲国家面临着四种陷阱:战乱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环绕的内陆陷阱和小国劣政的陷阱。在这本书中,科利尔提出的命题就是,为什么最底层的10亿人难以建立起稳定的国家?
这本《战争、枪炮与选票》则深化了相关思考,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科利尔通过统计、调查等方法对“非洲病”进行了诊断,很多的结论是令人震惊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的魅力所在。
重审民主与国家的关系
冷战结束之后,战争的风险下降,尤其是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基本销声匿迹,战争更多的是以内战形式进行,尤其是在中东地区、非洲内战已经变成当下国际政治面临的一大挑战。科利尔的《战争、枪炮与选票》在2010年出版,那时候中东地区的政治秩序看上去还算稳定,如果现在他重新来写此书,想必其中的案例会从非洲转向中东,后来的叙利亚战争进一步证明了科利尔的洞见。
冷战结束之后,民主化的浪潮赢来第三波,然而,民主化的推进并没有给所有发展中国家带来秩序、稳定和繁荣。民主制度并不能简单化约为选举,选举是民主实现的一种方式和手段,但如果颠倒过来,就会出问题。民主需要一套权力的制衡制度,民主是可以容忍和善待失败者的,并不是一锤子买卖,失败者可以东山再起,也是因为这种程序的存在,所以,选票可以代替子弹。另外,民主制度需要一套问责制度,选举上来的政治人物需要为公众服务,尊重选民赋予的权力和责任,有议会和媒体的监督,而下一次选举是最好的监督。
此外,关于民主与国家的关系,科利尔认为民主或者说选举并不能直接建立国家。就像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国家就是在一定疆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国家是浴火重生的,是在战火中淬炼出来的,欧洲国家是从罗马帝国崩溃转型而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所谓的“国家”(state)建立起来,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欧洲国家之间经历了三四百年的战争。
查尔斯·蒂利就认为,欧洲国家的形成遵循着战争与资本两种逻辑,战争淬炼了欧洲国家的认同感,而战争高额的支出迫使欧洲国家先后建立了公共财政制度,战争最终还是每个国家融资能力的竞争,最先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国家是荷兰,虽然没有地理优势,但是荷兰的举债成本非常低,对抗来自西班牙、法国等大国的战争压力。可以说,现代国家不仅是暴力的容器,也是资本的容器。现代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因为这一制度所内含的暴力与财富的能量,而让欧洲国家可以殖民全世界,并且将这套制度推向了全世界。
并不是民主建立了现代国家,而是现代国家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演化到了民主阶段,可以说,国家的构建与发展是民主最根本的前提。科利尔悲哀地发现,“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历史悠久,但是它们现在的国家很年轻。这些国家往往太小,无法维持安全的规模经济,力不从心地维持着国内的稳定。也因为它们建国的时间不长,很难打造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认同,不足以抗衡古老的族裔和宗教认同。所以,这些国家虽然对安全来说太小,对公共品所需的社会凝聚力来说,又显得太大。结果一定是公共品短缺。”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却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科利尔进行了量化的研究,认为人均GDP2700美元是个临界点,“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数值未必是精确的,但是代表着一个趋势,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物质基础,而选举过程无可避免地会有一种对现有财富的重新分配。最底层的10亿人并没有形成对国家的认同,相比之下,族群要比国家更靠谱,选票的分配并不是根据候选人的政绩和能力,而是其族群身份,可以说,族群认同压倒了国家认同,选举过程加剧了族群对国家的“俘获”。族群认同加上国家所内含的暴力性,导致的结果就是政治纷争和内战不断。
最大的挑战是驯服暴力
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国家并不是内生的,而是被赋予的,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外部的主权,或者形式的主权。值得关注的是,非洲国家青睐一种绝对主权观念,也就是反对外部的干涉。如果回到主权国家的原点,我们会发现,主权其实主要是针对教权,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世俗国家,所以,这也是现代国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只不过,几百年之后,这一背景已经被淡忘。
科利尔研究了现代国家的“装置”,但他认为,让非洲等后发国家重走一遍欧洲国家的战争立国的过程是非常残忍的。那怎么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国家呢?首先就要诊断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族群政治是很重要的原因,从政权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转换需要构建国家认同,但是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印尼总统苏加诺虽然缺少搞经济建设的能力,但是他们任内还是建立了国家认同,尤其是印尼这么一个群岛国家,能够整合为一个国家,苏加诺功不可没。
不过,科利尔发现,构建民族国家的认同具有很强的偶然性,需要出现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而这样的领导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多数的领导人会依据自己的族群和统治的小圈子来建立庇护关系,长期把持国家、政变或内战在这些国家基本是家常便饭。
依靠这些国家自己的努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比较稳定成熟的国家,既然是被国际体系所“赋予”的国家,那么帮人帮到底,科利尔提出的方法就是国际社会向这些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安全和问责制度,为这些国家“输入”基本的制度。当然,这样的方法触碰到一个根本问题,即主权问题,科利尔建议“共享主权”或者“治理主权”,绝对主权并不是阻挡国际干预的挡箭牌,相比于人道主义干预来说,科利尔的建议相对比较温和。通过维和行动和远距离的安全承诺,逐渐打破最底层10亿人面临的国家构建的难题。
枪炮能够杀人,但是真正杀人的还是人,但枪炮的泛滥无疑恶化了非洲国家的公共安全,而非洲国家的军事开支中有40%是来自海外援助,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果说发展援助无意中为购买军火买单,而且廉价的枪支增大了内战的风险,一个可能的对策是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
所以,国际社会应该减少对非洲的武器出口,工业化时代的战争的后果已经被人看到了,那就是二战那样的惨烈战争。对非洲国家来说,军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内战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浩劫,而且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发展前景。在内战爆发的诸多原因中,科利尔发现,一个国家之前是否发生过内战,是决定它再次发生内战的关键原因。所以要打破一个国家的内战的陷阱,就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维和,而不是在内战结束之后就开始选举,选举无疑会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内战。伊拉克、阿富汗的例子也确认了科利尔的洞见。通过比较长时间的维和,确保国内的安全,同时要发展经济,保持货币的稳定,二战之后的欧洲重建有赖于北约和马歇尔计划,不能不说,这是从非西方视角重新审视欧洲,提供了不一样的见解。
相比于内战,政变的冲击要小得多,而且非洲国家的政变时有发生,科利尔将政变比作不受控制的导弹,政变也有可能让一个国家打破一潭死水的状况,将国家导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科利尔看来,政变有可能成为精确制导的导弹,国际社会必须诱导领导人遵循政治发展的规则,比如任期制,选举落败之后交出政权等。至于如何去做,科利尔提出了一套操作方法,但是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谁愿意去承担为非洲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和义务。
科利尔坚持认为,最底层的10亿人应该生活在国家之中,但是,通往现代国家的道路是曲折的,“国家的形成不是族群凝聚力的结果,而是由暴力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现在知道,暴力不是建国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往往暴力泛滥。”对于最底层的10亿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驯服暴力,建立一个可以合法垄断暴力的“利维坦”。□孙兴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