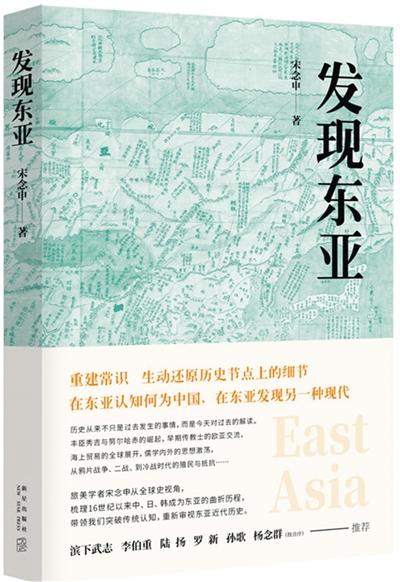
《发现东亚》
作者:宋念申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8年7月

丰臣秀吉(1537-1598)

丰臣秀吉派兵入侵朝鲜,明、朝联手抵抗,直至秀吉病死、日本败退。
公元16世纪末,丰臣秀吉越海兴兵侵略朝鲜,遭到明朝和朝鲜的联合抵抗,历时七年,以日本失败告终。这个事件在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是一笔带过的,似乎除了证明日本觊觎征服大陆的野心由来已久外,并无其他深意。而旅美历史学者宋念申的新著《发现东亚》,却对这个事件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
在宋念申看来,丰臣秀吉发动的这场“朝鲜战争”,奠定了此后三百年东亚的区域权力格局。战后的日本开启了江户幕府时代,中国方面则是满洲的崛起与清帝国的盛极一时,而朝鲜之所以对明朝怀有一种特别忠诚的情感,也是这场战争的社会与文化后果。换句话说,东亚社会的现代历史由此开端。
丰臣秀吉之后,东亚时间开始
宋念申对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东亚大战”本身并未着墨很多,相反,他的观察是从世界史视角出发的。比如,他注意到火器和成建制的火器部队在这场战争中的应用,这是葡萄牙人开拓东方的贸易带来的副产品,同时,海洋贸易通道和基督教的传播,将欧亚社会在万历/丰臣秀吉的时代连接起来,而东亚社会的政权彼此之间的互动,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重塑了天下秩序。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时代之前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并非静态地等待欧洲现代性文明即将带来的冲击,而是自身也在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系,并经由这种联系构造出具有东亚主体性的“现代”。
这种看法相当挑战我们头脑中某种似乎已经固化的历史观念和知识惯性。黄仁宇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万历十五年是“无所谓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其实那一年并非真的无所谓,黄仁宇暗示平淡的1587年其实已经充分证明还在自以为是的明朝要完蛋了,而且不仅是明朝要完蛋了,“以道德代替法律”并“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儒家社会即将走向不可遏制的衰败(decline)。如果说,黄仁宇的解释是一种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论调的话,那么,宋念申对万历二十年发生的朝鲜之战,则保持了一种汤因比式的乐观情绪,丰臣秀吉似乎无意之中对东亚现代性的历史贡献被我们忽视了。
我们一直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比世界史将航海时代到来的1500年视为近代史开端整整晚了340年。这种历史断代的方式,很有费正清冲击-回应论的理论痕迹,似乎东亚社会如果不受到西方冲击的话,自身永远无法进入现代。费正清的冲击-回应论早就被批判为西方中心主义,但仅仅批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发现替代费正清思想的理论工具,以图构建有东亚主体性的历史叙述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念申发现了一段被遮蔽的东亚时间。在他看来,实际上,丰臣秀吉之后,东亚时间就开始了。
新的天下秩序在战后形成
宋念申试图从这段被遮蔽的时间入手,建立起“东亚”与“现代”的历史关联。这种关联来自丰臣秀吉之后东亚三国的互动性历史实践。这里比较有趣的是日本,现代之前的日本有自身的文化底蕴,却也高度儒家化。丰臣秀吉兴战朝鲜的指导思想,正是源于他的中国观和天下观。他着迷于日本之外的那个“天下”,认为大丈夫一生最宏伟的事业,就是入主中原,令“四百州尽化我俗”,实际就是取中国而代之,把大明、朝鲜甚至印度都纳入以日本为“中国”的“天下”。
所以,丰臣秀吉想要摆脱“东瀛”的身份,成为天下共主,或者说将“天下”秩序的中心移到日本。因此,朝鲜之战依然是儒家世界的天下观在发挥作用。虽然朝鲜之战没有在根本上撼动“天下观”的地位,但是新的天下秩序却在战后形成了。此战之后,丰臣秀吉的势力一蹶不振,东瀛诸岛由德川家康收拾统一,锋芒内敛,开辟了两百六十多年的江户幕府时代。大明和朝鲜则元气大伤,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在辽东迅速崛起,并在此后几十年中征服朝鲜半岛、结蒙藏、入中原,创立了盛极一时的清帝国。
而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又令区域内认同于“天下”秩序的各个政权,对作为天下核心的“中华”产生了迥异于前代的理解,自我观和世界观均发生深刻变化。“天下”秩序得到维系并扩张,但其内涵已和此前不同,更孕育了日后与现代国家制度、国际体系相互吸纳演化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念申认为,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的几十年,由朝鲜之战和满洲崛起带来的大变动,是东亚整体步入现代的一个开端。
宋念申提出的这个不以欧洲殖民现代观为参照的“东亚现代”,其意义在于对西方中心主义与东亚的三种国家中心主义的双重批判。如其所言,探讨东亚自身的“现代化”轨迹,其历史观基础是“欧洲、亚洲、美洲乃至非洲的多元的现代历史,都可以被看作是整体历史的地方性部分,不同地域和文化环境中的人既不共享一套时间观念,也不遵循同一种发展逻辑”。所以,谈“发现东亚”,如果只是去发明一些东亚“特有”的“价值”、“道德”、“传统”,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最根本的二元逻辑,也因此更为需要回到本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脉络中来讨论东亚的“现代”演进。这种演进固然有受到欧洲文明影响的因素,但始终保持着某种东亚社会共享的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轨迹。
东亚思想史的“多元一体格局”
宋念申的立场显然是反对历史书写中的各种中心主义。
首先他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中,“东方”始终是“原始的”、“未开化的”、“过去的”、“停滞的”,而西方则是“文明的”、“智化的”、“未来的”、“先进的”。在这一套象征结构中,“东”与“西”之间的二元对立是建立在人类发展的时间序列中的,但二者之间并非是割裂和孤立的,“东方”世界通过发展也可以进入,并且最终必然要进入到“西方”世界(即所谓的“现代”)之中。近代以来日本宣称自身的“脱亚入欧”,其理论逻辑即在于此。而恰如宋念申所揭示的,福泽谕吉对国民国家改造的现代性阐述,“脱亚”的本质是扬弃儒学礼制,而“入欧”则是后人的牵强附会,不过是日本转型成功,希望跻身于西方殖民列强的一种说辞而已。
其次,宋念申也反对近代以来东亚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中心主义叙事。事实上,当东亚历史在时间上被国家主权切割了之后,人们无法解释天下,无法解释包罗万象的大清,也无法解释西学东渐。这同时彰显出发现“东亚空间”的历史重要性:西学东渐之后,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国家边界之上的区域共同性被遮蔽了。在宋念申看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东亚,其重要性似乎并不低于中、日、韩、朝这些分裂的主权国家。无论如何,思想史意义上的东亚有着共同的文明底色,共同的遭受西方冲击的历史遭遇,以及不同的应对西方挑战的历史命运,这或许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这一点上,我沿着宋念申的讨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
东亚文明的特质是天下观,天下秩序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之说,暗示了天下秩序的一种恒常性,其“变”实为“不变”,如顾炎武所谓“亡国而不亡天下”。这种恒常之内,含有儒家的“华夷之辨”,这是儒家中心的普遍主义看法:需要变的不过是“以夏变夷”,而“教化普遍”的儒家自身,即使自身有变,也始终是一种文明标准。然而,与天下观相比,“现代”是一种崇尚变化的观念和制度,特别是科学主义认识论带来的进步史观,赋予历史以实现理性的目的论,在此种“现代文明”的参照之下,儒家思想不过是“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真正的普遍主义似乎已经远离东亚而去。
当天下秩序的时空观念向进步主义的时空观念发生转变,“东亚”与“现代”本身就成为一种进步主义时空观下形成的西方式概念。这可能误导我们的观念,认为“进步”之道路唯有“脱亚入欧”。然而,无论时空,东亚之“脱亚”必不可能,遑论“入欧”。宋念申之对东亚的重新发现,恰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探索,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非不可调和,东亚秩序本身就蕴含了可以转化至进化观念的基础。尤其是朝鲜之战后期,满洲崛起所逐步形成的新的天下秩序,不仅孕育了日后与现代国家制度、国际体系相互吸纳演化的契机;同时,华夷之变与区域性多元文化的强烈碰撞,促使传统儒家的天下秩序发生了转变,几乎是提前预演了今日所谓的民族主义问题。
从“文明开化”观念的入侵到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东亚社会自身也在不断发展演进,尽管这个过程中饱含着新旧混杂的秩序观为天下带来的危机与战火。时至今日,作为舶来品的民族主义观念深重污染东亚,近代以来东亚社会之间的各种恩怨情仇仍无了结。而对于东亚社会未来的思考,却正应从批判性反思民族主义的起点重新出发。
□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