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春华,儿童文学作家,浙江淳安人,现居上海。40年来一直为儿童写作,代表作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等。


《米斗的大计划》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8年7月

《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5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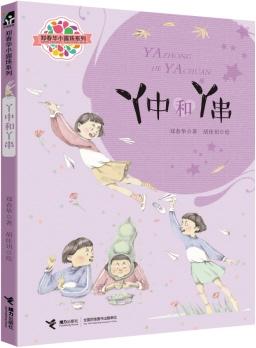
《丫中和丫串》
作者:郑春华 插画:胡佳玥
版本:接力出版社 2016年12月
85后、90后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记忆里,都有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位置。这部制作称不上精细、形象设计也显得有点简陋的片子,即便过了二十几年再看,也不乏闪光和动人之处。那个总是和儿子玩各种游戏,从不高高在上而是做“一对好朋友”的爸爸,现在仍是许多家庭有待努力的方向;片子里那些家庭日常的呈现,与童话式情节的交融,依然有着国产动画少见的亲切和生活质感。
郑春华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故事的原创者,也是1995版动画片的编剧。比起这部作品的大名气,知道她本人的观众和读者可能没有那么多。在中国儿童文学拥抱市场的近二十年“黄金年代”里,郑春华显得比较安静,她的作品不算多,也不常在媒体上露面。直到最近因为新书《米斗的大计划》出版,记者才在出版社的反复协调下,通过电话对她做了一次采访。
曾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组成的三口之家,是幸福家庭的一个样板,但在郑春华近两年的三本新作中,她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有着伤痛或残缺的家庭和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孩子。2015年,《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写了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的小女孩柔柔的故事;之后的《丫中和丫串》,写小区里一对外来务工家庭的双胞胎女孩如何与城市里的同龄孩子相处;最新的这本《米斗的大计划》,写父亲去世的一年级小男孩米斗怎样走出丧父的状态。
在儿童文学中写不幸,并不普遍,也不容易,因为浸透阳光的快乐童年才符合绝大多数家长的期许。读这三本书,故事里的孩子们每次敏感地体会到自己的缺失,都让读者揪心,虽然故事的走向和结局都是温暖的,但那种抚慰、喜悦夹杂着苦涩、无奈的感受,是儿童文学作品不常能提供的阅读体验。
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这三本被命名为“小露珠系列”的新书,对郑春华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但其实在当年,她的创作初衷就在于看到了独生子女时代很多孩子的孤独感和父亲陪伴的缺失。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还是直面缺憾本身,近三十年过去,郑春华不同的选择之下,都不曾离开对童年和社会现实的关怀。
新京报:为什么会从《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开始创作这样一个系列?有具体的生活原型或缘起吗?
郑春华:《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其实有一点点生活原型,是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个伙伴,她本来是我们的邻居,在父母离婚之后搬走了。我们有时候会想到这个小孩,可怜她,担忧她。几年之后,我在一个文具店里遇到她,认出她来,很惊讶,因为她和我想象中的离异家庭的小孩完全不一样,比以前长得好看,穿着打扮也很好,跟爸爸自然地交流,好像在给老师选教师节礼物。如果我不知道这个小孩的过去,根本不会想到她来自一个离异家庭。那天从文具店走出来之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灵感。
我想得比较多的是,有时候我们成人因为已经有阅历、有经历,已经吸收进来很多东西,在生活当中遭遇一些不幸的时候,之前吸收进去的负面东西可能会去强化它。小孩子他们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面对生活当中灾难的时候,可能处理的方式反而跟我们成人不一样,更单纯、更包容、更有力量。
新京报:儿童文学一般来说都是美好的、阳光的,你选择以苦难为题材,自己会感到是一种挑战吗?
郑春华:我觉得儿童文学好像不能很单一的、永远是写快乐校园的一些作品。因为世界是完整的,肯定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要经历这些不幸的,这是童年生命当中客观存在的事件,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写。
我认为儿童文学任何题材都可以写,问题是你怎么去写。像《米斗的大计划》的写作,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我对于儿童世界的长期观察积累的一个产物。因为我觉得我们社会对儿童的尊重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情感和心理上,对孩子有太多太多的不理解。很多大人,包括我也是会带着一种固有的经验去认为一个离异家庭孩子就会是怎样的,一个失去亲人的小孩就会是怎样的,但其实不是。所以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其实是想探索儿童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儿童文学有儿童性的要求,你在写作时,如何调配苦难与阳光之间的比例?
郑春华:有一点我是很明确,因为我写的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它首先是儿童的,其次才是文学。所以我写这样的题材,肯定不会写成那种很痛苦的、催眼泪的。我会又顾及这个题材,又顾及这是儿童去看的。所以说回到的就是儿童的单纯性,一种不受成人世界干扰的、产生于他们自身的那些力量。他们有那种很单纯的童心去面对、去消化这些生活当中的变故。所以写到米斗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去强化这个悲剧,而是用自己的单纯和简单去吸收消化这个灾难。
新京报:你想象中的读者是有类似经历的孩子,还是那些生活幸福、从来没有体会过这些的孩子?
郑春华:其实我不会去想太多这样的问题。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写作首先是为我自己,就是心里感受到的东西我得把它表达出来,发现的东西我要尽可能地把它展现出来,不表达出来我会很难受。第二呢,我觉得我的写作应该比较多的是跟孩子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去教育他们。
像这样的题材在孩子当中应该不是一个大众化的题材,甚至很多家长可能会蛮回避的,觉得它是不吉利的、不开心的。家长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接受那些快乐的儿童文学,我知道这些,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编辑。所以我比较多的想法是在于自己,不会过多地去想读者群。
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一个作品只要它具有文学魅力,不管是哪一类题材,我觉得孩子都同样地会去吸收它,家长也一样。而从我的写作来说,我肯定一直坚定自己的价值取向,坚定自己的三观,我不会去迎合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或者说小朋友的价值取向。
新京报:《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获得了成功,现在的童书写作和出版受到市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是怎么看待影响力、收入和你的创作之间的关系的?
郑春华: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回答你这些问题。我现在一年365天,其实分成了三大部分。三分之一的时间,我是在阅读、看书,我不是去研究它,只是沉浸在这些故事当中,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需要。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写作,表达。你说的迎合市场这种,我做不来的,也不会去做,我只能做的是我想写什么。可能出版社也比较了解我的个性,大家不会来要求我写什么东西。
还有三分之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无奈。(叹气)我必须去做校园活动,我必须去签售。那么这一点我为什么又屈从了?我毕竟也是一个生活当中的人,我知道今天的作者跟出版社、跟书店,已经是一个团队了。编辑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在做你的书,营销这一块我就必须配合。从我内心来说,就整个的签售活动,我心里是很抗拒的,但我没有办法。
其实去校园跟小朋友们做演讲、互动,我还是很喜欢的。所以现在到学校去,我做到的只能是,不希望在现场卖书。我又不是到学校去叫卖的,喊“这个袜子是全棉的,这个T恤是吸汗的”,如果变成这样一种效果,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还有一家出版社曾经跟我沟通,要在一个商场的中庭请我做一个讲座,把我所有的作品打包售卖。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的反应是很抗拒,抗拒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其实在我的心灵深处,我真的在坚守自己最后的尊严,我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完全变成一个商品。
新京报:你未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郑春华:前段时间电视里太多太多的真人秀,造成很多孩子一天到晚的理想就是歌星明星,那我会在想,我们这个社会主要还是普通人,是很多普通的职业,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在我的作品里展现这些职业。我要以他们为主题写一些故事,所以我最近连续写了蛮多的绘本,还在继续写,比如消防员、环卫工、园林工人、机场指挥飞机的引航员……包括那些24小时便利店里晚上值班的人。我们忽略了他们,也不会去告诉我们的孩子,有这些人在为我们服务,要尊重他们。那我至少在儿童文学作品里面让你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职业,并且对他们有一种敬畏的心。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