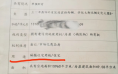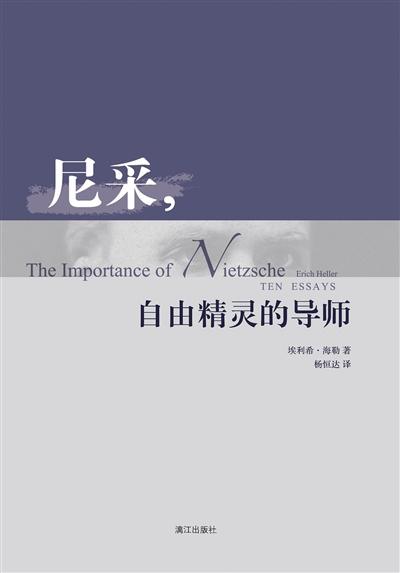
《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
作者:(美)埃利希·海勒
译者:杨恒达
版本:漓江出版社
2018年8月

里尔克画像。

维特根斯坦画像。
20世纪著名人文学者埃利希·海勒所著的《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是一部独特的尼采研究专著。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横向比较研究的跨度和视野,这在浩如烟海的尼采研究文献中可谓独领风骚。
纵观现代德国文学和德国思想,受尼采哲学影响者几乎可以构成大半部文化思想史。诗人里尔克、格奥尔格,作家卡夫卡、托马斯·曼、穆齐尔,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任何一位,按照尼采研究者埃利希·海勒的说法,说出他们名字的同时,也意味着说出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名字。当他们以或诗意、或哲学的方式思考世界,尼采思想就是他们用以解释的工具。于是,尼采成了“后尼采时代”思想者的某种思维范式:无论是从主题,还是结构的角度。
作为尼采研究专家,人文思想领域的著名学者埃利希·海勒在这部集结了十篇尼采研究性论文的作品中,结合尼采的重要著作如《人性的,太人性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等,对尼采与布克哈特、里尔克、叶芝乃至维特根斯坦等人,做了关联性的比较。
尼采、布克哈特与信仰
19世纪的文化史、艺术史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杰出研究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有一段时期与尼采是巴塞尔大学的同事。尼采在一封信中如此描绘这位年长的同事:“那位近老年的、十分有独到见解的人,不是倾向于歪曲真相,而是倾向于悄悄忽略真相。”
在尼采看来,布克哈特的宁静生活似乎是一副面具,面具之下是一个叛逆者的心灵。事实真的如此吗?与尼采不同,布克哈特对传统信仰的思考,乃至对信仰的丧失,并不如尼采那样彻底,他的丧失“只是由悟性流露出来的”。宗教危机,在尼采那里激发出靠荒野而活的超人,对于布克哈特来说,他所经历的“动摇”,比如对基督诞生细节的怀疑,并没有扰乱其存在的核心。1889年1月6日,尼采在致布克哈特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教授先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也会十分偏爱巴塞尔的一个教席,而不愿当上帝;但是我不敢在我私下的自我主义中竟至于因为这个原因而避免去创造世界。”面对尼采的态度,布克哈特的回应是冷漠的,因为前者似乎触碰到了他那不忍去触碰的“绝望的自我”。
海勒认为,对于布克哈特,尼采虽然在理智上抛弃了他,在情感上却仍然是认同的,而另一个如此存在于尼采心目中的是叔本华。知识上的诚实,清醒的精神活力,这些特质让尼采仍然赞美他们。尼采在古希腊人身上发现了这种特质,并在《悲剧的诞生》中热烈地讴歌。
在《布克哈特与尼采》一篇里,海勒对尼采与布克哈特在思想上分道扬镳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分析,从他者的角度展现了尼采对宗教问题的态度。
尼采、里尔克与诗
奥地利诗人马利亚·里尔克,其年轻时期的诗作便受到尼采的影响。海勒认为,里尔克在早期的作品中模仿着尼采,且有一定的庸俗化。尼采哲学的巨大冲击力表现在里尔克的作品里,但这种表现仅仅是流于形式的,前者的深邃和复杂并没有真正被吸收。比如早期的短篇小说《使徒》,便是对尼采风格的某种“拙劣”模仿。
然而,在诗人的生命接近终点之时,那两部伟大的长诗,众所周知的《致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以及《杜伊诺哀歌》,便深刻展现了诗人与哲学家之前内在观念和态度的愈来愈深的相似性。他们对平庸时代的厌恶,对贵族血统的渴望,这些精神上的共性表现为他们各自作品中的某种共鸣。
譬如里尔克的诗句:“成功地调和了他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的人,将它们收在一起变成一个象征,把喧嚣的人群推出宫殿,将成为不同意义上的节日,接受你作为他温柔夜晚的客人。”
而尼采在他的《诗集》里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在一起确信我们的胜利,我们庆祝万节之节:朋友查拉图斯特拉来了,万宾之宾!世界欢笑,可怕的幕布被撕开,无论有光还是有黑暗,婚礼都已到来。”
海勒把前者称为“对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诗歌的极强音段落中失去控制的主题的慢板处理”。
在《里尔克与尼采》一篇中,通过两者具有呼应性质的诗文的对照分析,海勒以复调般的技巧探索着里尔克与尼采两者各自对宗教、艺术、音乐等主题的思考。
尼采、叶芝与词语的激情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作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唯美主义认为艺术只能以自身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为了传达某种观念或思考。正如诗人自己的诗句所说的,“想得太久的东西,不再是思想”。
叶芝大概是在1902年接触到尼采的作品,那时哲学家已经在历经了十年的疯狂后去世。在那本关于尼采的小册子的页边,叶芝留下了许多笔记。而这些笔记与其说是对尼采思想的理解和解读,不如说是某种更个人化的“介入”。正如海勒所说,“一旦叶芝在页边上纠缠于尼采思想,便倾向于消失。”
比如叶芝在尼采反基督、反托马斯的文章旁问道:“但是为什么尼采认为夜里没星星,除了蝙蝠、猫头鹰和不清醒的月亮以外一无所有?”可问题是,尼采的文本中并没有表达出相关的意思。有趣的是,诗人同时期创作的诗句却包含了这些意象:“因为事情的说出伴随饥饿的号角/猎手的月亮,挂在日与夜之间。”所以,海勒如此评价诗人的这番阅读:“无论理智是什么,无论清醒月亮的可转化清醒意义,还是那些页边的蝙蝠和猫头鹰意义,只有一颗心,为它自己的诗的事务忙碌不堪,竟然会以如此富于想象的不耐烦来读另一位作家的著述。”
尼采是一位箴言大师,他对词语的精准的语言感,直接表达并激发着思想。显然,叶芝读尼采,很多时候不是解读,而是在哲学家的文本中再次激发自己内心早就存在着的概念。
尼采、维特根斯坦与天才
海勒在《维特根斯坦与尼采》一篇中,准确选取了尼采文本中与维特根斯坦思想极具相似性的段落,做出了精彩的对照分析。
维特根斯坦是剑桥哲学家、潜在的工程师、闻名于家族的建筑师,同时,也是乡村小学教师、辞典编写者、侦探小说爱好者,以及极具艺术修养的爱乐人。如果用一个词来给他做一番速写,这个词一定是“天才”。同样,天才的称呼也适用于尼采。
维特根斯坦与尼采极具相似性,前者一生行事可算乖张,而后者直接走向了疯狂。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激发了他同时期和之后的几乎所有哲学家的个人思考,尼采亦如是,两者都堪称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尼采去世时,维特根斯坦还是名少年,在思想上,两者并没有真正的交集。
“我任何时候都以我的整个身体和我的整个生命思考。我不知道纯有理解力的问题是什么……你通过思考知道这些事情,然而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经验,而是其他人的经验的回声。”
这难道不是《哲学研究》里的某个小节吗?不,这来自尼采死后发表的关于《曙光》的笔记。
在《快乐的知识》里,尼采曾写道:“我来得太早了。我的时辰尚未来到。这个非凡的事件还在半路上走……闪电和雷鸣需要时间,星星之光需要时间,它们的光和声音即使在行为发生之后,也需要时间才能被看见和听见。”于是,他以疯狂代替了沉默的等待。
而对于他的读者,无论是诗人、思想家、作家,还是任何一个我们来说,尼采作为一种范例,“陌生、深刻、混乱、诱人、令人生畏”,他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被认为真正的范例。然而他以其狄俄尼索斯式的力量,为我们的思想划定了疆域。□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