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时间1月12日,法国“黄背心”运动示威者发起新一轮示威抗议活动。图/视觉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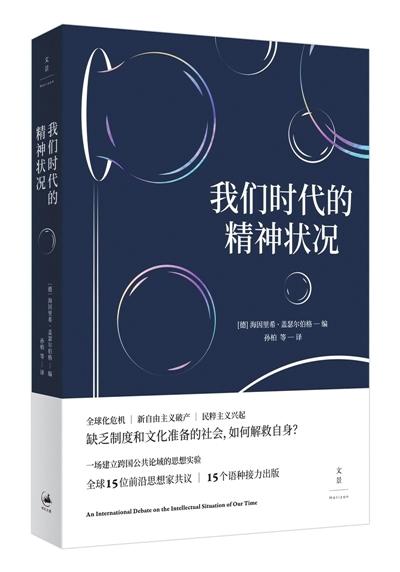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作者:(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
译者:孙柏等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政治变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旧秩序的瓦解。弗朗西斯·福山适时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取得最终胜利,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将成为支配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世界向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打开大门。但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似乎并未验证福山积极乐观的预言,历史并未走向终结,反倒是充满危机和创伤。
在德国出版人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所编的《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15位享有国际盛誉的思想家几乎同时给出了一个略为悲观的结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大衰退”的时代,威权崛起、国家高压、宗教冲突、民粹勃兴、移民恐慌和反伊斯兰情绪蔓延……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出现了功能性失调,整个社会弥漫着严重的受挫情绪,以及因之而生的不满和怨怼,自由民主日趋寡头化;政客被财团势力裹挟;党争渐趋白热化,致使公共事务所必须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
新自由主义面临复杂危局
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至上原则,强调个人权利,包括少数族裔的权利,尊重个人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选择,支持民权运动;强调平等与社会正义,保障社会福利;提倡宗教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实现民主和平。
但书中弗雷泽的文章《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为我们描绘了一种悖论性的局面。新自由主义的种种理念在社会中达成了两项联盟:一方面是新社会运动中各类主流力量(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LGBT权利)的联盟,而另一方面则是高端的“象征”,即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商业领域(以华尔街、硅谷和好莱坞为代表)。
在现实中,这两项联盟为损害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生机的政策推波助澜。多样性、反歧视、女性赋权等政策并非旨在废除等级制,而是为了识别精英群体,“这些术语将解放等同于在赢家通吃的公司等级制中‘有才’的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者的崛起,而不是废止这种公司的等级制”。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美好理念只不过是等级制的装饰,是精英群体身份的标定,通过支持多元文化、少数族裔权利、宗教宽容等,精英得以维持自己的身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图景中,获益的始终是精英群体,至于大多数人所体验到的则是一种缺失感。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置身于流动的现代性中,新自由主义是促成流动社会形成的重要力量。强制的流动性和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摧毁了个人、集体,以及政治认同旧有的根基。大多数人体验到若有所失之感,并对体制抱有一种强烈不满。
例如,在美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过去二十多年来失控的金融化逐步蔓延,使得该地区的工业中心遭受巨大打击,工人群体生活条件日益恶化。正是这部分人,在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对这些人来说,自由派的那些理念无异于天方夜谭,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机会、税负、宗教信仰和社区安全,而新自由主义政策往往忽视了这批人的诉求。
因此,当今时代的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怨恨的政治,米什拉在其文章中称其为道德化、情绪化又政治化的分崩离析。新自由主义先是打破个体对自身既有社会位置的认知,个人主义的信条削弱了社群连带,个体原子化状态明显,孤立感不断增强。鲍曼在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提到,正是这种不稳定状态,促成人民对“决断论”领袖的需求,从而挑战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理念。
如今,新自由主义危机重重:首先在经济领域,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并未恢复经济增长与繁荣。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在民众看来,政治权利越来越牢固地掌握在大公司的手里。政治和经济勾结,社会抗议运动将此视为民主的堕落。在参与“占领华尔街”的民众看来,新自由主义许诺的自由、平等、正义等理念已经成为空头支票,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助长了右翼保守势力的进一步崛起。
右翼保守势力进一步崛起
保守主义的声音如今越来越明显,事实上,最初的保守主义运动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它更多的是各种抗议声音的集合。还是以美国为例,尽管保守主义形式多样,但它们的共识是反对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它们相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日益膨胀的官僚化,甚至走向极权,最终摧毁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多元主义、LGBT权利等,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严重损害了基督教的传统伦理价值,价值相对主义制造出了巨大的精神真空,最终会成为导致西方自身毁灭的工具。
保守主义运动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其支持者往往是下层民众。对于后者来说,新自由主义及全球化的获益者,是那些参与了国际竞争的企业家和相关部门的合格雇员,还有世界公民,而失意者恰恰是本国下层民众。因此,当代的保守主义崛起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美国的茶党(Tea Party)运动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运动,其理念正是保守主义,而它代表的正是受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双重挤压的中产阶级,如小业主、小商人等。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的理念。在经济方面,茶党要求削减支出、减少债务、平衡预算、改革税收、反对医保改革;在社会价值上,主张维护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在社会政策方面,拒绝全球化,反对移民,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特朗普上台后,其政治主张更是体现了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他希望借此颠覆美国长期执行的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各项政策。
右翼力量的崛起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首先,它将进一步激化宗教冲突,它将重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事实上,基督教在经历过现代化的洗刷后已经变得非常世俗化,而伊斯兰教则多少保持着原教旨主义色彩,随着中东、北非地区的战乱,大量穆斯林涌入欧洲,使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更为紧张。加上欧洲出生人口的连年走低,欧洲的穆斯林化成了极为严峻的问题。
最后是民族主义的问题,特朗普上台后的口号是“让美国重新强大”,其一系列政策优先考虑美国,而不是承担国际责任,例如关闭移民口岸、退出《巴黎协定》、与各国展开贸易战、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特朗普的这些措施放弃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普世主义理念,甚至回到一种前现代的“部落主义”,对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
书中,国际知名左翼思想家齐泽克有一个颇具洞见的观察。在他看来,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带来了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即它成为政治舞台上唯一抱着真正的政治热情,抵抗全球化后政治自由民主霸权的力量,尽管我们不得而知这种抵抗将会把我们带向何处,但它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政治的机会。
齐泽克用“后政治”去描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历史终结论带来的局面,后两者将政治降低为一种治安技术,通过权利和角色的分配,将一部分人纳入体制,而将另一部分人从社会系统中排除,政治成为技术官僚与专家系统掌控的治理术,而真正解放的政治则被当作噪音被压制了。在右翼保守主义崛起过程中,部分正是那些在系统中被排除的无份之人,他们希望要回属于自己的平等权利。
正是在这里,齐泽克意识到,右翼保守主义的崛起也为左翼运动提供了新的力量,因为二者有了共同的目标:挑战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左派运动一直致力于反对体制化的力量,追求个人自由和解放,而新左派的社会运动也一直围绕着身份政治展开,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差异化的政治局面。他们用一种风格化的反抗方式维护着个人的自由,反对技术统治、官僚化政治和盲目的经济增长。
保守主义的崛起正是建立在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对自由主义攻击的基础上,不过它只是为了不同的目标而精明地挪用了新左派的理念,尽管二者在很多政策上针锋相对,例如对少数族裔权利的保护上,新左派显然是要维护他们的权利,而右翼保守主义则选择直接忽视他们,甚至反对他们的合法权利。但齐泽克之所以要重提新左派,是想利用新左派的理念去抗衡右翼保守势力,避免后者走向极端化、法西斯化。
弗雷泽认为,这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也是建立一个新的“新左派”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该丢掉虚假的神话,在精英虚伪的多样性、宽容之下重新承担起责任。拒绝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和反动的民粹主义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借助广泛且不断扩大的社会反感情绪来重新制定新的秩序。
□曹金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