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国人涌上街头庆祝“公理战胜强权”。然而,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陆续传来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国人的自强迷梦,整个中国如同一个被引爆的火药桶,群情激奋,躁动不安。正当此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在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华访问,并迅速掀起一阵思想旋风。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进步教育运动之父”。
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停留的杜威,被眼前这个从沉重历史中苏醒的新生共和国深深吸引,他改变了原定计划,两次延长学术假期,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一生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杜威,并未安坐于书斋,而是踏遍了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在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民主和教育观念的同时,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对中国时局、文化、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在孙中山、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知识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如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尽管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更像是一个带着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观者,但人们还是迫切地想从他身上找到诸多疑难杂症的答案。
杜威也试图结合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现实观察,为中国人提供一份可靠的答卷,但有时候他也会陷入怀疑和沮丧——他心中的问题多于答案。尽管如此,他还是自发地充当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大使”,把美国的民主理念和实践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寻求国际支持和民族独立的民意传达给美国。他向世人强调,“中国正在迅速发生改变”,美国应当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角色。他成为两个民族交流经验与思考的关键人物。
今年是杜威诞辰160周年,也是杜威访华100周年,新京报文化频道策划此专题,旨在重新检视杜威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并重温其关于教育哲学、实用主义和民主问题的思考,这种回顾与反思对今天的文化和时局仍然大有裨益。
杜威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爆发前的1859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二战后的冷战,今年是他160周年诞辰,距他去世(1952)也已经67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从上世纪末开始,杜威又重新受到美国思想界的关注,一下子涌现出许多关于杜威的学术著作——
《杜威对美国传统的贡献》(1995),Irwin Edman Bobbs-Merrill
《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1997),Robert Westbrook
《杜威的政治哲学》(1998),Terry Hoy
《杜威:思考我们的时代》(1998),Raymond D. Boisvert
《杜威论民主》(2000),William R. Caspary
《杰出的教育家》(2000),Maurice R. Berube
《杜威的教育:传记》(2002),Jay Martin
《经验与价值:论杜威和实验自然主义》(2003),Morris Eames
《杜威的精神哲学》(2010),John R. Shook
《约翰·杜威》(2010),James A. Good
《生活的信心:杜威的早期哲学》(2011),Donald J. Morse
在今天,杜威对中美两国学界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他与两国现实的联系方式和内容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当下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对美国读者来说,他更是一位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土实验主义哲学家。
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提供的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思想或公共政治理论;但对美国读者来说,杜威讨论的自由和民主是他们的国情政治。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谈杜威:杜威和他的时代,杜威式的公共政治,以及对今天的美国仍具现实意义的杜威哲学。
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杜威
民主理论是杜威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在哲学、教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领域论述的聚焦点。如今看来,杜威的时代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1952年他去世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艾森豪威尔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才3400美元,大学教师的年薪大约是5100美元,只有3/5的家庭拥有汽车,2/3的家庭拥有电话,1/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快餐店正在越来越受欢迎,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还没有疫苗,汽车刚开始装上自动变速箱,汽油是每加仑25美分……在那个如此“久远”的年代诞生的杜威民主理论,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其实,杜威的时代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久远。早在1919年,希特勒就预言,一个独裁的时代将要来到,他说,德国需要由一个独裁的个人来领导一个独裁的国家(autocratic state),“德国的重生将不是由民主来启动,不属于那些受党派教条和无良报纸影响的不负责任的大多数人,也不依靠国际上那些标语和口号,而只能依靠有能力领导国家的个人独裁,他行动果断,有内心责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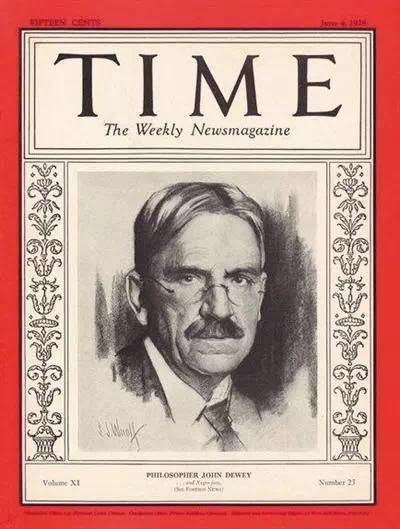
1928年6月,杜威登上《时代》封面。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陷入危机,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相信自由民主必将被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所代替,他们有的直接投入法西斯主义事业,有的成为他们的同路人。三四十年代,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加入亲德和亲苏浪潮,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杜威不仅捍卫了民主理念,而且把民主当做一种合乎理性的,因此必须与非理性的法西斯主义相对抗的信仰。
这就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人道自由主义”(humanist liberalism)民主观念,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今天,许多美国学者重新认识和重视杜威,是因为他们认清,随着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新专制主义的兴起,人类世界又一次面临普遍的民主信念危机。杜威民主理论的信仰坚持和价值探索,不仅要对抗这些反民主的逆流,而且也要批判审视自由民主本身的缺陷。杜威的民主信仰所坚持的不是民主的完美性,而是,不管面临怎样的外部威胁,不管民主本身存在什么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重新思考杜威式民主》一文里指出,杜威说“民主是充分运用(人的)智力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民主是一种探索的形式,也是相信,理性思考可以让社会和世界变得更好。这是对民主的信仰,而非民主的现实。
杜威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影响,在卢梭那里,人性本善也是一种信仰,人在原初自然状态中的善良,既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你相信,那就够了。正是由于杜威对民主的这种性质的信仰,他在美国民主因其不完善而饱受攻击和怀疑时,能够保持信心。但是,他同时认为,民主是需要在探索和实践中改善和优化的,他称这种探索和实践为“实验”。他认为,民主的实验会一直继续下去,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听命于少数精英,而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们共同参与这样的实验。杜威说,“我们在世界的一边建立起一座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伟大的社会实验将会使全世界受益”。他还说,“无论(美国民主)问题有多么严重,实验还在进行。美国还没有建成,对美国民主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对民主有着同样信念的美国人。
杜威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他那个时代理论争论的产物,他的民主信念与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和记者李普曼的“现实自由主义”(realistic liberalism)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原则性的冲突。一战前后,美国民众受战争宣传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狭隘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使得包括李普曼在内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公众极为失望。战争是最容易鼓动民众集体爱国狂热的,这也是民众情绪和舆论最容易被政治宣传操纵的时候。美国虽然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那样经历过民众狂热投入法西斯或其他专制政治运动的事情,但是战争宣传极易在民众中获得影响力。李普曼于1922年发表了《公众舆论》一书,强调“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和不可信任。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复杂和规模使得一般人难以对它有清楚的把握。他们一般从事某种单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计,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深度关切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很少认真涉入公众事务讨论。他们遇事往往凭印象、凭成见、凭常识来形成意见,因此很容易受到政客的煽动和利用。
杜威认为,李普曼这样看待公众舆论无异于在起诉当代民主,他在《公众及其问题》(1922)中对此作出反驳。杜威指出,民主不只是政府的运作和决策,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按照某些基本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些原则包括人人可以对社会有所贡献,人人都有理性决定的能力,只要学会了学习和讨论的方法,人人都能够弄清复杂的情况。杜威反复强调,无论民主的现实多么不尽如人意,民主是可以改进的,而改进民主的根本前提就是对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他指出,公众是实实在在的人群,公众不等于民众,公众是那些拥有共同问题并共同需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众。当民众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并将之合理解决的时候,他们便成了公众。公众舆论总是与民众看到问题、讨论问题、努力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杜威承认,民主和公众舆论还不完善,但这是因为这二者都还处在“初期”阶段,并不是因为公众必然无能、民主必须精英的缘故。

《哥白尼式的革命:杜威哲学》 作者:约翰·杜威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2月
身体力行的公共知识分子
杜威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哲学家或理论家,而是一个身体力行自己民主信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到他92岁去世。从19世纪80年代他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开始,他就已经在从事心理学和哲学方面的写作,随后出版的教育和政治著作更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人物。美国“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1890-1920)结束的时候,当时许多人认为杜威的学术生涯已经达到巅峰。
有人向哈佛大学校长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建议把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招聘到哈佛来当教授,洛威尔认为杜威已经年过六十,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所以拒绝了。但是,洛威尔错了,杜威更多产的日子还在后头,在接下来的15年里(1919-1934),杜威创造了美国思想史上的奇迹。他的《重建哲学》《人性与行为》《经验与自然》《作为经验的艺术》一本接一本地出版,同时还在《新共和》上撰文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缺陷,甚至还准备组织一个比民主党偏左的第三政党。
不仅如此,上世纪30年代晚期,杜威又出版了其他哲学著作,包括《逻辑:探索、自由和文化的理论》。他78岁的时候,到墨西哥城去主持“杜威委员会”(Dewey Commision),调查关于托洛茨基勾结纳粹的指控,杜威委员会于1937年9月21日在纽约公布了调查结果,宣布洗刷莫斯科审判期间强加于托洛茨基的所有指控,并揭露这一审判对被告栽赃陷害的事实。1939年5月14日,杜威和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创立“文化自由委员会”(CCF),它关于组织原则的第一份公开声明,就明确区分了民主社会和极权社会的根本界限。到40年代,杜威仍然非常活跃,对1948年总统参选人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提出批评。
杜威是一个真正投身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他的哲学、政治和人生是一致的,至今仍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表率。他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那个时代虽然看上去已经离我们相当久远,但杜威讨论过的一系列公共问题,仍然能对我们今天有现实的启发,尤其是他对公共理性、公共经验分享、公共交谈等问题的观点。这些问题构成了杜威的公共政治理论,是他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杜威强调公共理性中的反省性思维。他在《经验与教育》(1936)一书中说,反省性思维需要“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念或被假定的知识形式,洞悉支持它的理由,以及它所进一步指向的结论”。反省性思维要求训练和耐力,“(一个人)可能还没有细加思虑便匆促结论;可能疏忽或减缩了求问和求知的过程;可能因为思想懒惰、反应迟钝或没有耐心而一有‘答案’便以为解决了问题。一个人只有在愿意暂时不下结论,不怕麻烦继续研究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反省性思维”。
在《民主与教育》一书里,杜威还指出反省性思维在群体交流中的另一层含义: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这时候,思想的力量和缺陷才会显露出来。为了交流,思想必须有所规范(formated),“规范要求我们以别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个孤独存在的人很难或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反省,也不可能从中总结出清楚明了的意义来。”
作为反省性思维的批判性思考,它的“批判”不是吹毛求疵地挑错,也不是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人,更不是给别人戴帽子、打棍子,而是一种自觉严谨的慎思明辨,也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理性思考”。理性是一种怀疑精神,包括怀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们引向确实的真理,但能帮助我们抵制谬误、自欺和欺骗。
又例如,杜威主张并致力于营造一种能让每个人都有必要的机会和资源来参与的共同体(communities),让每个人都有可能参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这是他的民主信念的基础,他哲学中的形而上、认知、心理和伦理理论都源自这个民主信念,涉及参与型民主不同方面的问题。他认为,人运用智力需要有与他人的系统合作,公民群体是实现公民自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是公民自由参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杜威崇尚的是人在社会中可以分享的经验,所以他特别强调人与人自由而直接的交谈(在互联网时代,这需要做技术性的修正)。他指出,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他在1927年写到,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哈贝马斯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在每次对话中,一个个私密性的个体会合并成一个公共团体,一部分公共领域便由此产生”。在他们那里,对话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
当代美国传媒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讨论杜威对公众交谈的政治见解时特别补充说,一般人际间的社交交谈并不能自动产生民主规范,更多的情况是民主创造对话,而不是对话自然产生民主。民主培养了某种自我,虽然难以察觉而且并不完善,却仍然效果显著。民主培养的那种“自我”有公共说理的意愿和能力,并要求用交谈和对话来参与公共政治。在民主国家和公民社会里,个人的说理和对话权利是公民身份的一种体现,也是行使公民责任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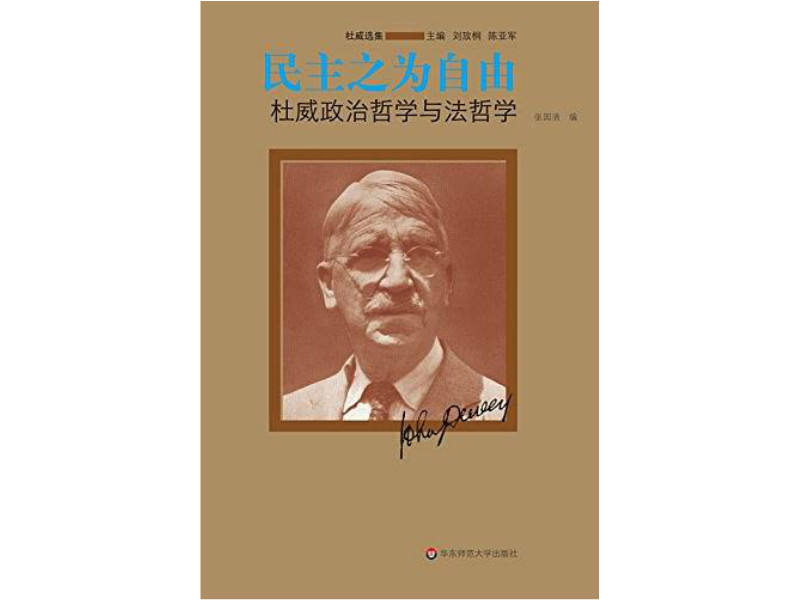
《民主之为自由:杜威政治哲学与法哲学》作者:(美)约翰·杜威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
今天的美国人为何关注杜威
美国政治学者摩根·威廉斯,在《21世纪的约翰·杜威》一文中提出,“杜威对民主、社群和解决问题的信念,引导了他的社会和教育哲学的发展。杜威也许是迄今对教育影响最大、最著名的哲学家”。
今天,不仅在教育领域里还能看到杜威的影响,在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里也是一样。杜威的影响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实验主义复兴有关。美国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实验主义的复兴》一书中指出,实验主义经过好几十年的沉寂之后,于20世纪中期重新在社会学、法律、文学研究、哲学等多个领域中重新受到重视,成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之外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杜威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实验主义(pragmatism)经常也被翻译为“实用主义”,但“实验”并不只是局限于实用。杜威的实验主义强调的是“创造性的智能”(creative intelligence),重在改变现状而不是与现状妥协,它是务实的,但在不少方面又有明显的理想色彩。杜威在《需要恢复哲学》(1917)一文中说,“有人认为经验主义只在乎发生了的或者是现已有的。但是,最要紧的经验是实验,是为了改变现有的……向前探索未知,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联系未来”。向前探索,让民主优秀起来,这正是杜威民主思想的一个特色。

晚年杜威。
由于实验主义在美国的复兴,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杜威哲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重新解释,也就特别受到重视。罗蒂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杜威和罗蒂的思想比较,已经成为美国自由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热点,也让21世纪的杜威研究有了一个20世纪的参照点。本文引言里提到的那些著作,不少都讨论到这个问题。
韦斯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的《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就是一个例子。他指出,罗蒂对杜威的解释,是在自由主义左翼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中发出的不同声音,杜威本人也属于这个传统。罗蒂认为,政治无非就是要保障个人与个人之间尽量不要互相伤害,也尽量不要干涉彼此的私生活,这样隔离公域和私域,与杜威不主张严格划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是不相符合的。由于隔离公域和私域,罗蒂重申的是经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也就是个人可以不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这是政府不能干涉且在个人之间也要尊重的自由。但是,杜威一贯坚持的则是一种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自由。在美国,公域-私域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在民主与法治制度中制定政策、政府有何权限、公民如何对待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些仍然是21世纪美国政治的主要问题。
杜威坚持认为,民主是在不断重构的,不具有最后的确定性。他的哲学实验主义把任何政治制度,包括自由民主,都视为人为的建构,反对任何先验的形而上的确定结论。但是,这不等于说,一切政治制度都是同等的武断和任意,没有本质的差别。杜威坚持认为,民主和专制、法治与独裁是有区别的,因为人类价值探索和不断实验所获得的知识,能证明民主有益于人的自由、自主性和全面成长,而专制和独裁则是有害的。
但是,杜威民主信念中的一些理想主义问题,在今天美国的现实政治中也更清楚地暴露出来。当年他与李普曼关于民众的争论议题——民众是否真的明白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够成为充分理性的公民、民众自决是否有效和是否过时——在今天成为更突出的问题。1925年,李普曼在《幻象公众》一书里把“公众”直接指称为一种幻觉。他认为,天真的民主主义者们自己长期头脑糊涂,才会自欺欺人地编造出公众和公众舆论的神话。他断定公众舆论“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力量”。公众舆论在过问政治时,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这简直就像是针对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利当选说的。大选的结果出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预料,使政治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民众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刻,是对民众采取怀疑、否定和犬儒的态度,还是保持审慎的信心和希望,成为21世纪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许多美国人认为更有理由重申杜威的民主信念,也更需要坚持,一方面要相信公众政治参与的能力,包括自我纠错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公众的启蒙要比对政府管理者的启蒙更重要。
在美国,杜威研究一直是美国自由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对自由民主的学术研究,也是对美国的一种现实国情研究,而不是像在一些其他国家那样,只是学院或书斋里的纯学术课题。这些研究与美国人改变和优化自己的政治、社会环境息息相关,也是他们须臾不可缺少的自我审视和批判性思考,因此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今天,美国还是有许多像杜威那样从国情来思考和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被称为“杜威式学者”(Deweyans)。他们的许多著作都涉及杜威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阅读他们的著作也会让今天的人们对杜威有新的认识。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加勒维,高度赞扬杜威对美国自由民主和社会改革理论的贡献。他认为,谈美国民主和民主理论不能不谈杜威,就像不能不谈杰弗逊一样,“杜威的著作(和杰弗逊的一起)已经成为最接近美国‘正式’哲学的那一部分”。与杜威的这种贡献相比,政治哲学家们是否同意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见解,已属次要。重温杜威的民主理论,也就是重温美国的民主理论传统。
杜威是从杰弗逊、爱默生到皮尔斯、威廉·詹姆斯这个美国本土传统中的一员。正如加勒维所说,“杜威结合了杰弗逊、爱默生和詹姆斯的道德理想主义和皮尔斯那种不屈不挠的科学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欧洲理论在美国的退潮和美国本土理论更加受到学界重视,杜威的影响也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徐贲
编辑:徐学勤、榕小崧、沈河西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