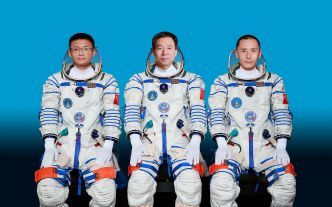曾国藩与他的同代人。
【编者按】
与其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国藩“出版热”反映了曾氏本人的多面人生,不如说这现象实际折射的是当代人的具体焦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作为个体重新融入市场参与竞争,如何在新的社会规则之下摸索出有效的生存之道和自我成就之路?此前历史变局下的个人选择为此提供了可参照的答案: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个善于自我规训、自我成就的典型人物——天资普通的草根通过自我奋斗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曾国藩对于今人的实用性正在于此。
然而,曾氏身上的复杂性和丰富内涵又绝不止于此,我们无法以当代命题来简化曾氏脸谱的真实复杂性。在晚清的动荡变局之下,曾国藩夹身于地方与中央、清政府与西方强国、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博弈与缠斗。作为跻身权力高峰的少数人之一,他接触了一个国家在方向上敞开的可能性,又身处具体政治斗争的困局之中,试图在传统儒家意识形态的底线之内调和多种现实因素。对于这样一个精神构造的人物而言,他的每一个选择都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或是“怎么做都错”的实践。
无疑,曾国藩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的为人、做事及政治、军事战略是丰富的,而他对待中西文化、国际格局的评判亦极具代表性。从晚清到民国,曾国藩的形象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在清政府的眼中,他是可靠又要提防的助手;在门生幕僚看来,他是人生的精神楷模;南京百姓视他为可恶的“曾剃头”;保守派推崇他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革命党人斥责他为汉奸;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曾国藩的形象又沦为了政治武器……
同僚眼中:令人信服的大先生
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叙述中,李鸿章平生最信服曾文正公,开口必称“我老师”,简直是奉若神明。然而这位学生对于老师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他曾轻视曾国藩的才能。早年,李鸿章认为老师虽然在学术和为人上的造诣极深,却是一个有点迂腐的端谨长者,优柔寡断,并不适合干实事,更不会治军打仗。
曾国藩曾力荐李鸿章组建淮军、驰援上海,担任江苏巡抚。从学生、下属到同僚,相处的时间越久,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崇敬之情越深。李鸿章晚年对后人说,现在所谓的大人物、大先生都是饭桶,我一个都瞧不上,只有我的老师曾文正公才是真正的大先生。
虽同为“中兴四大名臣”,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情感更为复杂。在外人看来,曾国藩于左宗棠有知遇之恩。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左宗棠对他应该自称晚生。但左宗棠却认为自己只比曾国藩小一岁,在各种场合只肯以兄弟相称,不愿示弱。曾国藩常自称“愚钝”,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的才干不及自己,总是瞧不起他,甚至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
曾、左二人彻底决裂于1864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南京之时。然而两人的私人恩怨没有影响到国家公事。左宗棠虽在人前指摘曾国藩,暗地里也佩服他公私分明。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战场的左宗棠派人送来挽联,称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己惭愧比不上曾公。在落款中更是出人意料地署名“晚生左宗棠”。左宗棠也很照顾曾家后人,他在信中写道,自己与曾国藩仅是政见上的不和,并非争权夺势,心术不正的人妄加评议之词,何不一笑置之?
曾国藩去世后,曾国藩的门生和幕僚对其推崇备至,而保守派和改良派人士把他尊为士大夫的理想模范,甚至为其歌功颂德。这在晚清最后几十年里逐渐达到顶峰。薛福成是“曾门四弟子”之一,也当过曾国藩的幕僚,他评价曾国藩“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进而歌功颂德,认为曾国藩在“建树宏阔”上超过了蜀汉的诸葛亮,在“步履诸艰”上超过了唐代的陆贽,在“百战勋劳、饱阅世故”上超过了北宋的司马光。
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留美学生容闳也曾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在他的建议下设立了第一个兵工学校,推动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诞生。容闳评价曾国藩道,“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都远远超过同辈,就好比珠穆朗玛峰独耸于喜马拉雅山诸峰之上。在评价曾国藩的军事作为时,先后出任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幕僚的王定安在《湘军记》中称曾氏“武功之隆、近古罕至”。
辛亥革命后,从楷模到“卖国贼”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章太炎的这句描摹,大致可以刻画民国时期曾国藩形象的鲜明对立。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曾国藩“士大夫楷模”的形象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和“汉奸”。时人谓“清末士人,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盗贼,以神圣颂洪、杨”,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平定洪秀全、杨秀英领导的太平天国。时境变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自视为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这样曾国藩、左宗棠就被置于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成为人人喊打的“反动派”。
对于很多革命党人而言,曾国藩不仅是旧社会的卫道士,更是“扶满抑汉”的历史罪人。写过《猛回头》、《警世钟》的革命人士陈天华就痛批自己的老乡:曾国藩“为数千年的腐败学说所误,不晓得有本族、异族之分”。在当时的很多革命人士看来,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反满革命,推翻异族统治的强烈愿望与废除帝制的政治变革交融在一起。这样,曾国藩不只是维护封建帝制,还是满族欺压汉人的帮凶。
民国初年的章太炎极力排满,他痛加非斥曾国藩的道德功勋,称其志向不过是贪图富贵,“封彻侯,图紫光”。当时距离曾国藩离世已有三十余年,章太炎认为他的后人都会以他为耻,即使悲痛哀叹,也改变不了这样“吾祖民贼”的事实。
排满革命党人如此贬毁曾国藩,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论战对象是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和保守派。然而“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却越发让梁启超敬仰崇拜。在曾国藩的身上,梁启超发现了中国古代“内圣外王”的传统路径,他认为品格的修养不仅是自我实现,更是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良方。曾国藩少年时期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曾国藩视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的自制力,与后来成功歼灭盘踞南京数十年的太平军密不可分。“制之有节,行之有恒”不只是私域之事,也关乎民族复兴这样的大事业。
1914年,袁世凯已经沉心于恢复帝制,他想借清史馆延揽前朝遗老、争取获得反共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于是汉军正蓝旗人赵尔巽受聘出任清史馆馆长,主持《清史稿》的编纂。在这部凝聚着赵尔巽对前朝眷恋之情的《清史稿》中,曾国藩的形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在他的笔下,曾国藩已经化身为至贤至圣的完人了。
三十年代的“曾国藩热”意识形态之争
等到20世纪30年代,一股“曾国藩热”在不经意间悄然兴起。毛泽东曾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但此时,曾国藩这样的中兴名臣主要是国民党治军、训政的精神楷模。当时,国民党政权正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
蒋介石自谓“平生只服曾文正公”,他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曾文正公全集》。“文能应试,武能上阵”是他心目中的完美领袖形象。为了效仿曾国藩的治军之策,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要求其部下学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蒋介石也多次参照过曾国藩的策略。在第四次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就参照了曾国藩当年的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策略。曾国藩赠予部下腰刀,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也会奖励“中正剑”来获得部下对自己的忠诚。曾国藩开始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各种书刊中充斥着曾文正公的事功、言论和思想。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希望借助儒家的“四维八德”进行社会道德和价值的重塑。国民党政要对于圣贤的推崇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响应,大量的曾国藩书籍著作出版,评价曾国藩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挽救民族存亡的关键人物。
徐凌霄、徐一士在《曾胡坛荟》中认为曾国藩早年敢于直谏咸丰皇帝的过错,有古代大臣的“伉直之风”。如果明朝的“一君一相”是朱元璋和张居正,那么清朝就应首推康熙和曾国藩;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认为曾国藩“发先圣先王之义蕴”,“革新守旧同时进行”在人格修为和道德上都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一般汉学家、理学家或文学家可以比拟的。后来他的战功赫赫,关心民间疾苦,兼具了圣人和王道的双重资格,被称为“圣相”当之无愧。
这场文化保守主义的狂风还想为曾国藩“扶满抑汉”的问题翻案。王德亮专门写了一部《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为之辩解。该书认为,曾国藩所歼灭的太平天国运动信奉改造过的基督教,是外来文化的产物,而湘军则是为保卫中国传统文化而战。
王德亮更进一步直接把蒋介石比作曾国藩:“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事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力图自立自强,践履笃实,以诚为一世倡。”国民党如同湘军,是中华文化的捍卫者,抵御入侵的外来文化。这场论战背后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昭然若揭。
显而易见的是,民国时期的曾国藩不受左派学者的待见。1943年7月,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明确表明了对于曾国藩的批判态度。陈文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划分为两个敌对的阵线,一是以太平天国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传统”,一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反革命传统”,曾国藩喻指着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左派学界对于曾国藩的批判在1944年达到了高潮,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借曾国藩讽刺蒋介石,在各解放区的新华书店再版不下十次之多,被时人称作“理解古代和现代中国政治的一柄钥匙”。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场“曾国藩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愈演愈烈,“圣人”还是“卖国贼”的两极化站队主导了讨论,而这位晚清中兴重臣的本来面目也越来越模糊。可以说,曾国藩收获如此矛盾的历史评价,近乎必然,因为这关乎中国近代抉择的核心命题——站在决定性的风口,选择不同现代性立场的人必然对他持有不同态度,乃至发生激烈冲突。不论吹捧、认同或是否定、批驳,对待曾氏脸谱的态度只有置于历史情景之内才能被充分理解。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