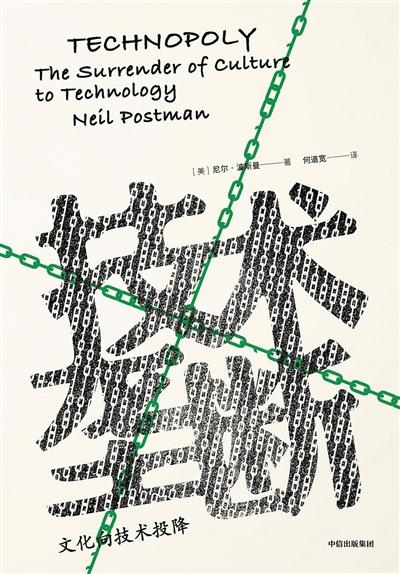
《技术垄断》
作者:(美)尼尔·波斯曼
译者:何道宽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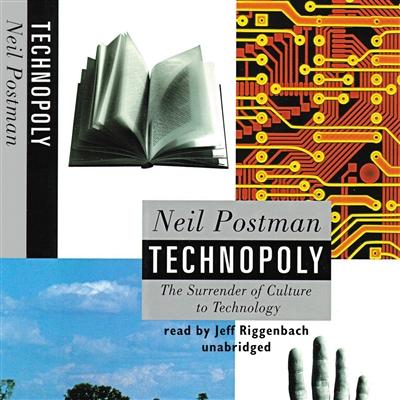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存世著作共25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尼尔·波斯曼的几部重要作品虽说都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但读他的书,人们的一种典型的反应是“波斯曼是时代的先知”。至今依然年销14万册的《娱乐至死》,无疑是波斯曼最成功的作品。它的一个令人过目不忘之处,在于它朗朗上口、预言式的口号: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娱乐至死”,这个书名就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将会毁掉我们的东西,最初在波斯曼看来是电视,但如今,说是智能手机、互联网也毫不违和。所以问题不在于电视,而在于更加宏观的人类技术状况——这一状况,被波斯曼称为“技术垄断”(technopoly)。人把一切价值都交给技术去决定,信息爆炸造成了普遍无知——这是波斯曼对于技术垄断后果的批评。
怎样的技术,创造怎样的人?
不过,一味地赞美波斯曼是一位“先知”,并不成为有创见地解读《技术垄断》的方式。毕竟《技术垄断》首次出版距今已经20多年。这段时间里,时代向我们展现了新的境况。它们不可能都能天衣无缝地套入《技术垄断》的论述。《技术垄断》与现今的社会生态之间的龃龉,恰恰体现出很多有趣的事。
“技术决定论”是很多读者谈及波斯曼时,常常会联系到的一个词。不过,关于“波斯曼的理论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这样的争议并没有价值。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本身已经过时了。一些人觉得技术的决定作用大,另一些人认为技术终归是由人的政治、社会因素来控制的(这是知识社会学、社会构建主义常有的立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争来争去,豆腐一碗、一碗豆腐,最后妥协说“技术和社会互相决定着”,等于没说。
问题的出路其实就在《技术垄断》中,这就是“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媒介生态学——如今我们需要从波斯曼思想中打捞的部分。
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造成震动。其背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于环境外部性的发现,是社会科学总体学术的生态学转向。举几个简单例子: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1960年创立社会生态学项目;城市生态学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建筑和城规的一个热词;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R.沃尔夫(Eric R. Wolf)在1972年提出“政治生态学”概念……
同时代,传播学和媒介批评也经历了生态学转向。媒介生态学本身,是由麦克卢汉于1964年构想的。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对媒介生态学的含义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如果把一种新的毛毛虫投入一个树林,你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树林+毛毛虫”,而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同理,如果你让全美国都看上电视,产生的社会不简单是“美国+电视”,而是被电视深刻改变的美国社会。
生态学范式的意义在于,它跳脱了“从复杂系统中抽取少数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决定论思维窠臼——也就是跳脱了“从复杂历史环境中,抽出文化和技术两个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思想窠臼。生态学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隐喻,生态学中一切互联,没有外部性。
《技术垄断》本身并没有完成媒介批评的生态学转向。它则是“技术决定论”和媒介生态学的混用。波斯曼最震撼人心的语句,往往依然是技术决定论的逻辑:呼吁人们警惕技术对一切意义和价值的垄断,警惕人文价值的失落。
但是,社会学研究不是文学写作,震撼人心不代表准确。波斯曼已经明白了“媒介生态学”的意义,但又无法放弃技术决定论和人文主义修辞的蛊惑人心的力量。波斯曼把我们的眼界带过了那个时代门槛,而他自己,却留在了那个门槛上。
波斯曼20年前的预言,与今天社会状况之间意味深长的相符与不符,恰恰说明了旧理论之外的新现实。下面举几个例子。
1 文化向技术“投降”了?
波斯曼从社会生态中抽取的“文化”要素,是不成立的。
20世纪初,大量技术乐观主义者——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相信,技术的进展终将带来富足,物质极大丰富,各种稀奇性问题、不平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技术不能消灭问题。新的技术只创造斗争的新领域,新的财富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
这种觉悟,不能推及文化:技术限制不了文化,技术会创造新的文化差异、新的文化动能。换句话说,文化不会像波斯曼预想的那样,完全被技术所控制,所“垄断”。
而且,波斯曼之后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新共识。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别有所图。文化的实质常常可以归于经济或政治。所谓“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地位、政治诉求、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别的东西。把“文化”和“技术”从社会生态中抽离出来并不现实。
就好比人们曾经期待ofo、滴滴打车、Airbnb会带来某种热爱分享、超越私有制、优化分配的“共享文化”。但当共享经济真实进入了社会生态,我们才能知道它们带来的文化冲击究竟是什么。比如小黄车的乱停乱放,引发的是针对城市空间的讨论;几次滴滴打车事故,让女性安全问题成为热议话题。
所以,紧盯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关系,往往是徒劳的。“文化向技术投降”之事,更是无从说起了。
2 在信息过剩中生存
“信息过剩”是《技术垄断》的一大关键批判,也是波斯曼从《娱乐至死》就开始关切的。谈到信息过剩的征候,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是这么说的:“(抵御信息过剩的)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会失去记忆力,也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
的确,当今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健忘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征候,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有多健忘。不过,足以令波斯曼惊叹的是他所谓的“垃圾场”上,已经成了一片新的生态领域。
从过剩的信息里面产生了巨大的产业,包括大数据、流量生意、注意力经济、区块链,等等。有企业家总结说:在这个时代,能够更清晰地组织数据,并用数据认识自己和外界,是个人、企业、国家的生存与成功之道。
技术打开了新的领域,人文科学应该做的,是去探索、占领这些新领域,确保固有的人文价值在新的领域得到延伸。反之,“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要慢下来等一等道德人心”,这种立场可谓是痴心妄想。
3 “异化”的经典批判,还成立吗?
异化,最简单说,就是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人性”流失。关于技术垄断的异化作用,说来道去,终归是说:技术或是信息过剩把人变成了傻子。
技术替代人去思考、判断、决策——这是波斯曼尤其感到警觉的事。比如书中他提到,人们会把医疗、生产事故归罪于“技术故障”,这就是人过于依赖技术,而失去了对自身的反思。问题的根源永远在人身上。
但是如今,异化批判的有效性确实发生了动摇。异化批判的人本主义基础被我们这个赛博时代动摇了。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号”空间站上的人工智能MOSS计算出地球的幸存几率为零,所以决定放弃地球。虽然最后电影中的刘培强等人超越AI,拯救了地球,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鲜明看出,人类在高技术时代一定会遭遇自己的生物能力极限。
这就是后人文主义的状况。没错,“人自身的发展”或云“人的进步”,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价值,也是从伊拉斯谟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波斯曼,都暗暗信奉的终极信条。只是,人类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发现人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异化”的批判力度显然会减弱。
一味相信波斯曼“准确预言了一切”,只会导致一种人文思想的惰性。因为波斯曼远没有预言到一切。甚至可以说,时代的快速前进,已经让波斯曼的技术批评思维到了不更新就会过时的地步。“让技术发展得慢一点”可谓是最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关于波斯曼的讨论最大的伪命题。让人文价值努力去跟上技术发展的快节奏,这才是人文思考积极的态度。
□袁子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