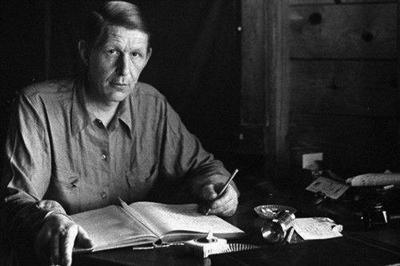
W.H.奥登(1907-1973)

翁贝托·埃科(1932-2016)

亨利·米勒(1891-1980)

雷蒙德·卡佛(1938-1988)

波拉尼奥(1953-2003)

阿摩司·奥兹(1939-2018)

奈保尔(1932-2018)

T.S.艾略特(1888-1965)

《最后的对话》
作者:(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奥斯瓦尔多·费拉里
译者:陈东飚
版本:新经典文化|新星出版社
201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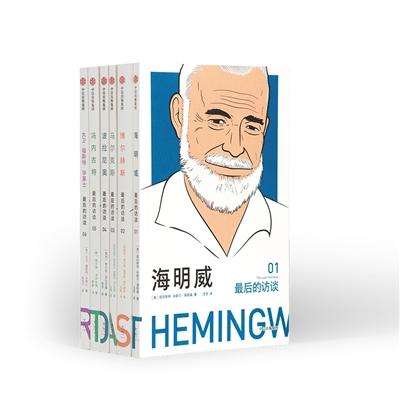
《最后的访谈》(6卷)
作者:海明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波拉尼奥、华莱士、冯内古特
译者:汤璐等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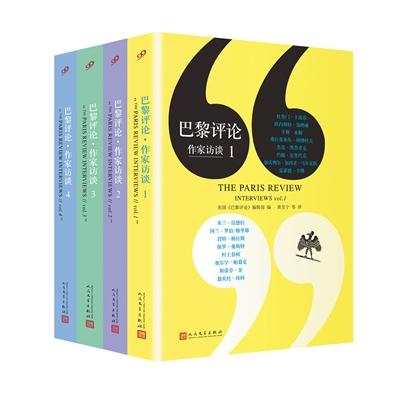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卷)
编者:《巴黎评论》编辑部
译者:黄昱宁等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有句名言:“从某种意义来说,诗的功效为零,因为从来没有一首诗歌能阻挡住坦克。”诚然,诗歌或曰文学从未能直接扭转一场战争、化解一场冲突或决定一种政治走向,但文学在守护人的精神世界、呼唤良知和道义,以及呈现纯粹的艺术之美上所做的贡献,却是任何一个政治或军事人物都不能比拟的。
那些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总是具备时代最睿智的头脑和最丰富敏感的心灵,他们洞察人性的幽微和时代的症候,常常如先知般振聋发聩;而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不仅是一种语言艺术,更是一种人性和时代的记录,它们比历史更细腻唯美,更透亮动人。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意文学家的声音,在意他们的浅吟低唱或嘹亮高歌。
本文从《最后的访谈》(6卷)、《巴黎评论:作家访谈》(4卷)、博尔赫斯《最后的对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中,辑录了近二十位已故作家的晚年谈话,他们都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者,在文学的万神殿中占有位置,这些声音反映出他们的个性和经历,以及他们对阅读、写作、爱情、政治、人性、死亡等问题的最终见解。
关于阅读
一种坠入情网的体验
阅读对我而言是一种不亚于周游世界或是坠入情网的体验,通过阅读贝克莱、萧伯纳或是爱默生的作品,我仿佛能亲眼看到伦敦。当然,透过狄更斯、切斯特顿和史蒂文森的作品,我也能看到伦敦。我总是先把自己看成读者,然后才是作者,后者或多或少都是无关紧要的。我是在父亲的藏书室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都知道,待在一屋子书中间,与书为伴,那就是我的命运。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悲伤的产物。文学对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留给我们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著作,还在于它催生了一种新型的人类,那就是文人。文学的概念是无边无际的,我自己对它都知之甚少,但我能教给你们的是爱,不是去爱我都无法掌握的文学,而是去爱某几个作家,那都有点太多了,爱某几本书,或许还有一些奇特的诗篇。——博尔赫斯
小说不需要与任何东西有关,它只带给写作它的人强烈的愉悦,给阅读那些经久不衰作品的人提供另一种愉悦,也为它自身的美丽而存在。它们发出光芒,虽然微弱,但经久不息。——雷蒙德·卡佛
当小说家读到其他小说家的作品时,他们会把这部作品一一拆解开来,就好像对待一部机器。在教你如何写小说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比阅读另一本小说来得更有效。
——马尔克斯
关于写作
永远坚守魔术的秘密
一旦写作成为你最大的恶习,同时也带来最多的愉悦,那就只有死亡才能阻止它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保障帮助会很大,因为它免去了你的种种担忧,担忧能够毁灭写作的能力。健康状况的糟糕程度和担忧的多少成正比,而担忧会攻击你的潜意识,破坏你的储备。
——海明威
失明以后,写作对我岂止是难,简直是不可能。我必须把文章控制在很短的篇幅内,因为我喜欢检查写好的东西,对于已经写好的部分没有什么把握。此前我在真正动笔前往往会先打很多份草稿,但现在没法使用纸笔了,只能在心中打腹稿,我常常一边在街上或是在国立图书馆里来回踱步,一边在心中构想写的东西,我尽可能的削减字数。我想在脑海中完整地过完所有构思好的部分,我为什么对长篇小说没有信心,原因就在这里。
——博尔赫斯
一名小说家必然要有求知若渴的精神。当你完成一部小说后,就应该把所有的草稿和笔记全部销毁,就像魔术师永远坚守着魔术的秘密,而作家亦是如此。
我热爱写作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写下去,我想我一直不停地在写,也是因为惧怕死亡,如果我就此停笔,那我很快就会死去。
——马尔克斯
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我对此非常确定。一连串的杀人案,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经过坟场,对视鬼魂。
20多岁的时候,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写诗,我想要的是活得像一个诗人。对我来说,身为一名诗人,意味着得是革命性的,一位彻底接纳各种文化和性的表达,最终愿意彻底接纳一切与毒品相关的经验。
——波拉尼奥
我的写作是间歇性的,当我写作时我一坐下来就会写上很久,十、十二或十五个小时,一天接一天,这种时候我总是很开心。可以理解,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修改和重写上面,我最喜欢把一篇写好的小说放上一段时间,然后把它重写一遍,写诗也一样。——雷蒙德·卡佛
十五六岁时,写诗像是一种自慰。但到晚年,优秀的诗人会焚毁他们早期的诗作,拙劣的诗人则把它们出版,幸好我很快放弃了写诗。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自己而写作的,我认为写作是一种爱的行为,你写作是为了付出某些东西给他人,和别人分享你的感受。作品能够流传多久,这个问题不仅对小说家或诗人,对每个写作者来说都是至为重要的。这好比你希望你的孩子继承你的血脉,如果你有孙儿,他就继承你的孩子的血脉,人们追求一种连续性。——翁贝托·埃科
只要考虑到连最简单的一个想法,都可以有一千种表达方式,那么作家感到压力也就情有可原了。作家非常在乎一件事情是如何被表述出来的,表达方式就是全部的差别所在。所以,他们不断地面对太多的选择,也不断地需要作出太多的取舍。
——E.B.怀特
写作是为了写就一本书,为了满足需求,为了谋生,为自己留下光辉的一笔,为了填补你眼中的缺憾,使其完整,我不为任何人代言,我也不认为会有任何人希望我来为其代言。——奈保尔
如果我一开始就能自立,如果我不需要操心赚钱,把时间全部都花在诗歌上,那很可能会扼杀我的写作生涯。对于我来说,参与一些其他的实践活动很有用,比如在银行工作,甚至是做出版。而且,就是因为抽不出很多时间来创作,反而会逼着我得在写作时更集中注意力。——T.S.艾略特
关于爱情
看到上帝眼中的对方
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不分大小,无论一个人何时坠入爱河,他爱上的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也许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当一个人落入情网时,他眼中的对方就是对方真实的样子,上帝怎么看这个人,他就是这么看的。——博尔赫斯
我努力不让爱情进入我的小说,因为一旦这种话题出现,几乎就不可能再谈别的了。读者不想听到别的事情,他们对爱情很狂热,如果小说中的恋人赢得了他的真爱,故事就结束了,哪怕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哪怕天空中全是黑压压的飞碟。——冯内古特
配偶双方在幽默感和人生观上的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我赞同歌德的意见,婚姻庆典理应进行得更安静、更低调些,因为婚姻是某种重要开端,该省点力气在喧闹的典礼上,多费些心神在今后的美满结果上。
——W.H.奥登
关于政治
无法割裂的权力纽带
我一直是左派,后来转向了托洛茨基派,但我同样不喜欢他们宗教般的全体一致,所以我最终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体一致总让我大为恼火。每当我意识到全世界都一致同意一件事的时候,每当我看到全世界都齐声咒骂一件事的时候,某种东西就会浮上我的皮肤表面,让我说出拒绝。
——波拉尼奥
我认为作家的政治角色受到每一刻社会背景的影响。当谈到政治工作时,作家喜欢做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我对于革命的观点就是,它是一种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寻求个体幸福的方式,而这也是唯一合理存在的幸福。我们要对拉美的殉教运动说不,革命的意义在于生,而非死。革命让全世界的人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喝更美味的红酒,开上更好的车辆,物质的富足不只属于资产阶级,那是我们人类共有的财富,只不过被资本家偷去了而已,我们要取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分配给每一个人。革命并不一定会带来死亡,革命也不是灾难的象征。如果革命会带来流血牺牲,那么这也是反对革命的人们所造成的。我们要明确的是灾难责任在谁,而正是之前的误解,让我们的母亲为此恐慌。
作为作家,我对权力感兴趣,因为在当中,你能找到人类所有的伟大和悲哀。我一直试图根本性地解决很多事情,而不是简单地签署抗议宣言。文学是不应该被当做枪械来使用的,而即便是有违你的意愿,你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会不可避免地在你的写作中反映出来,对读者造成影响。我认为,我的作品对拉丁美洲造成了政治影响,因为他们会有形成一种拉丁美洲的身份,他们会帮助拉丁美洲人对其自身的文化变得更有意识。
文学、电影、绘画、音乐对锻造拉丁美洲的身份都是必要的,我想要看到一个团结、自治、民主的拉丁美洲。文艺向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观服务的,但文艺绝不应该为某个政府服务,我们必须抗击石化的语言。我和政治领导人的友谊是最缺少政治因素的。——马尔克斯
我的写作和绘画都与政治发生着不同的联系。但我既不会去特意写一个简单的关于政治现实的故事,也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政治话题,政治本身就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决定性影响,它以不同方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认为政治应由政党去决定,那样会很危险。文学有改变世界的威力,艺术也是。文学所造成的改变是无法测量的。——君特·格拉斯
在我的国家,诗人总是和政治纠缠在一起。我不认为我的生活在诗歌与政治之间是割裂的。我是个智利人,几十年来,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各种不幸与艰难,了解智利人民的一颦一笑,我曾是其中一分子。对他们来说,我不是陌生人。我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我从未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勾结,我一直认为我的职业和我的责任,是用我的行动和我的诗歌为智利人民服务,我活着也是在为他们歌唱,守卫他们。
——巴勃罗·聂鲁达
作家很少能成为好的领导者,首先他们是独立自主惯了,他们与购书读者都很少联系。再者,对作家来说很容易就变得不切实际。我没有对政治丧失兴趣,但我开始认识到如果遭遇社会或政治的不公,只有两样事情有效:政治行动和直接报道此事。艺术在此无能为力。即便但丁、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莫扎特等人从未降生人世,欧洲的社会史和政治史该怎样就还是怎样。身为诗人只有一个政治责任,即通过他自身的写作来为它不断堕坏的母语,建立一个正确使用的典范,保持语言的神圣性正是诗人理应担当的角色。
——W.H.奥登
政治就是一个完全烂透了的、散发着恶臭的世界,我们从那儿什么也得不到,任何东西跟它沾边就变味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缺少一种真实感,而一个政治家首先得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想搞政治的人不能有太多教养,得有点杀人犯的素质,随时准备并且乐意看到人们被牺牲掉,被屠杀掉,仅仅为了一个或善良或邪恶的念头。——亨利·米勒
关于人性
一切矛盾和悖论的结合体
如果我足够勇敢,我对勇敢无畏可能就不那么重视了,人们总是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格外关注,比方说有个女人很爱你,你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甚至会对她产生厌恶;但如果你被抛弃了,你就会觉得天都塌了,不是吗?那些事情总会发生的,你最看重的往往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恰恰是你所没有的东西。
——博尔赫斯
男人和女人有截然相反的困难要去对付,对男性来说,困难在于要避免变成一个唯美主义者,避免那种不去追求真实、只关注诗意效果的言说。而女性的困难是如何与情感保持足够的距离,她们都不是唯美主义者,也不曾写过打油诗。如果你讲了个有趣的故事,只有女人才会问:“它真的发生过?”我揣想,倘若男人们知道女人们相互之间是怎么议论他们的话,人类都有可能会灭绝。——W.H.奥登
名气对我的个人生活来说是一场灾难,就好像你可以通过周围众多的人群来感知自身的孤独一样,围绕的人群越多,那种渺小感就越发强烈。——马尔克斯
我不想出名,我不喜欢公众关注,我对生活仅有的要求只是写作、打猎、钓鱼,以及隐姓埋名,名望让我郁闷难受,问题让我饱受折磨。——海明威
我发现家庭是最为神秘的机构,最不可靠,最为悖论,最为矛盾。多少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听说关于家庭之死的预言,并看到了家庭如何在宗教、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历史变迁中生存下来,看到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以及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理念使我们认识到世界上的许多冲突,可以在家庭关系中体现出来:爱与恨、嫉妒与团结一致、幸福与神秘的永恒交替。
在家庭中,每个人都与他人之间具有冲突,每个人都是正确的,就像在拉比与山羊的故事中一样:儿子是正确的,因为父亲专横残暴;父亲是正确的,因为儿子懒惰无礼;母亲是正确的,因为父子如出一辙,堪称绝配;女人是正确的,她无法忍受家里的气氛,离家出走。然而他们都爱着对方,因此我有时通过家庭视角看到国际冲突。——阿摩司·奥兹
关于死亡
一场久候多时的赴约
我不认为死亡有多可怕。尽管人难逃“凡人必有一死”的宿命,但当死亡那天来临时,他仍可以借助人生不过是一场梦这一事实从容离去。死亡意味着你将不再存在,不再有思想或是感觉,不再有求知欲,但幸运的是你也不用再烦恼了。也许你还会有烦恼,就像那位拉丁诗人所说的,为死后等待你的不知是什么样的日子而烦恼。想象死亡没有任何难度,就好比我每天晚上都要睡觉一样,它就像是我最后的长眠。——博尔赫斯
我们是唯一知道自己必定会死的动物,别的动物不知道,它们只在当场、死去的那一刻才理解死,它们不可能明白地表述出“人终将一死”之类的说法,我们可以,这可能是我们有宗教、祭祀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原因,我觉得喜剧是人类对恐惧死亡作出的典型反应。
——翁贝托·埃科
如果不想到死亡,我就不会充满陶醉的享受人生的乐趣。我想到过死亡,但是我更多地想到死者,想到死者便是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因为那些死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存在于我的渴望中,存在于我重构以往瞬间的能力中……我宁愿死亡再过50年才来,我热爱生活,极其享受生活,我的生活由死者和生者共同构成。如果死亡今夜来临,他只会发现我愤怒而不情愿,但并非没有准备。——阿摩司·奥兹
撰文/整理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