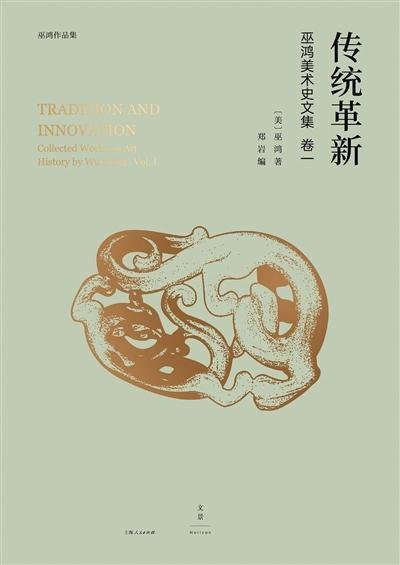
《传统革新》(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一,另有卷二《超越大限》)
董牧孜 擅于格猫致知。
出于采访的缘故,急来抱佛脚读巫鸿。最新出版的《巫鸿美术史文集》是编年体,从早年写古代美术史的论文和讲稿开始,看他往后的研究怎么开枝散叶。巫鸿也太能写,从古搞到今。书的话题从黄泉下、古墓中,跑到了屏风前、废墟里,又在东村与三峡同当代艺术家一同玩耍。总是多任务操作,不同课题研究彼此交叉。好像学术写作是像吃饭喝水一样的事情。
巫鸿早年在故宫干过活,是“文革”后最早一批的艺术史留学生,有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的训练。这种处身交叠和断裂处的历史位置,也算时代幸运儿。
我对于他最直观的印象是,保养很好,皮肤很好。听说他的迷妹很多。巫鸿曾是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学生,也是今天西方学界认可度高的中国学者。作为大佬自然也有争议,最著名的一桩公案是西方学者贝格利对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的差评,李零、田晓菲等学者都参战,堪称一场学术上的“科索沃战争”(李零语)。这场辩论有点好玩,体现出不同艺术研究背后的不同史学观念。
对于美术史,我是非专业读者。但翻书党有乱翻书的读法。写论文时养成读书较“专”的习惯,做记者时又改作看书较“杂”——都是为了写,也就都带点功利意思。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爱看别人怎么写,他们的脉络是什么,再想象拙劣如我的写手还能怎么处理——就连读余秋雨时也这么想。假如把我丢到亚欧落寞古文明的国家去写《千年一叹》,每天交稿一篇,需要哪种知识结构和信息储备?该怎么组织起我的情感与惊叹?想想就苦恼。
既写古代又写现当代,巫鸿的写作谱系如此,活动谱系也这样,还搞了很多策展和艺术家个案研究。当然,这不能算是罕见。艺术家朋友说,“搞中古历史研究,再插一杠子当代艺术”是个流行的模式,意大利的奥利瓦,德国的于贝尔曼,还有一些国内学者都这么干。
读巫鸿写中国古代美术,让我感到极大的轻松与快乐。庙、墓、玉器、佛教美术、敦煌洞窟、石棺乃至五岳等,考古部分也没什么距离感——我当然无法从专业上做优劣判断,但大致理解自己读感上的亲近。一方面,他写的东西有对话、沟通的欲望,读者意识强;另一方面,大概来自方法论上的熟悉,似乎是在看中国古代事物自身与西方理论变换体位的左右互搏。
用一个读艺术理论的朋友的话说,他“摘概念非常巧,书名也起得好”,比如《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西合璧弄得漂漂亮亮。他能巧妙把玩概念的游戏感,将中西研究对象与方法论框架摆盘对照,模糊古代与当代的边界——当然,要带着问题意识与足够的警惕去这么做。
巫鸿自己这么说,古代与现代之间,对他来说不存在思想和写作上的转换困难,只有研究材料、目的和方法的区别。随便举例,就说《废墟的故事》。中国虽然有凭吊怀古诗,但建筑和图像之中并没有西方那样的废墟美学——西方浪漫主义看待废墟的传统,后来成为流行的美学态度。要怎么把中国(非西方视觉传统)的废墟,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肯定要带着对西方历史经验是否有普遍性的反思,还要探索中国古代艺术自身的特殊形态和历史逻辑。进入现代语境就好说些,我们有圆明园这样的战争废墟,还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建设下的城市废墟,当代艺术家很热衷这些。于是《废墟的故事》就有了当下的面貌,第一章是古代艺术,后两章是现当代,用“过去与未来之间”做个总结——熟悉亲切的汉娜·阿伦特出现了(借用她的著作)。假如我还要从事论文生产,这种写作思路具有绝对的可模仿性。
读巫鸿时,突然再次意识到自己跟传统中国知识体系的距离感,似乎总要借助西方理论的中介,来更接近中国自身的传统。全球化时代接受教育的文科学生,大概多有如此的窘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