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时期的翁达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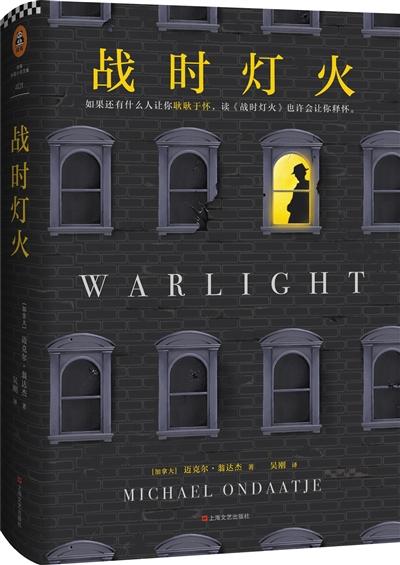
《战时灯火》
作者:(加)迈克尔·翁达杰 译者:吴刚
版本:读客|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7月
《战时灯火》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最新的长篇小说。他素来有着诗歌与小说全才的称号。作家与作品如果对上了“韵脚”,会彼此成全。这一次,翁达杰在诗歌和小说上的双重才能尽显在了《战时灯火》中——他将一个本该紧绷激烈的关于战争年代的故事写得辗转舒缓,隽永深沉。
镜头转向1945年的伦敦,14岁少年纳撒尼尔的父母突然离开,把他和姐姐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从此身边来来回回出现了许多神秘人物。十多年后,31岁的纳撒尼尔依然对母亲的离开耿耿于怀,于是开始搜集线索,寻找真相……这样如侦探小说般的离奇情节,却在翁达杰的笔下,染有了诗意又温暖的色调。诗性潜入了戏剧冲突,它们看似在交锋,实则构成了互文的空间,朴素又多面的人性在这空间中慢慢显现。
谜底的诱惑
人生谜团也许终不可解
《战时灯火》的情节设定,有着典型的悬疑小说气质。但悬疑小说的弊病通常在于,情节的推进倚靠在对于谜底的探究之上,我们往往急不可耐地关注谜底究竟是什么,而一旦谜底揭开,小说便也达成了使命。但左手诗歌、右手小说的翁达杰,却完全打乱了这种节奏。他的文字在平易中蕴藉着节制的美感和诗性,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他的布景。一脚踏入之后才会渐渐惊觉,这居然是个关于战争和情报工作的故事。难得的是,扑朔迷离、悬念迭起、错综复杂,这些特质并没有消失在翁达杰诗性的叙述之下,反而因为他波澜不惊的格调,拨云见日地将我们的视线引向情节之外的深层意蕴——那是关于自由和宿命的命题。
翁达杰干净利落地将小说分为两卷,看起来很符合悬疑小说的路径——第一卷,陷入谜团:“我”14岁那年,和姐姐一起开始陷入父母离开后迷雾重重的生活;第二卷,解谜:当“我”知道母亲是一名情报工作人员之时起,一切记忆的碎片和生活的蛛丝马迹都开始聚拢,拼凑起“我”心心念念的真相,那些曾经照看“我”和姐姐的古怪的人的身份,也被一一解开……但翁达杰并不对谜底痴迷。陷入谜团和解谜的过程,显然是更能凸显他创作意图的戏份。甚至,翁达杰将谜底也留在了质疑的追光之中——“我”的发现被不断推翻和重审,真相真的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可靠和唯一吗?
翁达杰曾经在与石黑一雄的对话中谈道:“我从来不愿意写一部结局完满的小说。在结尾处我总要留一扇门。我的故事里有角色消失了25页以后忽然又回来了,但他们并不需要解释之前去哪儿了。”
《战时灯火》在结构上的断然利落只是表面性的,翁达杰不会只满足于所谓的条理清晰。正如小说中翁达杰借“我”的口说道:“我们宛如置身于一颗战争年代的时间胶囊,灯火管制和宵禁依然在实施,周遭能看到的只有战时灯火,驳船只有熄灭了所有的灯火才能允许在这片河面上航行。”
此刻,作者和叙述者的身份合二为一,提醒着我们,这本在结构上看起来井然有序的小说,实际上一直在关注时间的碎片化,时间的维度一再被重置。叙述上的跳跃、闪回,不断地模糊着“我”的想象与回忆的边界,但作者的这种“混淆”的意图又并不明显,仿佛我们的记忆本就是这个样子——充满盲点和混乱。当我们在对故事的信任和怀疑间被不断推来推去时,因为诗性和戏剧性交错而生的张力,便成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
从谜面到谜底,直至意识到人生谜团也许终不可解,《战时灯火》由表及里地同构出了命运的起落和无奈。
凡人之歌
不可思议又令人动容
翁达杰的反转能力,不仅体现在让小说在诗性和戏剧性的交融中获得张力,更在于他能将离奇的故事和遥不可及的人物拉到我们的身边。他在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摹上,天赋出众,所以,即使他取景的时代背景和讲述的事件并不寻常,却依然能让人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我们对第一卷中的种种悬念念念不忘,对第二卷中的解密兴致勃勃。
这才是《战时灯火》最致命的诱人之处。小说说到底,是关于普通人的艺术。无论情节多么离奇,甚至玄幻,如果它不能抵达普通人的内心,显露出日常生活的肌理和质感,那么就无法真的打动人。翁达杰用一个离奇的故事,平静地沉潜入日常,这就是为何他的小说会吸引人,会让人陷落的缘故。
在母亲突然消失的岁月里,“我”在假期里去标准剧院打工,多年后依然记得那些日日夜夜,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男孩青春岁月中的春日碎片”,“是男孩唯一孤独的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我”遇到了女孩艾格尼斯,她的世界“是‘我’此刻孤身逃往的世界”;在跟随看管“我”和姐姐的“镖手”“跑河上”的那段日子里,虽然流离不知前途,“我”却饶有兴致地得窥“镖手”那混沌朦胧的生活时间表……就这样,在茫然未知又险阻重重的命途里,“我”和姐姐的生活依然充满活生生的细节。
生活永远在继续。至于小说的核心谜团——母亲为什么会选择离开“我们”去做情报工作人员,翁达杰给出的理由看似古怪却引人沉思:因为重遇了已经身为谍报人员的童年密友,母亲发现了那个能点燃她热情的神秘世界,“因为她所想要的,是一个自己能够充分参与其中的世界,哪怕这意味着会令她得不到完全的、安全的爱。”以这个理由投身危险离奇的情报工作,荒诞但流露出平凡的感人气息。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一名记者在德国街头采访来往的路人:“每天无尽的轰炸和死亡,你是如何熬过了战争,熬到明天?”其中有人答道:“因为明天还有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不可思议又让人动容。
宿命之上
“困厄的人生”被消解救赎
将看起来重要的事件和不重要的细节并置,一种恒长而宽阔的生命感会蔓延开来。小说中,一边是惨烈的战争,一边是如常的生活;一边是生死的较量,一边是小儿女的内心纠结……这些对比一旦被推向极致,关于战争、关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便会不请自来。
作为小说家的翁达杰,高明之处是将这些命理捏碎了分散在他小说的纹理之中。我们于是时而跟随“我”一起经历种种迷糊又布满危机的日子,时而又被搁置一旁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审视这些过往的岁月,仿佛要逃离叙述者“我”热情的控制。这种流转和切换,使得小说虽然到处是乱麻一般的问号,却葆有了一种秩序和淡定。人生的状态本就是这样充满问号和未知的吧,所以焦虑何用?小说中几次出现“困厄”(schwer)一词——“生活就是困厄”,但“我”并未从悲苦的角度去理解它,是的,时事艰难,“可我对于那些沉重的或是难以消化的东西总是回避加忽略。非法的世界令我感到更多的是神奇,而不是危险”。“困厄的人生”就这样被消解,获得了救赎。
不断并置,继而不断消解。灾难与痛苦,残酷与未知,都在翁达杰的笔下变得举重若轻。因为他的诗性背后是对人情的通达和对人世的悲悯。所以,尽管小说始终在表达现实的飘忽不定,及至最后一刻都在揭示我们心心念念的蓄意探索终究难逃落空的宿命,但是他设置了一项明白无误的结论:母亲虽然突然离开去投身她的神秘事业,却并没有抛弃“我们”。来照看“我”和姐姐的那些古怪的人,以及在“我们”身边出现过的许多人,都与母亲有关,他们是来保护“我们”免受伤害的。尽管小说的格调并不抒情,但是,这种温暖的光晕统摄了小说,令其在情节和风格上获得了平衡。
由此,人性的美好和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可能,成了这部小说自主性的要素之一,《战时灯火》的意象和隐喻意义也因此被延展,被繁衍。在战争和灾难面前,人既渺小又伟大,渺小到可以命途如尘埃,也伟大到可以坚不可摧、淡定自如地面对所有的困厄。但这样的气度和理想化同时也会令《战时灯火》在直面现实的力量上有所折损。小说总爱将读者留在光明里,好吧,这是弊端,也是希望。
翁达杰设定了一个不合宜的战争情境,来安放亲情、爱情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言喻的关系,但正是这个“不合宜”,赋予了我们以新的体验维度。他在小说中写道,“你自己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是的,《战时灯火》展露出的对于人生际遇的种种“古怪”看法和处理方式,让我们对生命的无限可能有了更宽幅的理解力。正如小说的封面上所写:“如果还有什么人让你耿耿于怀,读《战时灯火》也许会让你释怀。”
我们都不过是隶属于命运的更庞大的情节而已,所以,还有什么不能释怀?
“没有任何东西随着过去而被带走,没有任何伤口随着时间而得到愈合,这里的时间一切都是当下的,没有结束的,充满怨恨的,一切都是相连着共时存在的。” ——翁达杰《战时灯火》
□来颖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