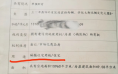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发光的小说》
作者:(乌拉圭)马里奥·莱夫雷罗 译者:施杰
版本:大鱼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在小说《科幻精神》中,罗贝托·波拉尼奥创造了一个怀揣作家梦的角色扬,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一部作品,但坚信自己会在未来成为一名“拉丁美洲科幻小说家”。这部小说出版于2016年,其时作者波拉尼奥已逝世多年,他自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二年,一位如扬一般喜爱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的乌拉圭作家也会驾鹤西去,更不会想到他也会和自己一样,公认的巅峰之作在去世之后才会出版。这位作家叫马里奥·莱夫雷罗,而他的巅峰之作就是新近译成中文的《发光的小说》。
拉美文学传统 模糊的文体界限
《发光的小说》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奖金日记”和“发光的小说”。2000年,马里奥·莱夫雷罗获得了古根海姆奖金,使他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专心致力于创作名为《发光的小说》的作品,出版后的《发光的小说》中的第二部分即为该作品正文,而奖金日记部分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从2000年8月到2001年8月这一年时光中作家的生活点滴。值得注意的是,按中译本页数来看,原本应为小说主体的第二部分仅有一百页出头的篇幅,而奖金日记部分则长达四百余页,并且无论是日记部分还是“正文”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叙述,这使得读者不禁心生疑惑:究竟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构?这究竟是一本小说,还是一本日记?首先,这种文体上的模糊性源自莱夫雷罗的刻意为之,莱夫雷罗一生创作长篇小说12部,短篇小说十余部,在最后创作的几本长篇小说中,他都刻意追求一种将散文、小说、回忆录等形式融合到一起的独特文体;其次,模糊的文体概念也恰恰是拉美小说的传统特点之一。
我们回到1939年10月12日,美国诗人阿尔奇巴德·麦克利希在《国会图书馆西班牙室揭幕献词》中讲述了他在巴黎的一家图书馆中偶然发现贝尔纳尔·迪亚斯所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1552)的经过,他认为正是这本书让他仿佛第一次真正领略了“美洲的经历”,因为“它不可能属于其他人;这是所有不管说哪种语言的真正美洲人的经历”。
《信史》一书写的是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的全过程。然而与传统的历史著作不同的是,作者进行叙述时使用的是“我”和“我们”的亲历者视角,在讲述征服战争的同时,还穿插记录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和印第安神话传说,每个兵丁都有血有肉,他们的生活和战斗被描写得细致入微,甚至连每一匹名马的名字和毛色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使得我们对拉丁美洲小说的界定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上文提及的模糊性。恰如我们无法确定《信使》是历史还是小说一样,我们也无法断言福·萨米恩托的《法昆多》和达·库尼亚的《腹地》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或地理著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会有人认为博尔赫斯笔下记录着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英美百科全书》真实存在,而波拉尼奥所撰的《美洲纳粹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史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发光的小说》无疑是拉美小说传统的一种延续,然而这部作品最大的“发光点”并不在此,而在于对拉美小说诸多其他传统的彻底颠覆。
莱夫雷罗 倡导极致自由的写作观
殖民时期,仿佛是意识到了小说的潜在威胁,宗主国西班牙严禁文学性散文和小说在美洲殖民地流通,因此拉美小说家们用了近三百年才写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作品,即出版于1816年的流浪汉小说《癞皮鹦鹉》。在先锋派作家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之上,拉美小说终于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大放异彩,出现了“文学爆炸”,拉美小说愈发体现出了介入现实的特点,作家们也始终希望以文学来改变拉美各国的命运。
莱夫雷罗在1968年出版了自己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又在1970年出版了首部长篇小说,这些时间点与“文学爆炸”的高潮期完全吻合,然而莱夫雷罗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道路。他不热衷与知名作家建立私交,终其一生也只是在乌拉圭、阿根廷等国生活。他只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与拉美介入文学传统背道而驰。
莱夫雷罗作品的英译者安妮·麦克德莫特曾经说过:“乌拉圭盛产怪咖。莱夫雷罗就是这么一个怪咖,而且是级别最高的一位”。持此观点的不止安妮一人,在1966年,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安赫尔·拉玛就曾经出版《百年怪咖》一书,介绍了15位乌拉圭怪咖作家。
这些怪咖作家不在乎创立文学流派,也没有众多的追随者,他们坚持为自己而写作。与“文学爆炸”代表作家们的群体化写作相比,莱夫雷罗进行的是截然相反的个体化写作。他倡导创作的极致自由,认为作家只有在对作品进行修改时才应该考虑技巧问题,而在写作时则应任由想象力自由飞驰,因此我们在《发光的小说》中看到的是他对作家/主人公琐碎的生活细节、梦境、思考的全方位记录。
莱夫雷罗当过摄影师,还做过漫画脚本作家,也许是受此影响,他在多场访谈中都曾提及“图像”的概念。他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图像”,而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秘密就在于由一幅幅“图像”结合而构成的情节。莱夫雷罗同时指出“图像”并非单纯的描写,它与行动并无矛盾,例如照片不算“图像”,而镜中的自己则算,它是丰满可变的。可以说,“图像”是莱夫雷罗文学世界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他对拉美文学传统的又一次反叛。他认为“图像”在拉美文学中是缺席的,因为拉美文学更关注修辞、善恶、情感和世界观,而这些元素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并无太大意义,甚至会造成民族文学的退化。莱夫雷罗曾举例阐述“图像”的内涵,他指出,任何一个读者都不会忘记费·埃尔南德斯笔下那将吸管插入小孔吸食马黛茶的老妇的形象。读毕《发光的小说》,读者脑海中也一定会浮现出那个或坐在电脑前,或吃着灵儿带来的美食,或在书摊挑选图书的老头的形象,这是属于莱夫雷罗的文学“图像”的胜利。
作为特立独行的怪咖,莱夫雷罗的作品在被读者阅读和接受的过程中很容易落入两种极端的境况:爱者愈爱,恶者愈恶。可莱夫雷罗对此并不在意,他说:“当作家并不意味着写的东西有多好,有的作家写得很烂,例如罗贝托·阿尔特,有的作家使用的语言缺乏文学性,例如卡夫卡,但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因为他们一生都在通过写作为自己的内心‘驱魔’。”
莱夫雷罗提到的卡夫卡是他最为推崇的作家,有趣的是两人的文学之路也有相似之处:作为作家,他们在生前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声誉。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他在世时读者无法接受,而在他去世二十或三十年后,欧洲终于变成了他笔下世界的样子。莱夫雷罗的作品曾经鲜有读者,而如今不仅如《发光的小说》等作品有了外文译本,连塞萨尔·艾拉、亚历杭德罗·桑布拉这样的热门作家也纷纷坦承受到了莱夫雷罗作品的影响,如此看来,莱夫雷罗也和卡夫卡一样,是属于未来的作家,而他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现在。
□侯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