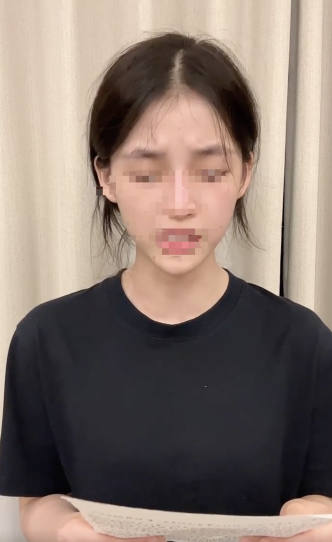在我看来好的小说家有三类,第一类是他写他的世界,比如左拉,第二类是他写什么什么就变成他的世界,比如博尔赫斯,第三类是他写他的世界,但他写什么什么也就变成他的世界,比如福楼拜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洛林作家尼古拉·马修可以算是第一类作家,他写出了一个被人忽视的洛林。

得主尼古拉·马修(图片来源:法新社)
地处法国东北的洛林算不上文学重镇,在今年之前法国文学最高奖项龚古尔文学奖的得主里只有三位来自洛林,今年的尼古拉·马修则是第四位获此殊荣的洛林作家。马修的这本小说《及其子孙后代》足有400多页,阅读的时候不止一次让我想起《铁西区》这部纪录片,漫长的阅读/观看过程与其中反映的“无聊”的生活状态颇为贴合。洛林也是法国的老工业区,小说中的虚构城市埃朗日(Heillange)位于河谷工业区,旧日的烟囱依旧高耸,但已沦入死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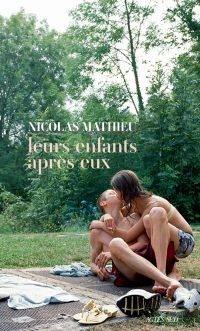
《及其后代子孙》法语原版封面。
马修的第一部小说是黑色侦探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是全球化的新世纪洛林地区一家即将关闭的工厂,有人在小说出版后问起他对他的家乡孚日地区的看法,他说他18岁便离开家乡搬到了同一个地区的南希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回想起家乡,还是感到极度无聊。老工业区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衰败萧条对生长于斯的年轻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们青春时期有什么样的冲动、喜悦、无聊、痛苦和忧伤?这部篇幅中等偏长的小说就像一部时长三小时的电影,看起来会有点辛苦,不过耐心看完确实展现了一个半小时的商业片一般无法容纳的细节与从容。
今年等待颁奖的过程对于关心奖项的读者和等待评选的作者来说也略显漫长。龚古尔文学奖历来是每年11月的第一个周一颁布,今年春天历年颁奖的Drouant餐厅换了老板,本该周一颁布的奖项推迟到了周三。10月31日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出来的四位作家收到了通知,请到巴黎来等着,“万一获奖了呢”。
延迟的决定很容易让人焦虑,法国媒体还专门采访了四位作者:中国题材的小说《主与奴》的作者保尔·格勒威亚克宣称周三早上将照常进行广告行业的工作,“这样能减缓焦虑”;另一位最终提名榜上的作者托马·勒维尔迪的小说《不满的冬天》题目取自莎剧《理查三世》的开篇独白,他对于是否最终能获奖表示自己很淡然,能够参与就是最重要的,最终提名已经是很好的肯定;大卫·迪奥普的小说《灵魂兄弟》写的是塞内加尔人参与“一战”的残酷故事,他是几位受访者里最迷信的一个,觉得如果把自己当天的时间安排透露出去会影响运气,不过他最终也没能获奖;最欢快的受访者应该算是尼古拉·马修,他开玩笑说如果能获奖那可对生活有很大便利,比他上个星期刚买的房子还要让人高兴。
尼古拉·马修最终获得今年的法国文学最高奖项,这颇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媒体之前普遍更看好迪奥普的《灵魂兄弟》。但可能这些年关于“一战”的各类小说实在太多,反倒是马修的《及其子孙后代》笑到了最后。
龚古尔文学奖的奖金只有10欧元,不过获奖小说至少可以卖出40万册,尼古拉·马修的玩笑并非玩笑,获得这项殊荣之后他的作家之路肯定不需要担心了。而出版他小说的ACTES SUD出版社也成了这几年法国文学奖的最大赢家,6年内他们出版的作家已经四次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实属罕见。媒体和马修本人对于能够获奖都有些意外,因为2017年的龚古尔奖就是颁给同一家出版社的《日程》一书。不过连续获奖的意外仔细想来也有其道理。
首先是这本小说不同于这些年盛行的历史小说或者寓言小说,反映了经济疲软、社会问题众多的法国社会现实,可谓不落窠臼,虽然作者描述的是特定时间(90年代)的特定地区(法国东部洛林地区的河谷工业区边缘地带),但这种“法国环城区”其实正是大部分法国人展开其日常生活的所在——东部等地区是巴黎的环城区,大巴黎又是小巴黎的环城区,大部分人挣扎在中心与社会边缘之间,这也大抵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生活状态。
其次,这本小说的风格和语言颇为别致,没有过度的文学指涉,相较之下,《不满的冬天》把女主人公设定为全部由女性演员排演的《理查三世》一剧的主角,然后让她一遍体悟角色一遍理解重重社会问题,这就有些过于刻意了;另一方面,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描写颇为生动,对话也颇受好评,本来很容易流于刻板印象的人物和场景居然给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难怪不少读者将马修比作“新左拉”,这位今年刚刚40岁的读者是否能配得上这样的比较还需要时间和更多的作品来检验,但第二部作品就能达到目前的高度,未来值得期待。
尼古拉·马修获奖后感叹自己落后太多,40岁才出版第二部小说,需要迎头赶上。不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其实也算成功,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续剧11月15日开始就要在法国三台播放,这次获奖应该能让收视率大幅提高。如果说《动物战争》这部小说写的是衰败工业区最黑暗的午夜,《及其后代子孙》追溯的则是夜色将至的薄暮,小说在一个傍晚时刻展开,在6年后的另一个傍晚结束,我想这一定是作者故意的安排。小说的主人公安东尼随着小说的展开从12岁成长到20岁,小说写了1992年、1994年、1996年和1998年四个夏天,四个章节的标题分别取自90年代的四首摇滚/说唱歌曲:1992年是涅槃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1994年是枪花的You could be mine,1996年是法国说唱二人组NTM的La Fièvre(《发烧》),1998年则是Cake乐队翻唱版本的I will survive。如果说第一张确实闻起来像是少年的神气,那么到了小说的末尾“我会活下去”可能已经显得颇为苍白无力,最后那个类似小说开头的傍晚,像6年前主人公一样年纪的少年们又在湖水边嬉戏,一如当年的他和表兄,但他的青春还没完全展开就已经开始枯萎,来日方长?明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母亲的劝慰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马修认为自己的小说并不仅仅是讲述故事,也不只是为了描述众生相,虽然他的小说描写了从小中产阶级到平民再到困难户(cassos,是法语cas social的俚语形式)的各个社会阶层。他认为小说应该有小说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意识,但小说家毕竟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政治人物,小说家不做审判,不做评判,只做观察,而他作为小说家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观察去理解这个世界。
这样的说法未免有些滑头,小说家的立场在主题和风格确立的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展现自身了,马修对法国中间阶层和中间地带的敏感与关注和他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他的成功之处也在于此,真正能打动人的往往是那些出自血脉深处的东西。如果马修的下一部小说换一个地理和社会背景,一种可能是他成功拓宽了自己的写作题材,另一种可能是,他也许会失去他熟悉的世界,毕竟他自己也在访谈中颇有自知之明的说到过,我们不应该试着去写那些让我们喜欢的作品,我们应该写那些我们有能力写的作品。
小说的名字有些不好翻译,语出《便西拉智训》:
一些人死后留名,今天的人民,依然赞美着他们。另外一些人,谁也不记得,仿佛根本没生过。他们及其子孙后代,死后被人遗忘。
小说的扉页就引用了“另外一些人”这一段智训。《便西拉智训》是犹太经典,不过到了新教那里已经落到了次经的位置,通过引用这段次经中对“次要人物”的描写,尼古拉·马修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些已经被人遗忘、正在被人遗忘以及往往被人遗忘的阶层、地区以及生活在这种境况中的人们,应该有人为他们去写一些东西。
他用一串许多法国人都不熟悉的洛林地区风貌让异国的读者都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青春时期的躁动与无聊,我想这也是他担忧的全球化威力的一个佐证吧,世嘉MD游戏机与索尼克,李小龙,枪花,涅槃,经历过90年代的读者大概有不少人会对这些感到熟悉,而好小说的妙处可能在于,它能超越乡愁感怀或者悲情回忆,把一个世界在我们眼下这个时空再次展开,让我们反观当下的处境,也许这反倒能让那些容易被遗忘的人物变成“难忘的人们”。
原标题:201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获奖小说书写了被遗忘的“次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