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文学”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它们的出版与影视改编,背后也映照着主流社会对待同性群体态度的变化。最近,我们专访了英国小说家萨拉·沃特斯,在她已出版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题材都围绕着同性之爱展开,与很多作家不同,萨拉·沃特斯直言不讳自己身上的“同性文学作家”标签。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 2017)剧照。
今天,有关同性恋的观念革新方面,图像走在了文字的前面。那些同性题材的电影有着太多的观众,例如《春光乍泄》《蓝宇》《卡罗尔》《小姐》以及最近的《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等等,在电影获得好评之后,这些小说的原著才出现在国内的图书市场上——仿佛影院的周边产品。的确,图像在传播上有许多优势,在英剧和日漫中,同性已经成为常见的桥段,它更直观、速度更快,比起小说更容易控制感情节奏。2016年,韩国导演改编的电影《小姐》上映,随后,原著《指匠》作者萨拉·沃特斯也走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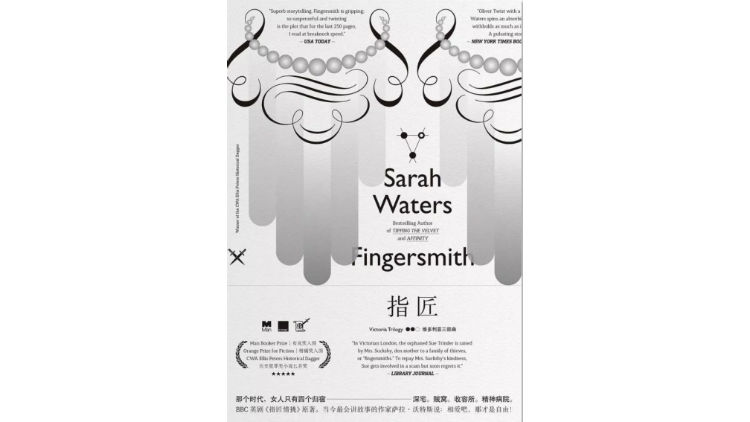
《指匠》,作者: [英] 萨拉·沃特斯,译者: 阿朗,版本: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9月。
而在文字世界中,虽然同性文学依然属于小众,尤其是像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和《鳄鱼手记》这类私密性和个人色彩极为浓郁的作品,几乎只有指定的读者会打开阅读,但它还是在国内得到了不少出版社的支持。有些作品的读者较少,例如威廉·巴勒斯的《酷儿》,而有些作品也有不少的读者,比如白先勇的《孽子》,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王小波的《东宫西宫》,今年也有同性题材的新书如郭强生的《断代》和再版的严歌苓小说集《白蛇》。同性题材的文艺作品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内读者的理解,尽管有些人还是带着恐惧和反感的态度,但文艺作品告诉我们,除了“赞同”和“反对”外,宽容是一种更重要的态度,这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属于现代社会的标准。尤其考虑到LGBT群体的运动历史并不长,直到1981年,挪威才成为全球第一个通过法律禁止对同性恋歧视的国家,到2015年,全球也不过有21个国家承认同性婚姻,看起来,人类社会进一步开放的空间还很大。

《断代》,作者: 郭强生版本: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6月。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是人们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便厌倦了LGBT运动的声音,很多人将支持同性恋视为强加的“政治正确”,在《月光男孩》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之后,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就更加激烈。而在亚洲,同性恋的生存状况一直很不理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亚洲国家通过同性婚姻合法法案。世界范围内,反对同性恋的浪潮也逐渐增多,人们担心这种导向会影响下一代的自然性取向,也担心艾滋病等卫生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讨论,但它在今天,却与一种世界性的保守主义与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回潮联系在了一起,正如萨拉·沃特斯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所谈的,“世界范围内,事情变得更加不同寻常”。
对于现代社会的这种奇怪状态,历史和社会学家需要给出解释,而文艺作品的创作者们——尤其是同性题材的创作者——需要化解这种敌对,用自己的作品展示同性恋者真实的情感状况,并让更多陌生的人体会同情,抵达宽容。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永远是没有界限的,最理想的状态是让我们把所有标签都撕掉,我们不会说某部小说是“同性恋小说”而视之为“爱情小说”,我们不必用特殊的目光把它筛选出来单独对待——但就目前而言,我们距离这种理想还相当遥远。因此,萨拉·沃特斯在采访中谈到,她会非常乐意被别人称为“女同作家”。在一个人们依旧对同性恋群体充满歧视和压迫的世界上,有时,借助标签的方式去发声是很有必要的。
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英国小说家,1966年7月21日生于威尔士。沃特斯在写小说之前是位学者,博士论文后开始第一部小说的创作。沃特斯目前出版6本长篇小说,除了《小小陌生人》之外,其余的作品都与性或同性有着关联。代表作品包括《轻舔丝绒》《荆棘之城》《指匠情挑》等。2003年萨拉·沃特斯曾被Granta杂志选为“20位当代最好的英语作家”。

萨拉·沃特斯(Sarah Waters),英国小说家,1966年7月21日生于威尔士。沃特斯在写小说之前是位学者,博士论文后开始第一部小说的创作,目前出版6本长篇小说。除了《小小陌生人》之外,其余的作品都与性或同性有着关联。代表作品包括《轻舔丝绒》《荆棘之城》《指匠情挑》等。
不介意被标签为“同性文学”作家
新京报:你会如何定义“同性文学作品”?是必须要由同性恋作家创作呢,还是只要反映同性生活就可以?
沃特斯:我很乐意被称作一个“女同性恋作家”,几乎我的所有作品都清晰地描绘了女同性恋的性格和女同话题。但是,如何定义“同性文学”,谁又有权利去给它下这个定义,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我知道有些同性恋作家会讨厌别人称呼他们为“同性作家”,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被贴上标签,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就不应该把他们的作品视为“同性小说”了呢?还有一些书,读起来和同性恋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一旦我们发现这个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同性恋有点关系,突然间这本书就有了某些同性恋方面的阐释。(我想想,这方面的例子有达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和《浮生梦》)然后,就像你所说的,有些描写同性恋的书籍其实是由异性恋作家完成的——它们算是“同性书籍”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但它是个好事情,我是这么觉得的,标签可以阐释一些事情,但也会形成限制;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同时,也可以只让我们看到故事的一部分。

《轻舔丝绒》,作者:[英] 萨拉·沃特斯,译者:陈萱,版本: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
新京报:当你第一次出版同性小说的时候,有受到什么阻力吗?
沃特斯:没有,而且我认为我的书对他们来说出现得正是时候。假如是在十年之前尝试出版的话,我认为主流出版社不会接纳它们——这些书可能会由一家小型的同性恋或女权主义出版社所出版。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英国的文化氛围宽容了很多,有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我想,对此我受益匪浅。在2002年的时候,《轻舔丝绒》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并且大多数人都对此感到兴奋。从头到尾,我都没有感受到任何的阻力。

《轻舔丝绒》(Tipping the Velvet, 2002)剧照。该剧也译作《轻击天鹅绒》《南茜的情史》等。
新京报:在你看来,一部优秀的同性题材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及,什么样的同性题材创作又会是糟糕的?能否举几个例子。
沃特斯:我认为一部优秀的同性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应该和其他好小说的品质是相同的:例如要有才华,有艺术感,能产生共情。在处理同性恋角色时要避免刻板印象,一个很优秀的例子就是艾莉森·贝克德尔,在她创作的每一部图像小说里,都充满了复杂又真实可信的女同性恋角色。一本糟糕的同性恋小说就会适得其反,它会充斥着关于同性和同性生活的陈腔滥调。我也能想到一些例子……不过,我不是很想分享出来。
新京报:你曾经是研究19世纪女性文学和情色小说的哲学博士,是什么让你放弃学术道路转而从事小说写作呢?
沃特斯:我在博士时代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及之后的英国男女同性文学。它也要审视情色小说,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情色小说是少数得以出版的包含了同性生活图像的形式之一。我喜欢写我的论文,但这个过程也很让人沮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只能局限于历史提供的内容,而在同性恋方面,我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又相当少。
但是,我意识到如果我成为一名小说家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在我的调查研究之上自由地安置小说,可以发挥想象力去弥补那些空白。这就是我所做的,尤其是我的第一部小说——《轻舔丝绒》,它描述了活跃在19世纪末伦敦的各种女同性恋群体,我通常把它称为一种“幻想历史”。
新京报:所以,当你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你内心有预设的读者群吗?例如大学教授,普通读者,或者是特定的同性群体?
沃特斯:我的内心肯定会有一个读者:我希望我的每一本书都能带领读者踏上旅途,偶尔带领他们进入意料之外的或者令人惊讶的地方。但我不会把我的书指向某一类特定读者,我认为这是极大的限制。基本上,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同性恋、异性恋、男性、女性以及这之间的所有人群。尽管我希望我能写得很巧妙——在小说中囊括像性别、性取向、阶级差异这些严肃话题,但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些书读起来都是非常轻松的。
新京报:那么成为一个畅销作家会对你产生困扰吗?你认为严肃小说和畅销小说之间是否有明确的界限?
沃特斯:对我来说,成为畅销作家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意味着你的小说能更广泛地抵达人群!我认为大众小说和那些深奥、艰涩的小说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对我来说,我最钦佩的是那些能够跨越这些小说和类型的界限的作家,比如说查尔斯·狄更斯、艾丽丝·默多克、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等等。他们都有充满智慧的事情要讲,同时也有很强的叙事天赋。
新京报:你的大多数小说都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为什么?在写作之前,你会就这方面做许多准备工作吗?
沃特斯:啊,没错,我被维多利亚时代给迷住了。拍摄《轻舔丝绒》(背景为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在19世纪中追溯得更远一些。所以,《灵契》的背景就设置在了19世纪70年代,而《指匠》则设置在60年代。我想,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有一种“传奇色彩”的特性——至少,从我们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我被那些巨大的、反人性的机构所吸引——比如庞大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同时,我也被那些繁杂、疯狂的时尚所吸引——紧身胸衣、笼式衬裙。他们让某种豪华的叙事成为可能(毕竟,这个时期也有像查尔斯·狄更斯和威尔基·柯林斯的那种“巨著”小说)。
在研究和准备方面,我一直都会做很多工作,随着写作生涯的发展,我所做的研究也越来越严格。在写作之前,我都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扎扎实实地调研,这有助于我创造人物和故事,也给了我一连串想探讨的话题。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就会继续保持研究的习惯,然后用不写作的时间读读书,看些图片和电影。

《指匠情挑》(Fingersmith, 2005)剧照。
对少数群体不宽容的社会,是不健康的社会
新京报:能否给我们讲一下维多利亚时期同性恋们的真实处境?
沃特斯:对男同性恋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时期。男人之间的性行为会被视为“恶心的猥亵”,会被当作刑事犯罪。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遭遇所揭示的那样,他们将会受到残酷的惩罚——在监狱里接受劳改,还要忍受社会的排斥。然而,王尔德的遭遇也证明了一点——当时的英国,尤其是伦敦,有着丰富的男同性恋亚文化,有着自己的时尚、行为准则、集会场所,还有自己的文学和艺术。
奥斯卡·王尔德,爱尔兰作家、诗人、剧作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伦敦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曾因性取向入狱接受“改造”。
我认为对女同性恋来说,她们也同样会遭遇这些事情,但如果从更细微的角度去考察的话,英国女同性恋的历史非常难以确定,因为在这里,从来没有一个女同性恋者因为性行为而被定罪——因此,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审判与逮捕纪录。而且在过去,女性们一起生活、同居、同床共枕、有亲昵的身体接触都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大多数女同性恋的关系都被“自动屏蔽”了。
新京报:除了性别,同性恋的遭遇会在阶级上有所差异吗?比如说,上层社会的同性恋是否更容易逃脱惩罚。
沃特斯:在阶层上肯定会体现出差异,但我并不确定这是否与逃脱惩罚有关——准确来说,这对女性而言是个可以好好利用的优势,她们就有机会从男性生活中独立出来。那些非常富有的女性,比如说娜塔莉·巴尼和芮妮·费雯,她们就能搬到巴黎去过着奢华的女同生活。对工薪阶层的女性来说,想以情侣的身份同居就非常困难,例如,她们中的一个人将不得不以男性的身份生活,以此来“合法化”她们的关系并赚取更可观的金钱,我们知道有些女性真的选择了这种方式。的确,这个阶级因素一直吸引着我,关于同性恋经常存在着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女同性恋的双方在某些程度上是相似的、是彼此的镜像。其实并非如此,她们之间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阶层、种族,还有年龄。

娜塔莉·巴尼(1876-1972)画像。她是美国诗人和剧作家,在1900年公开了自己的女同性恋身份,致力于推动女性写作并成立女性知识学院,反对一夫一妻制。
新京报: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稍有好转的?你认为目前在英国及世界范围内,同性恋运动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沃特斯:在英国,这种情况在20世纪缓缓转变,然后在过去的20年里,情况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如今,对同性恋者来说,就法律保护和主流关注度而言,英国已经成为了最理想的国家之一。然而,恐同症依然存在,而且目前,随着英国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像我这样的同性恋者就会意识到,我们很容易和其他的受辱的少数群体一起成为仇恨的靶子,比如移民和要求福利的人。在世界范围内,事情就更加不同寻常。当很多国家——例如英国——已经接受了LGBT权益的时候,有些国家却让LGBT人群越来越难以安全并有尊严地活下去。在谈及如何支持世界范围内的LGBT运动时,我认为,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这个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改善吗?
沃特斯:当然不能。你不能指望通过法律来消除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与恐惧,但是,通过法律,你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来支持和保护同性群体,这也是为什么一项法律的改变如此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我是人类尊严信托(Human Dignity Trust)这类组织的忠诚支持者,它是一个建立于英国的慈善机构,支持全世界的人们向反同性恋的法律提出挑战。一个公正、人道的社会必须要包容多样性。
新京报:有些时候人们会觉得支持同性恋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尤其是一些作品涉及女权和同性的时候,人们就很难提出批评。也有很多人会说:“同性恋有表达自己的权利,但我也有表达自己厌恶同性恋的权利”。
沃特斯:我认为,就艺术作品而言,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失败的作品,无论它涉及的主题是什么,提出批评都是很好也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如果我的读者因为担心批评我的作品而导致“政治不正确”,因为我是个女同作家从而给我的作品以特殊待遇,那么我会相当反感。我希望他们能够诚恳地指出我的作品中有哪些艺术缺陷。我认为任何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但是,如果有人是因为厌恶同性恋和同性题材而批评我的作品,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表达和纵容一种缺乏宽容的态度。他们会使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去打击其他人的言论。一个不宽容的人将不会是一个幸福的人;一个不宽容的社会也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新京报:在最近的小说中,例如《小小陌生人》,你开始把背景从维多利亚时代移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主人公也不再是同性恋。能说说为什么做出这些调整吗?
沃特斯:因为我一直是哥特小说和电影的粉丝,在《小小陌生人》中我看到了一个写鬼屋小说的机会——这些东西总是非常吸引我。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个故事,它很明显不是同性小说,也和性别没有关系——它更多地讲述阶级和二战后英国的变化,当时这个国家失去了一些陈腐的等级制度,并且开始变得更加精英主义。但我之前的作品《守夜》,也设置在相同的时期,可它依然和同性恋的人物角色有着联系。所以,即使有一些故事设置上的转变,但我一直都对LGBT群体的生活保有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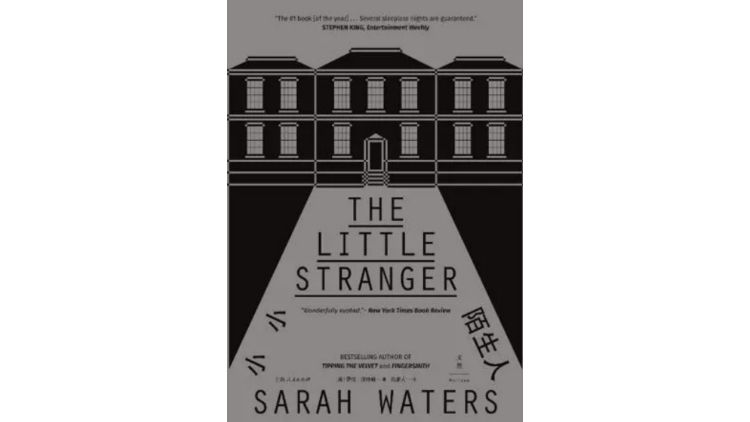
《小小陌生人》,作者:[英] 萨拉·沃特斯,译者:孔新人,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新京报:在这些作品中还是能看到你对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式大宅的迷恋。古老的家族,庞大的庄园……
沃特斯:的确,英国的庄园别墅有许多扣人心弦的地方。它们本身就非常优美——美妙风景中的辉煌建筑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都是英国社会的核心,它们有很多迷人的(有时候也是丑陋的)事情值得讲述,例如英国如何组织和划分自己——淑女的房间、绅士的房间、公共区域、私人区域等等,还有那些最明显的——“楼上”和“楼下”,舒适的、供上层社会的人休息并陈列物品的区域,以及那些不怎么舒适的、供下层阶级工作的区域。它们告诉了我们一些英国历史的事情,包括我们来自哪里,以及我们现在身处何处。
作者: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编辑:走走 西西;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