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部分人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都是从国别史或者民族史的角度出发学习的,即便是学习世界史,也经常以西方为中心,将各文明的历史简单地罗列在一起学习。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历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全球史热潮。全球史学家们,如威廉·麦克尼尔,反对西方中心论,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考察各文明间的互动,来理解世界变迁。诚然,这给了我们一种用“广角镜头”来看人类历史的视野。
但是,过于关注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可能也会忽略某个特定国家本身。那么,既忠实于各个国家的身份,又不囿于民族偏见的牢笼,我们能否以这样的方式叙述一段历史呢?在以身份认同为主题的讨论日益激烈的当下,如何维护开放、多元的历史观?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法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布琼的兴趣。他以全球史为范式,主编的《法兰西世界史》在法国国内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
12月10日,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和帕特里克·布琼在法国文化中心,一起探讨全球史及其影响。
为什么全球史变成了学术时髦?
布琼认为,全球史只是历史学科中的一个部分。然而,当钱乘旦回忆在2006年去德国学术交流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在场的大部分历史学者都在研究全球史。为什么全球史变成了一种学术时髦,好像不研究全球史就不算历史学家一样?钱乘旦认为,这说明了我们对全球史的认知存在着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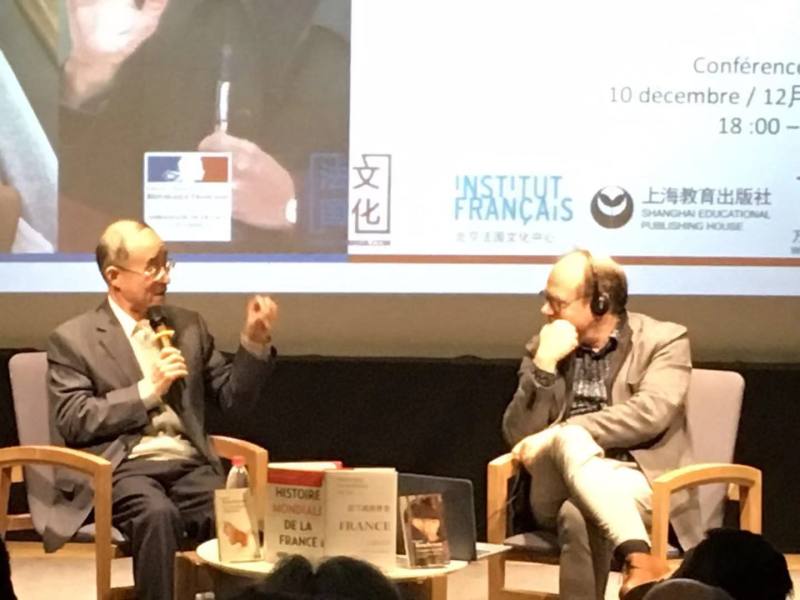
讲座现场,钱乘旦教授在演讲。
那么什么是全球史?钱乘旦不置可否。但是他赞同布琼的一个说法:全球史是一种历史书写方式。这也意味着,全球史与其他历史书写方式,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书写的维度。在全球史这种书写方式出现之前,人们都习惯于一种纵向的书写方式,即按时间的脉络写下来的,尤其是在兰克之后的西方历史学界。钱乘旦认为,这种纵向的历史书写方式,还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而中国的历史书写也相当大程度上具备这样的特点。
全球史是一种横向的书写方式,它最关注的是相互关系的问题。钱乘旦打了一个比方,在宇宙里,有一个个实在的“天体”。一般的历史学家往往关注于一个个“天体”。但是,“天体”之间并不是空无一物的,全球史学家就关注这些“天体”之间的东西,还有这些“天体”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也需要历史学家拥有宽广的知识面,来填补这些“天体”间的空缺。这也是全球史对历史学的价值和贡献。
但是,钱乘旦也总结了全球史的几点缺陷。首先,做历史研究需要高度严谨和专业,而全球史学家因为跨度太广、要求很高,很多学者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其次,做全球史的学者比较难用第一手的资料。在兰克之后,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这意味着史料很重要。
第一手材料是做历史的基本要求。因为做全球史的学者不可能懂得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所以在研究他们不熟悉的文明时,他们只能用二手材料,这使得严谨性大打折扣。再次,我们研究“天体”之间的空隙的时候,很可能把“天体”本身给忘了。所以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就算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名著《世界史》,描述法国大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样的重要事件,篇幅也很短,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互动和关系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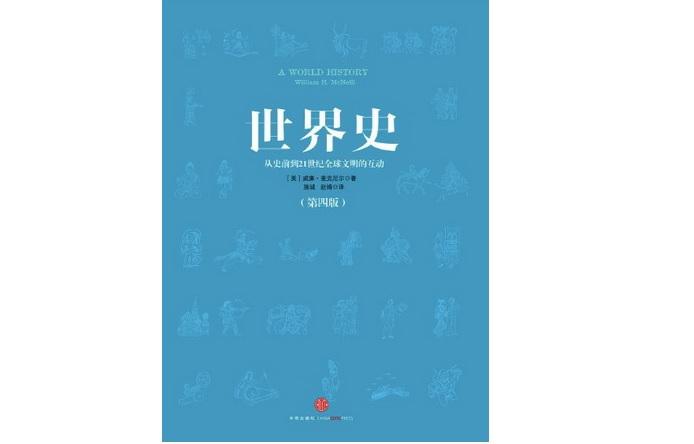
《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版本:中信出版社,2013年10月
因此,钱乘旦并不认为全球史就是历史学的最伟大成就。他希望有一种能把纵向和横向的历史书写方式结合起来的方法。全球史这种书写方法之所以崛起,是因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钱乘旦很好奇,在反全球化力量高涨的今天,全球史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会不会因此衰落下去呢?
在反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史应该怎么写?
布琼认为,自十五十六世纪西方崛起以来,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就开始蔓延,逐步笼罩全球。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也开始反思西方中心论。其实,很多文明都曾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中心,这是我们理解世界很自然的一种方法。布琼很欣赏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将西方地方化,把各地变成一个个“省份”。在这些“省份”之间,有着许多互相关联的中心点。这是全球史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方法。
比如说,过去在法国,很少讲美国独立战争和海地革命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全球史的视野就能很好地去帮我们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钱乘旦认为,法国的“人权宣言”受美国的“独立宣言”影响很大,而美国“独立宣言”里的人生而自由来自英国,人生而平等则来自法国的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联系和流动,在全球史的视阈里就非常清晰。
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互相联系,经济和贸易上的互相联系也是全球史经常探讨的课题。钱乘旦举例说,拿破仑试图摧毁英国的商业,采取了“大陆封锁”政策,结果使得南美的商品无法进入欧洲大陆,这使得德国人不满,并激起德国人的反抗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这种普遍联系的视角,也使得历史学家能摆脱单民族中心的论述。
布琼更希望全球史能让所有的历史都发出它们自己的声音来,不止是解释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很多做希腊历史研究的人都会做古希腊研究,因为古希腊对于西方文明很重要,但是很少人会研究古希腊之后的希腊史,因为大家都把那段希腊史融合进拜占庭的历史里,这导致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貌似没有连续性。但是,历史并不是一系列战胜史,或者光荣榜。很多被征服民族的历史,还有很多弱者的历史,都是历史学家需要去关注的。
钱乘旦认为,虽然很多西方的全球史学家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这很值得赞赏,但是其实这非常难彻底做到。摆脱中心论更像一个美好的愿景,它也是每个人共同的任务。跳出狭小的视野,思考整个人类终极命运的问题,才能避免中心论。虽然这个世界比一百年前获得的共识更多,但是今天的世界却正一步步走向分裂。所以,学者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遍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实习记者 徐悦东
编辑:寇淮禹;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