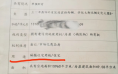贾樟柯一直是国内备受关注的导演。长期以来,他在自己的创作中着力呈现中国的当代经验,这让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在兜售中国符号。相较于他的电影创作,他和当代艺术的关系则较少为人了解。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贾樟柯就已经从当代艺术中汲取养分、获得灵感,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电影创作有不小的影响。
12月28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第二期艺术沙龙上,贾樟柯就“当代艺术与当代电影”这一话题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思考。他认为当代艺术区别于传统艺术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当代艺术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让人们有可能凭依各自不同的人生经验去解读、去感受,而这一当代艺术的特质始终提醒着他,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也应尽力追求多义性,保持电影语义的开放。当代艺术的实验精神则启发了他以结构为手段,打破单一线性叙事的束缚,以便在电影中准确地呈现他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体验和生存感受。此外,他还谈到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分,他个人喜欢的导演以及他正在拍摄的武侠电影。
以下内容整理自贾樟柯当晚的发言。
创作的初衷和意欲达成的目标,
是区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重要标志
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种二分法,在我们的话语空间里是常见的界定电影的方法。既然使用这样普遍,就说明这样的划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概括的准确性。
电影进入到工业生产以后,需要有严格的计划性。比如从拍摄流程上来看,需要确定用什么型号的摄影机、什么系列的镜头、什么样的声音系统、什么样的灯光——特别在过去感光胶片不是很成熟的年代,灯光非常重要。好莱坞为什么坐落在洛杉矶?因为那里常年有太阳,很少下雨,非常适合电影的生产。光在早期电影里非常重要。拍摄之后的冲印、剪辑,所有这一系列的工业流程,对电影的生产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套系统的良好运行的话,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艺术电影不是说不要这样的工业化的生产,而是说其中最重要的创意核心——编剧、导演、演员,是为了把内心真实的声音传达出来而进行的创作。他们为了把对电影语言的探索传达出来,为了准确地把我们此时此刻对人和事的看法讲述出来进行拍摄,这样一种类型的创作,就是艺术电影。
商业电影则另有一套创作的方法,比如会进行市场的估算。为什么会有类型电影,因为拍了各种各样的电影,后来发现有一些,比如有开枪和骑马场面的电影,讲求速度的电影,观众最喜欢看,于是就再拍一部,然后发现反响还是很好。那么这样对于投资来说是很稳妥的,那就持续组织这样的拍摄。
整个组织模式和创作方法都是市场导向的,由市场导向推算出来、组织起来的拍摄,拍出的电影被称为商业电影。所以实际上并不是说花了多少钱、是否是大公司出品,就能界定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而是从创作者的初衷和创作理念来界定的。

《夺命金》剧照
当然,今天有一些导演在自己的类型片、商业片里,放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他们的作品里有他们对电影美学的想法和探索。他们的影片既符合市场要求和规律,又保持了作者性。比如法国导演梅尔维尔,拍的都是警匪片,但他的电影有对社会状况和人物的精神状态的非常准确的捕捉和刻画。又比如香港杜琪峰导演的《夺命金》,讲香港金融社会里的人性问题;虽然用枪战片的类型语言来拍,但在这样类型化的手法背后有他对香港社会的观察。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为工业中的作者或者商业片中的作者。我们熟知的科波拉、斯皮尔伯格都是有作者倾向的商业导演。
我的电影创作深受当代艺术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是我小学、初中和高中时期,当代艺术逐渐进入我的生活。这既包括当时发生在山西的那些艺术实验,也包括在长期的闭关锁国之后通过阅读带来的视野解放。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德国表现主义》,人民美术出版社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那时我在上高中,新华书店里有卖。翻看那本小册子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来自图像,而且来自图像背后的、透过图像传达的观念的冲击:自我的、个人的精神世界怎么样用一个和传统语汇不一样的方法表达出来。
那时山西有一个大的艺术实验叫作“乡村计划”,差不多有将近20个艺术家参与其中。这个计划给我的冲击有几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跨艺术门类的计划,有传统架上绘画的艺术家,有行为艺术家,有音乐人,也有做电视的,还有好几位作家,都参与了这个计划。
以前我们理解的艺术活动,都是单一的:写一本书,拍一张照片,写一首音乐,但是忽然你发现,组织一个事情本身也可以是艺术。就像今天的策展人一样,展览中的各个参展艺术家和展品所形成的互文关系,以及展览本身传达的意念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品。
“乡村计划”把这么多的艺术家综合到一起,同时进行一个艺术动作:下乡。下乡,不管是沿黄河也好,或是去一个偏远的地方也好,这在过去都曾经有过,但现在它被重新组织,这意味着对土地、对生活的一种重新的理解,用新的语汇,面对同一个创作对象,来传达转型时期的新的感受。所以我当时对“乡村计划”的组织方法非常震惊,它的结构性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多年之后,当我来到北京,在电影学院读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它;而透过直观的生命经验和后来的理论知识,我又反过头来理解了当时“乡村计划”带给了我什么东西。
传统的叙事艺术里面的叙事模式,三一律、线性叙事,我总觉得无法概括当代生活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需要通过结构来完成对当代生活的更为准确的呈现。比如2013年的《天注定》,那四组人物虽然都是嵌入到暴力处境中的人,但他们在命运上没有什么交叉,在剧情推动上也没有任何的支撑作用,我为什么要拍这样的四组人物呢?

《天注定》剧照
那是因为我非常需要用结构的方法来传达一种时代气息,这个气息是什么?是密集发生的暴力事件,这种密集性无法通过一个故事来呈现。上个月刚发生一件,这个月又有一件,这种感受你怎么表示呢?你通过一个单一的故事无法解释或描绘我们对这类事件频繁发生的感受。这时结构性就非常重要了:透过四个故事的编织,密集性就可以传达了。
我的电影创作中的另一个手段是建立作品内部的对话性,比如2008年的《二十四城记》。那时正是经济转型期,大型国营工厂或者改制或者倒闭,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生活及其载体——工厂——都在消失。
我找了很多工厂,重庆的、上海的、武汉的,最后选择了成都的这个五万多工人的工厂。我们用各种方法找到愿意讲述的工人。在拍摄的过程之中,你会发现纪录片的优势在什么地方。纪录片是实证的,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真实的经验被记录下来。

《二十四城记》剧照
但当我们拍摄到100多个人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单靠纪录片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讲述者,受制于他的成长经验、教育程度、表达能力和关注点的不同,谁的叙述都无法把我在采访这100多个人的过程中了解到的东西传达出来。这时我感到特别需要虚构。
虚构是有效地呈现事实的方法。于是我们在片子里加入了四个虚构的角色,最典型的是陈冲演的那个角色。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那个工厂招了很多上海技校的学生,因为修理飞机要求非常高。陈冲的角色讲的其实是我采访的十几个上海女工的记忆,如果我们不通过虚构把众多人的记忆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这部影片传达的历史信息、生存信息就会变得非常窄。
所以当我想用这些方法来结构我的电影的时候,是和我上世纪80年代成长经验中了解到的那些已经用实验艺术的方法来进行结构性的处理的艺术实践有很大关系。比如宋永平,他的绘画语言从传统的写实,转变到表现主义,以便捕捉真实的精神状态。那时大家的关注点都已经进入到当代性,不再追求造像写实,而是捕捉真实的精神状态。
当时还有一个作品,好像是宋永红的,把十几辆自行车,在黄河边用压路机碾压在一起。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个作品究竟传达了什么,但它最起码传达了多义性,传达了一种无法言说的经验。所以多少年之后,每当我的电影被观众说看不懂时,我就暗自窃喜,因为我觉得至少我保持了电影的开放性和多义性。我觉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是否置留了一种多义性,可以让人们用各自不同的生命经验去附着、去读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当代艺术的实验,那时我们才改革开放十年。比如徐冰的作品《天书》,是我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里读到的,我觉得好有意思啊,他颠覆了我们对文字的理解。又比如黄永砯的搅拌美术史,把一本中国美术史和一本西方美术史在洗衣机里混在一起搅拌。看到他们的创作的时候,就跟我刚看到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比如《黄土地》的时候的感受一样,我会觉得他们是一些天才。

徐冰《天书》

黄永砯《〈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
而所有这些当代实验最终形成了一些共同的艺术精神,比如说反叛,又比如说怀疑。那时候我们电影学院旁边有一个诗人开的酒吧,黄亭子50号,经常组织读诗活动。有一天食指也来参加了。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诗歌界的一个前辈,文革期间在我的老家山西插队。他的代表作比如有《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和《我相信》(注:实际此诗的题目是《相信未来》)。
有一天郭先生在酒吧朗读了《我相信》,刚朗读完,郭先生刚走,就有一个愣小子走上台说,我给大家朗读一首北岛的《我不相信》。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影响,从“我相信”到“我不相信”。这种怀疑精神,对个体经验的怀疑、对社会的怀疑、对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的怀疑,在当时是一个共同经验。所以谈当代艺术的影响,不能仅仅从视觉上、从电影语言上来说,要把当代艺术提供的精神融入到创作之中。
今天我们看一些电影,拍的都是当代故事、当下的人物,但就是觉得好老好旧,因为它对社会、对人的理解是陈旧的,它的观念是陈旧的。但是另有一些电影,可能拍摄于很久以前,但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是当代的,因为它是在当代语境之下进行拍摄的,是和当代艺术的思考并驾齐驱的,带给观众以新的理解人、理解社会、理解事物的方法。当代艺术就是这样具有启发性和精神性的。
十几年前,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行过一个大型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我2001年的纪录片《公共场所》也参展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对当代艺术的直接参与。蓬皮杜艺术中心把展厅做成一个超市的样子,商业气息非常浓,我觉得它的布展方法对我很有启发。当时中国的消费文化刚刚兴起,消费氛围刚刚呈现出来,我拍电影可能是一个直观的捕捉,但这个当代艺术的展览,不仅加深了我对即将到来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性的社会氛围的理解,还加速了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也是实验艺术的一个作用,它总是有预言性的。
通过当代艺术,我们能够尽早地得到关于这个社会即将到达何处的更多的信息。
《江湖儿女》讲的是古典伦理的消亡
三峡开始大规模地移民的时候,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去三峡拍东西。那时在北京聚会的时候,经常就有朋友说:我下周要去三峡了。那时我一直想拍刘小东,有一天他和我说要去三峡画一组画,你要想拍我你就来吧。于是我就去了三峡。

《三峡好人》剧照
坐船从宜昌逆流而上往巫山、奉节走的时候,一路上看两岸风光,我觉得好像古代并没有消失,今天我们看的这些山和李白看到的是一样的。后来人家和我说不一样,因为今天的水位高了,李白看得更雄伟一些。但整体的气质和氛围没有变。
在中原地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拆迁建设,让每一个村落的变化都非常大;而沿长江坐船逆流而上的时候,有一种进入古代空间的感觉。于是当我一下船之后,对比非常强烈,我面对的是一个坍塌的、拆迁的废墟。那么大面积的废墟,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在《三峡好人》里,楼会飞走,有踩钢丝的人,有飞碟,都是因为那时三峡给我的超现实的感受。

《三峡好人》剧照
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场,就像一个装置艺术一样,是可以代表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改变的最为夺人心魄的外化场景。3000年的城市,变成一个一米不到的废墟,一船一船的人离开故地。三峡集中呈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去了拆迁的工地,楼的窗户、阳台都已经打了,但里面小饭馆还在做饭,麻将一桌桌还在打。人的日常生活和这样一个超现实场景就那样交织在一起。有人看我的电影,可能觉得“怎么又拍三峡?”但我真的没有拍够。
去年拍《江湖儿女》,我觉得可能是我的一个后三峡时代,除了现实的可见的外部世界的剧烈改变,我想拍一个内在、看不到的世界的终结。这个终结就是传统的人际关系、人际方法的落幕。信啊、义啊,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古典伦理,一直在消失,今天的中国人好像换了系统一样。有一次我有个朋友,说山西人有个特点是看破不说破。这个过去是存在的。大家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交往的方法,用同样一种伦理,所以不说破,对方也能理解;今天你不说破,对方以为你不知道呢。

《江湖儿女》剧照
《江湖儿女》就是讲古典的伦理是怎么消亡的。如果说十年前《三峡好人》是讲外在的建筑和城市的消失的话,《江湖儿女》讲的是我们内在的、建构我们情感世界的建筑也已经拆除了。
技术改变了人类情感
我对这些年的时空变化有特别直观的感受。
我小时候所在的县城,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建筑。街道上看过去,就能看到马进士、王进士的房子,张家大院,刘家大院。另外,那时的人是不流动的。我们有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县城里没有公共汽车,家里没有摩托,没有汽车。所以我小时候就在一个相对封闭、相对稳定、相对古典的一个时空感受里面。
从县城往北,是一座山,有一家林场,我小时候觉得那里就是世界尽头。对于一个只有自行车的家庭,那是太遥远的地方,我也从来没有去过。这两年我比较多在老家住,经常去那儿,因为开车20分钟就到了。现在的20公里和过去的20公里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时20公里意味着千山万水。那时很多村子里的人,从来没有去过县城;而县城里的很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县城。现在年轻人里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因为筹备武侠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游侠、武侠、浪子?因为他可以移动。在那样一个人们不能大规模或者频繁移动的古代社会里,那些四海为家的人非常浪漫。一会儿在华山比武,一下子又到了蒙古大漠,又一下去了嵩山少林寺——这对那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新的通讯方式也在改变我们的情感体验。我不知道当我们可以轻易地视频通话的时候,过去琼瑶小说里写的那种相思还存在吗?比如你男朋友去美国留学了,过去每个月你等他写一封信,通过海运寄回来;今天你随时可以问“你在干吗呢?”不是说相思会消失,但一定改变了。过去你在房间里等一封信,通过文字这样抽象的形式去感受他,去理解一个你爱的人,跟今天你随时打开视频,吃饭也视频,走在地铁里也视频,那相思的强度肯定减弱了。
人的移动带来的改变也是巨大的。《二十四城记》里的工厂工人,真的是工人。因为他的命运跟具体的一家工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跟机器是有契约关系的。一辈子要在这个工厂,他的福利、劳保,他的教育、他孩子的教育,所有的这些都是工厂提供的。今天这样的一种阶层可能已经消失了。你去东莞,只有打工者,他做的还是工人的活,但他流动性很强。今天在这个工厂,明天在那个工厂,流水线的工作三天就可以培训好。
在这样高速的流动、重组和时空的变化之中,我意识到我需要按照科幻电影的方式来拍武侠片,因为科幻是穿越到未来,武侠是穿越回过去。为什么要写一个古代的故事?我觉得是出于我对今天生活的感受和理解。
撰文、整理: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
编辑:李妍;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