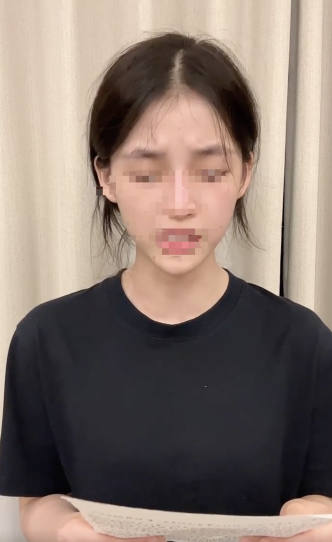有一种学说认为,地球是人类的监狱,重力和大气层就是这监狱的栏杆。然而,如果冬天不是生活在准静止锋之下,不是在潮湿、阴冷、阳光难觅的中国大西南,你很难自觉感受到这种无处可逃的囚徒困境。
表面上,囚禁人的是有形的空间,事实上让人无法逃离的是无处不在的时间。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似乎暗示着超越在于走入别人的空间。但是这种做法是无效的,因为天下同此寒暑,能够让人获得诗意的,唯有对时间的剪裁。数万年中,从洞穴中的原始人到高塔上的贵族小姐,人类曾不断地在篝火边讲述,在羊皮纸、打字机前书写,尝试着唤醒逝去的既往,预测不可知的未来,有时甚至不得不借助于无法把捉的梦境。
还好,人类在一百多年前发明了电影技术,于是那些雕刻时间的人们出现了。从爱森斯坦、奥逊·威尔斯到塔尔科夫斯基,时间因为这种雕琢变得有形而易于把捉。这真实的梦境,让人得到瞬间的安慰,在对生命、生活、存在的无力、平庸、甚至是悲怆的陈列和展示中,暂时与无法宣泄的欲望媾和。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使贫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电影就是当代人的诗歌。时间就是这诗歌的语词和韵律,而负责剪裁的是那些最幼稚的儿童,或者最幼稚的囚徒。
一. 意象的复沓与互文的诗意
毕赣的两部长片《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物质符号的使用和空间的设置呈现出复沓和互文的关系。物质符号有:钟表、垃圾场(车辆报废场)、摩托车、绿皮火车(闷罐车)、瀑布边上的逼仄住房、台球、破旧的电视、斑驳的墙面、摆渡船(滑杆)、雨、野柚子、香蕉(苹果)等等。空间有:凯里、荡麦(梦中的多层剧场)、路与河流。

这些贵州凯里的典型意象,加上从来没有出现的阳光给人的观感并不是很好。在《路边野餐》的开始,我甚至产生了一种感受:如果这是一个绘画主题系列,也许可以入巴塞尔展。这些意象似乎共同涂抹出一幅西南腹地落后、肮脏、阴冷的图景,仿佛上帝拿着镜头在解剖这个地区的人类的待启蒙和“阉割后”状态。所以曾经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毕赣也许在讨巧、献媚、自我文化殖民……但是,就算是有吧,这些符号却在后面的编织中被赋予了诗意。
没有人能回避这位年轻导演对钟表的执着征用。童年卫卫近似魔怔一般的不断在墙上画着钟表,有的宛如日晷,有的又近似画家达利的风格;罗纮武的父亲葬礼时在墙上被拿下的早已停止了的钟,和张艾嘉交出的最珍贵的不再走动的手表,都是时间的象喻。(关于时间,我们下文还要继续谈到,在此先打住。)老医生的那壶水的倾倒,被一个长镜头从头至尾拍摄下来。这大概是能买到的容量最大的壶了,但它仍然是有限的。《路边野餐》中从来也没能买到的香蕉,被陈永贵读出来却没有实体的野柚子。这些水果,象征着味道在影片中的弥散。《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万绮雯拿到了水果机中的野柚子、在看电影时边吃边哭,少年白猫因为母亲的失落从皮到核完整地吃了一个苹果——又是一个完整的长镜头。在梦境中,遇到的马所驮着的、继而又因为马惊撒落一地的橘子。而摆渡船和滑杆,和蒙克的《嚎叫》中的桥形成了互文关系,沟通了此在和彼在等等。但这些还不是这位导演最出彩的意象使用,最值得一提却可能被忽视的应该是“在路上”。

在《路边野餐》中,毕赣执着地要拍出一种“在路上”的状态。无论是从凯里到荡麦、从荡麦到镇远、从镇远回凯里,抑或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中从梦中的坑洞回多层的时光的监狱,摩托车这一山区最为实用的交通工具取代了沃尔特·塞勒斯(电影《在路上》的导演)的大平原上的汽车,成为路的践行者、人的承载者和两点之间的去远者。虽然这一角色有时也被绿皮火车(闷罐车)所替代,但是显然,摩托车优于后者,因为它将人的身体暴露于外,这就是一种保留和去避的状态。
据说毕赣曾是一名婚礼导演,也许就是在旷日持久地对千篇一律的彩车队的拍摄中,他发现了“在路上”中的诗意。王晓华在《身体诗学》里谈到:“道路是最原始的诗性意象。它是起点与中途,过程与目标,生长与衰落”。毕赣还实验性地让它沟通了现实与梦境。
二. 多层舞台与时间并置
长镜头当然指向真实感,但更重要的是它总在提示观众开始感受或者思考。对于长镜头的拍摄一直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一种是完全还原的纪实派,这一派只要把摄影机用三脚架支在街头连续拍摄就可以了。另一种是设计派,充满了对走位、机位和景别的调度。侯孝贤是后者,毕赣也是。《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主宣传片选取了左宏元在抓住了罗纮武和万绮雯这对露水鸳鸯后的唱卡拉OK的片段。镜头同时勾连起罗纮武、万绮雯,将一种就要炸裂的三角关系化解为一首伍佰的歌(也是一个不断复沓的毕赣符号)。这也许不失为一个卖点,但是这个桥段中人物的表演和氛围的烘托仍然是粗糙的,充其量达到了普通港片的水平。
如果从镜头质感的角度论诗意作者,毕赣和塔尔科夫斯基完全是两回事。让毕赣卓然于众多“剪刀手”的,不是他的镜头表现力,而是他的无与匹敌的舞台设计。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将诗意、哲思具身化(embodiment)或者落地的过程。而其要表现的对象并不是左宏元、万绮雯或者罗纮武的身体或者三角,而是时间。

如前所述,钟表是毕赣最重要的一个意象,它像时间监狱的开门按钮。当它还在走动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对逃离时间监狱的希望,也还对过去、未来以及梦境存在幻想。《路边野餐》中的荡麦场景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实验,而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多层舞台,这种实验变得炉火纯青。这是一种将时间空间化的尝试。《路边野餐》的开头引用《金刚经》中对过去、当下、未来的论述已经将导演的野心昭示清楚。而它的英文名字“Kaili Blues”则暗示了影片许缓、低回、阴郁的基调。很可惜的是,这部影片虽然引起了关注,却没有完成导演最初的理想。
荡麦场景试图同时拍摄过去与未来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呈现。剔除因为经费不足造成的影像质量问题,《路边野餐》中镜头在对人物的追逐中的力有不逮的分叉、错位、变形,平面化的空间设定加上对一镜到底的执着导致了部分的影像冗余,也让接受者感到迷茫。由此可见,平面空间的设定难以完成时间的并置。

而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梦中的多层舞台成为了三层的立体空间,不仅并置了过去和未来,还多出了一个梦中的孩子的因素,难度更高。但是借由这种时间的立体化处理,终于完成了对过去、未来、梦中之梦(可能性)的并置。这大概也是曾经的婚礼导演在不断安排新人、家人及朋友的舞台调度中,意识领域开出的形而上花朵。在梦境中,罗纮武借由一个轨道装置摆渡到了待名(未生)孩子的坑洞中。这是梦中之梦、时间外的时间,因此,这个坑洞被安排在空间的最上层。梦中人在和孩子打了一场乒乓球之后,被他(它)骑着摩托车送出。此时,梦中的罗纮武有了一个清晰的意识,这是他的可能的、却终未出生的孩子,如果活着已经12岁。所以,在路上他顿然醒悟,孩子是一个鬼,他的心中之鬼。这种意识借着梦中的孩子的口说了出来。孩子的问题似乎将他从这层梦境中唤醒:你亲过嘴吗?接下来在孩子的帮助下,他乘着滑杆下降到了第二层,遇到了还没有到凯里的万绮雯(凯珍)。台球、游戏机、小镇青年的标配,野性又庸俗;野柚子,水果机中最难被击中的对象,当它被击中,就将会带着凯珍去凯里成为万绮雯。这是他对神秘的带给了他爱的体验的万绮雯的想象。当他们被铁栏杆挡住,想象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孩子的乒乓球拍为他们解了围——梦里是半逻辑的。于是,他们一起飞到了第三层,遇到了举着火把的疯女人。疯女人吃了很多苦,只有在养蜂人的身上才能感到丝丝的甜蜜。这个疯女人,她的最珍贵的东西——表,停了,一如罗纮武父亲葬礼时被卸下来的已经不再走了的钟。她的苦让罗纮武(白猫和罗纮武、白猫妈妈和罗纮武未出现过的母亲分别呈现出一种互文关系)连核啃噬苹果。而那匹马载着的、撒落一地的并不是苹果,而是酸甜交错的橘子。
有评论说,这部片子唯一能带来一点浪漫情愫的是最后燃烧着的小小烟花,当然还有那个似是而非的吻。这大概是喜欢元叙事的导演和观众玩得一个另类版本的“最后一分钟”的游戏。和类型片不同的是,这部影片的最后一分钟要营造的是爱的可能却短暂的氛围,而不是英雄救世的壮举。爱虽然迷离又短暂,但它是值得被停留的。
三. 梦的逻辑与叙事的边界
最后,我们谈一谈这部影片两极分化口碑的成因和它实验性的内质。
如果从画面的质感、演员演技和故事的流畅度来看,毕赣应该是一个需要重修的学生。(特别是汤唯的高配显然与凯里蓝调的整体氛围反差过于强烈,是不适宜的。)但是如果从影片中体现出来的哲学和诗性来看,又是一个少见的高手。正如陈凯歌所说,《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一部现象级的影片。与之相对地,也有评论者指出导演被大卫·林奇、王家卫、侯孝贤、塔尔科夫斯基复合体的虚名所累,拍摄了很多冗余的意象,同时,导演也有过度消费艺术电影之嫌(见李飞,《<地球之后的夜晚>的三重诱惑》,中国艺术报)。的确,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弗洛伊德的释梦都不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主题。这大概是其观众极为分野的根本原因,至于营销、被利用洗钱等,不是我们探讨的范围,此处从略。我们关注的焦点,在影片的内部机理。导演对于时间的空间化呈现的尝试我们前面一节也谈到了,这一节主要谈一谈边界。
在梦中,如果边界得不到突破,人就会醒来;如果得到突破,梦就会继续下去。因此,梦是半逻辑的,又必是无逻辑的,在一个长达七十分钟的梦里,边界问题就成了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同时,在电影文本中,凡是遇到梦与现实的边界问题,都难免一定程度上带来接受的阻滞甚至障碍。《香草天空》、《盗梦空间》,甚至《黑客帝国》都可以被当成典型例子。毕赣的长镜头自然带来了很多第一,虽然这有些过于元叙事了,但仍然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而他对边界的处理大概是使观众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的闪回、闪前、器物或空间的转场等处理方式叙事的痕迹过于明显,与其要营造的蓝调风格有违和感。在《路边野餐》中,导演在这个问题上束手无策,直接将梦境与现实的边界贯通。而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他选择了影中梦的叙述方式。

那个就要被拆迁的红灯区的综合体的设定,暗示着一直在尤利西斯般寻找中的罗纮武的理想行将幻灭。当罗纮武走进电影院,戴上了3D眼镜,他的梦就将在头脑/电影中开始。他要寻找的、等待的最后相会只有在梦里/在镜中。这一边界的设定使得前面的一个小时成为了后面长镜头的陪衬。而如前所述,这个长镜头事实上是一个被梦勾连起来的可能性、过去、过去的未来三层立体并置的戏剧。毕赣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用梦境将这同时进行的三场戏以运动中的人物勾连、调度了起来。这三场戏剧之间的边界分别是:轨道摆渡装置(从现实到彼岸坑洞)、滑杆(从坑洞或地府到过去的未来)、废弃监狱的栏栅(从过去未来到过去的过去、父母一代)、废弃监狱的外围栏栅(从立体舞台中退场的门,象喻着死亡)。事实上,这种对边界的使用又超出了古典主义戏剧中对机关和装置的使用。因为这个长镜头是同时进行着的,没有幕布的三场戏的复合体。戏剧的走位、机位、景别、叙述视角的综合考量远远超过了任何一部戏剧或电影,这从布景和道具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可见一斑。正是有了对边界的处理,才使这个梦境达到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和可能之境的无界融合,这种状态,就是被共时化和梦境化了的人的存在。
在梦境的末尾,过去的未来与过去的边界也被打破,红衣的凯珍和绿衣的万绮雯合二为一,爱在被烧毁的房间里再次停留,罗纮武的梦得到了实现。镜头在拍摄完拥吻之后自己走回了化妆间,画面定格在那支只能燃烧一分钟的小小烟花之上。在火星阑珊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时间、空间、爱情和情感上的纠结获得了它短暂的诗意。
从这个意义上讲,毕赣的电影既是一种元电影、又是一种元戏剧、还是一种元情绪、更是一种元生活。当我们谈论“元”这个概念,意味着对感受本身的感受,对思考本身的思考,在存在中谈论存在、在时间里展开时间。诗意的栖居不在于栖居地本身,而在于存在的人对这些元问题的顿悟。而将这种顿悟符号化,需要工程师般的耐心和设计师般的创意,也正是因为这种耐心和创意,值得我们这些接收者去解码这些元叙事的实验。虽然,它和任何人类的造物一样,也并非完美。
作者:王坤宇(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编辑:董牧孜;校对:翟永军
原标题:从《路边野餐》到《地球最后的夜晚》:时间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