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披头士很红。他们1965年去美国演出。当时鲍勃·迪伦刚有点名气。列侬特别喜欢他,就把迪伦叫到他的旅馆。迪伦就去了。迪伦旁边站着经纪人,但他随手从兜里掏出一把大麻,就开始抽。当时披头士的经纪人就很紧张,因为周围有‘朝阳群众’。
迪伦很惊讶地问,‘你们没抽过吗?’列侬说,‘我们真的没抽过。’迪伦说,‘哎,你们不是有首歌吗?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就高了、高了、高了(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列侬当时特别不好意思,因为那是‘I can’t hide’,我没法躲藏。迪伦听错了。
但是,披头士这几个人里,列侬比较叛逆。他一看有同龄人在抽,于是自己也抽。但他要提防‘朝阳群众’。他就让经纪人拿浴巾把所有门缝和窗缝都堵得严严实实,才开始点了第一根大麻烟。也就是说,是迪伦把披头士引坏的。” 袁越分享了一则八卦,引起了现场阵阵笑声。”

披头士
也许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袁越这个名字,但不少人熟悉他的网名“土摩托”。他是生物学硕士、乐评人、作家、《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他曾就转基因问题跟众多微博大V“车轮大战”;他也发表过《土摩托看世界》系列,写他的旅行见闻;他也写过科普图书《生命八卦》;也写过嘻哈文化史《20世纪最后的草根艺术》。而袁越的《来自民间的叛逆》则是他最早的一本书,也是国内较早的系统介绍美国民谣和嬉皮士文化的著作。
1月5日,在《来自民间的叛逆》再版之际,读库邀请袁越和台湾乐评人马世芳在郎园·vintage举办了一场“嬉皮流水·嬉皮士文化的精神内核”的座谈。他们以六十年代美国民谣为切入点,剖析嬉皮士文化对现代生活造成的影响。
嗓子不是评判音乐的唯一标准
马世芳十几年前就开始从豆瓣里看大陆年轻人写的乐评。他曾震撼于大陆年轻人经常一写一大篇,宏论滔滔。但是在震撼感过去之后,他发现很多文章的基本假设都是错的。很多文章的激情胜过说理。那是因为在一个资讯相对比较荒芜的时代,大家写文章必须要有这样的激情,才能补充资讯不足的劣势。
但当马世芳读到《来自民间的叛逆》时,他觉得耳目一新。因为袁越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考证详实,有凭有据,前后逻辑关系很清晰。“那么厚的书,全都是干货,”马世芳说:“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没法像理科生那样下死功夫,我觉得我还是写写我的抒情文章就好。”

《来自民间的叛逆》作者: 袁越,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出品方: 读库, 2018-11-6
在那个时代,袁越“孤军奋战”。在完稿之前,也没有读者给他提过意见,而且他同时还在念学位。马世芳很好奇,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热情,让他对美国民谣和嬉皮士有着如此强烈的表达欲呢?
面对马世芳的盛赞,袁越有点不好意思。他说,他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有着理科生的逻辑,而是因为他真的喜欢,书里有刺激到他的地方。袁越在出国读书之前就很喜欢音乐,比如崔健、罗大佑、童安格。他在中学时也听过鲍勃·迪伦,如《答案在风中飘》。等他到了美国时,袁越买了一个鲍勃·迪伦的精选集,放给他的美国室友听。他室友跟他说,“《答案在风中飘》不好听”,就跳过了放另外一首歌。“我当时非常震惊。”袁越说,“我当时的世界观是,音乐是有好坏的。这音乐是好的,我们肯定都会喜欢,这音乐不好听,就肯定没人喜欢。我很惊讶于发现这个人怎么喜欢这么怪的歌?吵吵闹闹的,也不好听。”

鲍勃·迪伦
袁越回想,这也许是在那个年代,美声唱法、民族唱法很流行,大家对歌手的嗓子有着很高的要求。到现在,电视节目选歌手,都是选谁唱得好。这个美国室友给了他世界观上的刺激。“原来这个世界比我想得要复杂得多。我们的音乐审美也很复杂,嗓子不是判断音乐的唯一标准,嗓子的好坏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迪伦早期的那些歌,有大量布鲁斯在里面。那时迪伦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嗓音却非常老。那是因为他想学美国老黑人那个嗓音。旋律也不是很悦耳。而不悦耳只是不符合我们的审美观”。袁越说。这也是那时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在那个资讯相对荒芜的时代,他花了七年,想将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叛逆的美国民谣?
其实一开始是一种传承
嬉皮士则更大地冲击了袁越的世界观。“嬉皮士反对一切的东西,我们赖以为自豪的东西:勤劳、爱家庭、忠贞不二、爱国,所有这些都不对了,这些是我更大的刺激。”
袁越认为,现在奉为嬉皮士经典的《在路上》,其实早在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类似的文学了。因为美国的地方非常大,有很多荒野,公路十分发达,汽车旅馆很多,所以能生活在路上。此外,对于美国民歌来说,美国的乡村文化很强势,再加上黑人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乡村音乐就这样被孕育着。袁越举了一个例子,在《泰坦尼克号》中,露西在三等舱里面看到的舞蹈,是爱尔兰的舞蹈,这也是美国民歌最早的基础。
马世芳认为,最早的美国民谣复兴运动,并不是为了创新和叛逆,而是为了传承。欧洲的乐器随着移民被带到了北美洲,因为漂洋过海,他们只能带一些小的,比如小提琴、斑鸠琴和吉他。然后他们发展出了不同于欧洲民谣的音乐形式。在底层,黑人白人分隔的界限并不分明,他们的音乐互相影响渗透。这些在猫王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在罗斯福新政里面有一项政策,就是采集民间歌谣,这让美国意外地留下了民间音乐的素材。因此在五六十年代,那一辈年轻人忽然发现,他们爷爷奶奶那一辈有着许多原始和本真的音乐,这变成了他们“精神的原乡”。于是,那些民谣歌手会去模仿那些老黑人。所以,最早的美国民谣复兴运动,他们念兹在兹的不是创作振聋发聩的原创曲,而是想把老祖宗断了的歌谣传下来,他们精细到连腔调都要模仿。后来,这才成为他们原创的养料。这是一种通过“返祖来叛逆”。马世芳认为,这跟二战后,美国变成一个强国的过程中,丢掉了一些美国年轻时代的珍贵价值观有关,所以年轻人要从爷爷奶奶那一辈中去寻找养料。
流行文化崛起其实与政府背后的推动有关
袁越认为,美国当时作为新兴霸主,要挑战英国的文化霸权,所以美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我们看到很多来自民间的文化,其实这背后都有政府的推动。
马世芳表示赞同,政府的角色其实远比大家想得要大得多。罗斯福新政对民间音乐的保留,使得国会图书馆有很多珍贵的民谣录音。马世芳回忆道,他在大学时代听的很多美国早期的民谣,就发现它们很多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
袁越也提到,英国政府其实也干过类似的事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地位眼看要被美国超越,火箭、坦克和飞机比不上美国,但英国人能够输出文化。披头士和滚石乐队等“英伦入侵”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
马世芳认为,其实英国当时是一个没落的帝国,给大家的印象很陈旧。但是后来,伦敦就成了全地球最“潮”的首都。这是因为英伦音乐成了全世界年轻人最时髦的东西,这也带动了时装、电影和其他周边文艺的火爆。英国政府发现,文化输出有钱赚,还能赚外汇,因此也用国家力量支持。其实,这就是现在我们各国都在学习的文化创意产业。
而且,英国政府对摇滚巨星们征的税是极其不人道的。披头士有一首歌,叫《Taxman》,这是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写的。第一句就把税率唱出来了,“Let me tell you how it will be,There's one for you, nineteen for me”。(让我告诉你该如何缴税,你留下1元,我收走19元。)马世芳调侃道,也难怪那么多英国巨星要逃税。
科技进步也改变音乐的形式
马世芳补充道,探讨六十年代民谣的流行的原因,我们不能忽略科技进步的力量。19世纪末,留声机才开始商业化。而广泛使用电力驱动的录音器材,要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而且,录音器材的体积,要从庞然大物到可以塞进一辆汽车的后备厢里,才能让田野录音变得可能。这也是罗斯福新政时,收集民谣的科技条件。
此外,还包括麦克风的技术革新,也影响了唱歌的方法。在没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们唱歌,像山歌,都是得扯着嗓子喊。包括很多地方戏,一定也是一嗓子喊出来,因为要让最后一排也听得见。包括爵士乐,一开始为什么铜管乐器会用得比较多,也是因为音量大。等麦克风出现之后,人类第一次能捕捉到更细腻的声音,甚至连呼吸换气都可以是歌的一部分。爵士乐也因此多了很多钢琴和拨弦乐器的元素。
而且,音乐载体的革新也影响歌曲的长度。在每分钟45转的单曲小唱片时代,A面和B面都只能装一首歌,每首大约三分钟。但是为了音质更好,很多歌控制在两分钟左右。A面一般是主打歌,B面一般是附赠的一些不太好卖的、奇奇怪怪的歌。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有“B-side”(B面)这种说法。
后来,随着LP唱片的普及,一般唱片的一面可以放二十几分钟。这就让一些音乐人有机会把LP唱片变成他们创作的载体。他们用唱片的整整一面去创作曲子。他们不走电台“打榜”的路子,而靠卖唱片赚钱。此外,fm电台的革新也影响了音乐的形式。虽然fm电台传播的范围弱,但音质好,可以放立体声,有些DJ就开始利用fm的系统,播放一些不“打榜”的歌,比如他们会播放18分钟的歌,或者播放五小时的实况音乐专辑。这样,一个地区的亚文化社群意识就被慢慢培养起来了,围绕电台,亚文化群体就形成了一种向心力。
另外,音响系统的革新也让户外摇滚音乐节变成可能。当时很多摇滚现场的实况,都是在俱乐部录的,因为场子大了,音质一塌糊涂。在1967年,人们才开始用当时最好的音响来尝试户外摇滚现场。有了1967年的试验,才有1969年的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袁越提到,那个年代的很多歌曲前奏都很长,是因为那是为抽大麻的人服务的,他们有些人要保持五小时的“high”。所以,音乐的形式跟当时所有的因素都有关,不止科技。现在的歌,前奏一般都不能太长,因为大家手指一划就能换歌了。
毒品与民谣怎么勾连上的?
马世芳首先声明,我们首先要厘清“Drug”的含义。尼古丁、咖啡因,其实都是药,只是不违法而已。以前很多乐手会用减肥药提神,因为早期的减肥药里面,含有安非他命。所以,他们会吃“Pill”,不然没法连续演出。而像大麻和LSD这样的致幻药的出现,对嬉皮士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LSD背后也跟美国军工业有关。
袁越说,他开始也很惊讶于LSD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嬉皮士文化应该是反主流、反政府的,怎么会跟CIA有关呢?在五十年代时,美国感到自己在创造力上落后于苏联。因此美国政府投资了科学机构,研究如何提升创造力。其中有一派科学家认为,药物可提升创造力。LSD就是他们合成的药。这种药物,只用十微克,就会产生很强烈的幻觉:你会觉得周围的东西都是活的,你会听到颜色,看到声音,脑子会很混乱。
当时蒂莫西·利里对LSD非常感兴趣。袁越说:“这个人是美国嬉皮士文化的‘guru’,翻译成现在的话是‘总仁波切’。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他以他的教授身份去推广LSD,当时还没禁。因为有哈佛背书,所以有人相信。他把音乐往这个方向带了带。”在1967年,他在旧金山的“Human Be-In ”的集会里演讲。他把当时民谣圈的人,诱导变成嬉皮。经过这次洗礼之后,民谣歌手的头发越留越长,也渐渐不洗澡不刮胡子了。

蒂莫西·利里
袁越调侃道,虽然鲍勃·迪伦受得更多是“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发现,在迪伦刚出道的时候,他的第一张专辑封面是一脸“小鲜肉”的模样。第二张专辑封面搂着女朋友,但还是“小鲜肉”模样。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到“blonde on blonde”后面就“疯了”。披头士被鲍勃·迪伦“带坏”之后,他们也从“小鲜肉”变成了“老大叔”。我们可以对比他们“The Red Album”和“The Blue Album”就知道了,那是在同一个酒店拍的。

“The Red Album”

“The Blue Album”
袁越还提到,《飞越疯人院》的作者肯·凯西(Ken Kesey),跑到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研究所里面当LSD的实验者。在实验结束后,他在那里当清洁工,偷LSD回家服用。他写的《飞越疯人院》的背后就跟LSD有关。在他赚到稿费之后,他在旧金山买了房子,经常邀请文艺圈的名人来开LSD派对,而他们服用的LSD,由斯坦利三世(Augustus Owsley Stanley III)那里买来的。
斯坦利三世是《绝命毒师》里“老白”的原型,不同的是,“老白”懂技术,斯坦利三世找伯克利大学的高材生帮他制作LSD。他对LSD有宗教般的狂热,他制作的成品比很多大公司制作得还好。而且他给自己的LSD定价2美元一剂,从不涨价。他免费散发的比卖出去的还多。比如,在他的派对里,他给每个发的苹果里都打一针,门把手都撒一点,所以很多观众都被动的“high”了,加上他买了最好的音响系统,放摇滚歌曲,让这种体验无限放大。在这样的带动下,波澜壮阔的反主流文化才开始兴起。
没有嬉皮士,
就没有今天习以为常的很多观念
袁越认为,我们不要被主流的宣传蒙蔽,只是觉得嬉皮士就只是避世、不洗澡、不劳动。其实嬉皮士的很多观念变成了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观念。比如,服用了LSD的人,因为大脑里的神经细胞链接方式在乱搭,很多物理经验会不存在,你会觉得世界都是活的、一体的,而世界同一,在各国纷争的时代,是比较新鲜的想法。
马古利斯,线粒体内共生学说的提出者,其实背后就受嬉皮士运动的影响。她认为真核细胞的线粒体不是慢慢进化出来的,而是被一种微生物吞进去的细菌的后代。双方各取所需,相互合作,最终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她相信不同生物之间绝不都是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互惠互利同样也是生物进化的主旋律。因此她认为,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每个物种相互之间都有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琳·马古利斯
旧金山嬉皮士运动元老级人物斯图尔特·布兰德,曾在旧金山发起过一次公民请愿活动,敦促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向全世界公布宇航员从太空拍下来的地球照片。1968年,NASA公布了“阿波罗8号”上的宇航员拍下的一张地球照片,这张照片让大众意识到地球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如果不用心保护,人类就没地方住了。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国际地球日”,增强了人们的环保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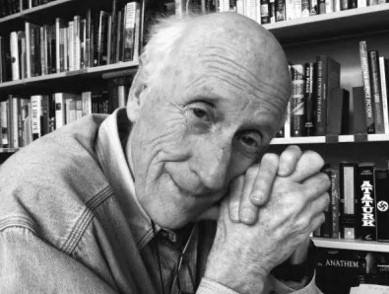
斯图尔特·布兰德
袁越指出,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在美国,环保、同性恋、不上班、丁克、不结婚、男女平权、种族平权等似乎都被广泛接受,但这些观念在美国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还是禁忌。这都是六十年代那批人的努力换来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那批人的过程和经历。他们还直接影响了当代的硅谷精神,包括互联网的开放性。
但袁越并不认为嬉皮士文化就是百分之百好的。震惊美国的“曼森杀人案”就是一个例子。凶手曼森随机杀人,让警方摸不着头脑。他是披头士的粉丝,他认为披头士的《白色专辑》给了他信号。袁越认为,这是从一种粉丝文化,变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马世芳则认为,其实他误解了披头士的意思,让那张专辑变成了“神谕”。此外,1969年,滚石乐队演唱会上发生了惨案,被世界上第一部摇滚纪录片《Gimme Shelter》记录了下来。这或许是嬉皮士时代结束的标志。因为很多人心中“爱与和平”的信念在那时破灭掉了。
现如今美国的嬉皮士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袁越曾探访过北加州的一个嬉皮农场,这个农场从1968年就开创了。农场里面住着很多好玩的艺术家。他们与世隔绝,一年下山一次。在山上,他们养鸡养鸭、挤山羊奶。嬉皮士们现在已经跟主流没什么联系了。但是他们曾经的理想和观念却早已融入了主流。袁越想记录的就是这些当年民间的“刺头”,而民谣只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手段罢了。
作者:徐悦东;
编辑:覃旦思;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