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的苏阳前年办了艺术展,去年又出了文集《土的声音》。早在“土味文化”流行之前,他已经在唱土得掉渣的歌。他的音乐《贤良》《像草一样》在城市文青之间有口皆碑,在这次的跨界书写之中,他记录了自己行走的民歌笔记,也追溯了自己从童年里生长出来的创作根源。

苏阳,民族摇滚音乐家。他将“花儿”、“秦腔”等西北民间音乐及传统曲艺形式,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和解构,经由西方现代音乐的理论和手法,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
苏阳的音乐是黄河流域典型的粗犷表达,然而他人却是打南方来。父母从江浙来宁夏支援边疆。7岁那年,苏阳也来到黄河边上。“早晨起来,门推开一看,我去,两天以前还是浙江小镇青山绿水。如今一推门就是一片黄色,等于就是一片荒漠。”
生活特别能塑造人的美学,成为新一代宁夏人的苏阳,也成了黄河水的组成部分。厂矿长大的孩子,身边的本地人也不多,他的普通话最能体现出“飞地”的混杂:宁夏口音里又带着东北人、上海人的腔调,一个字,乱。与工业小城的生长同步,苏阳的童年也从一条单薄的同心路逐渐热闹起来。逃学,逃离工厂,去工地打工。1969年出生的苏阳,跟贾樟柯差不多大,改革开放之初还走过穴,电影《站台》里所有故事他都经历过。
“干过好多活,瞎混。”80年代少年的人生目标就是生存下去,喜欢音乐就自学弹吉他唱歌,没想到后来曲曲折折跟西北的民歌有了连结,从花儿、秦腔等民间音乐里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唱出了“像草一样”的一代人的生活。《土的声音》记录了这段他自谦是“没有任何自觉”的往昔岁月,以及他最具创作自觉的音乐是如何在土地上长出来的。
“我的故事一点都不励志,少年时迷迷茫茫就过来了。知道后来发现,左邻右舍谁生了孩子,明天谁结婚了,有人走了,这些生活才是最应该被表达的。”“我对世界化的理解是什么?”苏阳说,“走过好几个国家,才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滴水,每个人可以表达他所在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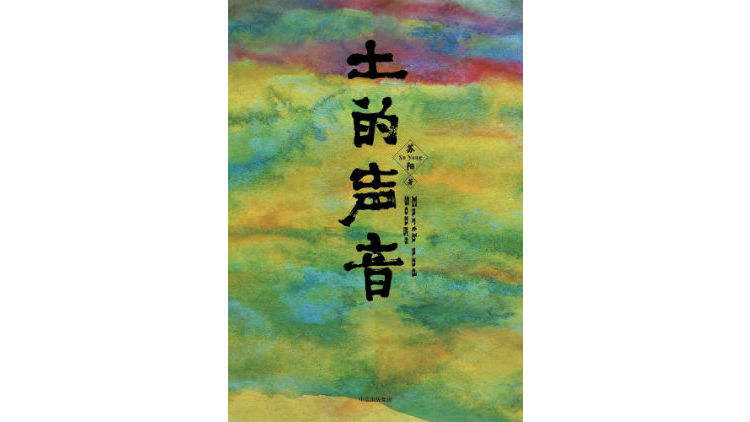
《土的声音》,苏阳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
新京报:《土的声音》记录了西北民间音乐人的故事,你做民歌采风的自觉和冲动来自什么?
苏阳:一开始是出于音乐的考虑。2000年初,我的音乐走到了令人厌倦的套路。我写过几十首歌,但如果把唱词去掉你听着就是一个国外乐队。我想应该找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听。因为一些偶然的机会我开始接触民歌。
民歌从技术上没什么可说的,但它改变了我对音乐的感受,对人和音乐的关系的认识,意识到歌唱的心态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觉得新鲜,发现了一种不一样的表达方式。慢慢接触地多了,你会发现在这东西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是每个人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新京报:花儿、信天游、秦腔都是从西北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年轻一代在电视上看到的往往是形式化、符号化的美声唱法,有距离感,难以被打动。你觉得民歌里面仍然鲜活的东西是什么?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苏阳:中国《诗经》的“国风”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比兴传统。这些中国的歌词后来转化成诗的传统。诗以造像的形式用文字画画,西方人叫意象。这种以图像建构文字的方式对我启发很大。以这种视角观看今天的城市,其实跟旧时农民观看他的土地和山水是相同的。民歌改变了我建造意象的方法,让我感觉到是在表达自己。这个过程也是在改变自我,回到更深处的自我。《贤良》《新鲜花儿开》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沿用民歌(即便沿用得不好)。远古时代起,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抒写自我。
民歌最大的特质是回到母语的表达方式。我在飞机上去意大利,听见注意事项播报的声音巴拉巴拉特别快。此前我去了一趟中国南方,发现上海人说话语速就没那么快。而从海口往南边飞时,语调是柔和的、低沉的。每个民族和地域的语言特性及其背后的音乐性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强调一定要用母语去建造意象,去建造你的节奏和旋律。西北话和南方语调节奏都不一样,这种东西无法统一,在这一点上恰恰是不可以被统一的。
只是民歌这种表达需要有一种能跟今天接气的形式。不用美声,而是用吉他,用更日常的声音弹唱。这样的表达我认为是有效的,它是我们自己的,是今天的,而不是存在于过去的东西。我的文字受民歌影响,从2003年开始,尤其到了今天,都是用图像的方式去建构意象,用母语的节奏和旋律去创造简单的旋律,以达到所有人在情感上都能够理解的东西。其实全世界的情感都差不多,男欢女爱,讨厌战争,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希望得到爱,得到照顾,仇恨,自私……这些情感都是通的,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这是我今天对民歌的理解,可能明天有看新的思考和实践,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新京报:民歌所依存的农耕畜牧文明被现代世界边缘化了,民歌在当代生活中消失似乎也合情合理。你怎么理解这种正在消亡的艺术表达方式,及其所依存的生活本身?
苏阳:消亡的只是形式。民歌从侧面反映出人和土地的关系。人对土地的依赖感很多时候是不自知的。几千年来,人都生活在土地上,人是来自土地的。土地消亡,但情感不会消亡;生活的方式变了,歌唱的方式也变了,今天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在西北那样的地方生活了三十年,只要出生时见识过,你的一生就会跟土地是有关联。即便你后半生都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笼罩的空间,对土地的情感也不会被抹杀。民歌这种音乐形式就牢牢挂靠在这种生活模式和情感里面。
新京报:你会缅怀这种消亡吗?或者会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心态去延续你的民歌创作吗?
苏阳:民歌自然地来,自然地走,这是一个时代正常的循环,艺术也存在于循环之中。民歌的形式逐渐消退,我无法担负保护的责任,我当然希望有机会这样做,或者在客观上达到了这种传承关系,但我的初衷是唱一首我心底的歌,一首能打动自己、能表达情感的歌。我到底不是一个农民,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从母体里面吸收营养,我才知道怎么唱下去。大家会说你这是摇滚乐或者民谣吧,其实不重要,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表达感受。重要的是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宁夏人,一个黄河边的人在唱歌,他是有辨识度的,而且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也惋惜民歌的消亡。民间艺术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民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民间的绘画和书写,这些东西都在逐渐消亡,甚至是以过度消费的方式消亡。不是它没了,它死了,而是它的精神死了。它曾经的辉煌不是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被继承,而是作为商品形式被过度开发,形式背后真正与土地的连结你看不到了。我觉得这是最可恶的一种消亡方式。
作者:董牧孜
编辑:覃旦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