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模仿说原本是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美学主张,不过,在伊丽莎白·普莱特约翰看来,19世纪英格兰艺术的蓬勃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古典艺术的模仿与创新。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一位极具传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他为南非所做的贡献为人所称颂,却也引发了不少质疑。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也许很难说清,但他在狱中27年所写下的一封封信,也许可以让我们能够从最为直接的材料中,走进这位传奇人物的心灵世界。
亚美尼亚人是欧洲南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民族,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和艺术为人所惊叹,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编辑出版的《亚美尼亚:中世纪的艺术、宗教和贸易》展览目录中,也许我们可以看到最为丰富的藏品和亚美尼亚曾经创下的辉煌奇迹。当然,我们也可以阅读一下小说,出生在列宁格勒(现彼得堡)犹太家庭的加里·施特恩加特,七岁移居美国,独特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创作视角,曾被英国杂志评选为美国最杰出的青年小说家的施特恩加特,这次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绝对美国的故事——当然,故事的主人公,对于美国来说,依然不过只是个游客。
模仿带来艺术的创新?
19世纪,随着博物馆的兴起,特别是1824年伦敦国家美术馆的成立,以及大量艺术复制品出版物的普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古典艺术变得前所未有的易于接近。受桑德罗·波提切利、扬·范艾克、迭戈·维尔·茨奎兹等人作品的启发,英国艺术家们通过大量的模仿,以及创造性模仿的过程,将当代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伊丽莎白·普莱特约翰分析了批评家、策展人和学者对昔日艺术大师的解读,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在忠于模仿古典艺术大师创作时,最具独创性,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现代画家与早期绘画大师》这本书涵盖了从拉斐尔前派到维多利亚早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脉络,追溯了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爱德华·伯恩·琼斯和威廉·奥本等艺术家从古典艺术中汲取精华,并由此创作出19世纪后期最为伟大艺术的方式。
这本书以福特·马多克斯·布朗(Ford Madox Brown)创作于1852-1855年间的《最后的英格兰》(The Last of England)开篇。这幅画描绘的是一对夫妇乘坐拥挤的船只,离开英国前往澳大利亚。这样的远行在画家生活的时代是常见的,自1820年以来,有超过一千万的英国人前往殖民地和美国,这幅画是布朗在英格兰创作的最后一幅画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并因此奠定了他作为拉斐尔前派代表人物的地位。

福特·马多克斯·布朗的画作《最后的英格兰》
在这幅画作中,他选择刻画的角度是极为巧妙的,甚至还颇为尖锐,如同现代社会的调色板:整幅画作之中,船只的栏杆上挂着紫色和绿色的卷心菜,画面的中心位置则是明亮的玫瑰色和一抹淡紫色——一顶被风吹开的丝绸帽子,以及被隐藏在衣服和手指之后的婴儿。紧绷的构图被压缩进一个近乎圆形的框架之中,船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颠簸的场景为这种并不稳定的选择提供了某种暗喻式的解释。画面中的两个人物,正是以布朗和他的妻子艾玛为原型,他们的服装表明,他们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当然,他本人曾经表示,这一画作“没有参照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的艺术,我想使这一场景被表现得如它将要出现的那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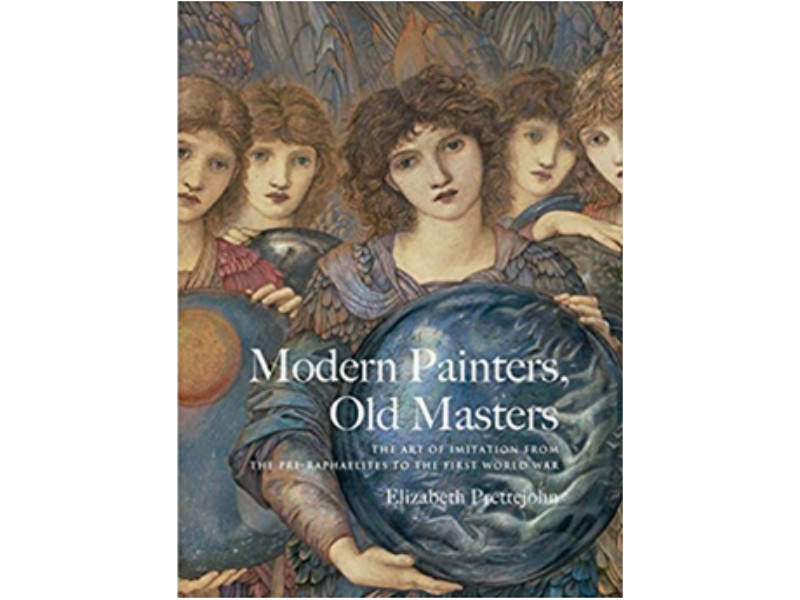
《现代画家与早期绘画大师:从拉斐尔前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模仿艺术》(Modern Painters, Old Masters: The Art of Imitation from the Pre-Raphaelit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作者:伊丽莎白·普莱特约翰(Elizabeth Prettejohn),耶鲁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曼德拉和一个男人的英雄主义
2018年是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诞辰一百周年,显然,他是二十世纪最具有启发性的历史人物。1990年从监狱获释后,曼德拉在一次演讲中描述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他为领导这场斗争付出了一切。“我们站在地上,而不是跪在地上,赢得了和平,”他自豪地宣称。
1943年纳尔逊·曼德拉加入主张非暴力斗争的非洲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1960年南非政府宣布这一组织为非法组织,数周后,南非军警在夏普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五千名抗议示威者射击,惨案共杀死了约70位抗议者。为此,他联合成立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并避免以人为目标。1962年,他秘密访问了几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并前往英国伦敦,寻求反对种族隔离的支持和资金。回国后不久,他就被捕了,当时的政治对手以“煽动”罪和“非法越境”罪判处曼德拉5年监禁。第二年,他再次被起诉,这次的罪名是“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1964年,曼德拉45岁,被判终身监禁,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很多人都认为他会被判处死刑。在那些日子里,很少有人能自信地预测到,在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将会在一个黑人的领导下,以他引以为豪的和平方式取得胜利。建立在法律上根深蒂固、暴力实施的种族隔离和白人特权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强大。
在纳尔逊·曼德拉被监禁的10052天里,这位南非未来的领导人不屈不挠的给监狱当局、其他活动家、政府官员写了很多信,最令人难忘的是,还写信给勇敢的妻子温妮和他的五个孩子。现在,这些信件还保存有255封,其中许多从未发表过,这些信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特殊的见解,让我们得以了解曼德拉是如何在几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保持内心的灵魂以及他是如何同外界进行交往的,而这个外界,也因为他的困境,而愈发愤怒。
这些由纳尔逊·曼德拉创作于监狱之中的信件,被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组织,根据他被判刑囚禁后的四个关押场所来区分,开始于比勒陀利亚当地监狱,1962年,曼德拉被审判后曾被关押在那里。1964年,曼德拉被带到罗本岛监狱,在那里,只有家人的来访和来信才能使他的生活稍显轻松。十八年后,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莫监狱,这是开普敦郊外的一个大建筑群,里面有床和更好的食物,但在那里,他和四个战友被关在屋顶的牢房里,远离监狱里的其他人。最后,1988年,曼德拉被关进了维克多·范斯特监狱,一直被关押到1990年2月11日获释。
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附有纳尔逊·曼德拉一些真实信件的传真件,揭示了这位接受过训练的律师,是如何倡导囚犯人权的。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他写信给女儿,“我有时希望科学能创造奇迹,让我的女儿可以得到她丢失的生日卡,并有幸可以获知她爸爸爱她”,显然,他意识到,他发送的照片和信件失踪了。最为痛苦的是1969年的一封信,当时曼德拉被禁止参加他母亲和儿子特米比的葬礼——只被允许通过信件来安慰家庭成员。
无论是面对因坚定地支持他而同样被监禁的妻子,还是概述一种能够引起今天共鸣的人权哲学,纳尔逊·曼德拉的狱中信都揭示出一个男人的英雄主义:在面对非同寻常的惩罚时,拒绝妥协的价值观。显然,正是这些信件,让我们将曼德拉定位为二十世纪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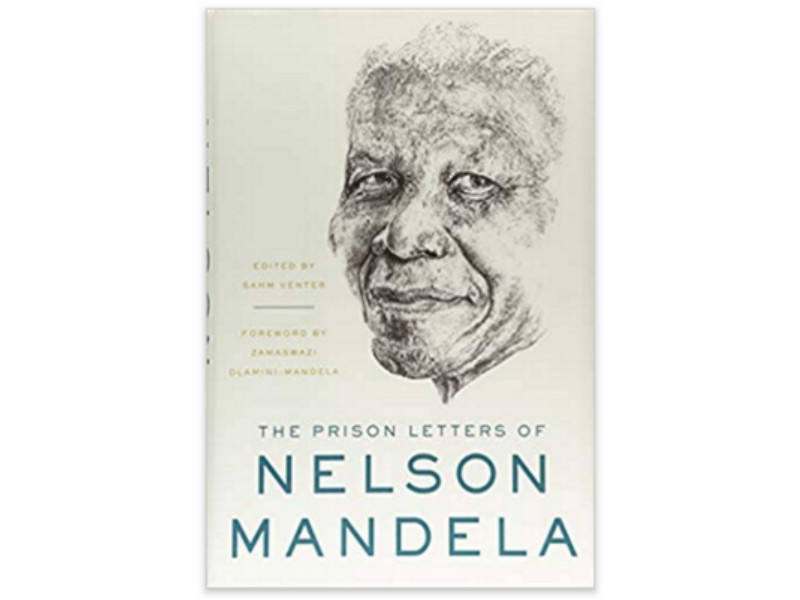
《曼德拉的狱中信》(The Prison Letters of Nelson Mandela)编者 萨姆·文特尔(Sahm Venter)利夫莱特出版社,2018年7月
亚美尼亚人的迷人艺术探索
亚美尼亚人是欧洲南高加索地区的古老民族,在中世纪,连接东西方的亚美尼亚王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迷人艺术探索。
作为第一批正式皈依基督教的人,亚美尼亚人委托并生产制作了令人惊讶的宗教物品,以及大批令人信服的艺术品,重新定义了中世纪亚美尼亚人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历史,这其中,包括雕刻、礼仪家具、精美插图手稿、镀金圣物、精美纺织品、印刷书籍等。亚美尼亚处于连接东西方贸易路线的中心,曾经是塞尔柱,蒙古,奥斯曼和波斯霸主的主要国际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拜占庭和欧洲十字军国家的强大盟友。这本书经由一批国际学者撰写,并且得到了亚美尼亚宗教领袖的支持,将成为关于中世纪亚美尼亚艺术和文化的权威文本。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作为拜占庭艺术的馆长,海伦·埃文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展览。但在最近的展览“亚美尼亚!”中,她再次超越了自己,这次展览的成功举办,有赖于迄今为止令人们意想不到的高质量展品收集。被亚美尼亚人称为哈奇卡尔(khachkars)的十字架石并不是最受期待的,在亚美尼亚高地的墓地和神殿中,它们曾经像巨人一样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十字架已成变成了一棵生命之树,深深根植于远古近东的想象世界。和大部分文明一样,古代亚美尼亚人先是自然崇拜者,后来转变为对神的崇拜。
虽然人们被那些充满活力的哈奇卡尔所吸引,而忽略这些手稿,但其实它们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所产生的。每个抄写员背后都有着不容忘却的英勇决心。每份手稿都带有抄写员最终添加的评论——希望读者们可以记住他。通常这些书籍为福音或者赞美诗,同哈奇卡尔一样,手稿来自同样一个社会。我们在为那些金箔上色彩明亮的美丽所疑惑时,我们也应该记得那些卑微的文字背后所向我们展示的苦难世界。一个抄写员在厄津坎所写的福音书副本中注释中说: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我在写这篇(手稿)的时候搬到了五个不同的地方。哦,兄弟们,不要怪我的书法粗糙和错误……那些逃走的人,被寒冷的天气吞没了,还没有到我们的地方就断了气。听了这一切,又看见这一切,又甚忧愁,就写不出来。”
用一位现代学者的话说,这些抄写员是“亚美尼亚文献的无名英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牧师,许多人都是已婚的小牧师,他们在家庭中传授自己的技能(有时传授给他们的女儿)。为什么需要记忆的工作强度如此之大,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世纪的亚美尼亚人要记住的历史不止一段。在这次展览中,我们看到了牧师和基督教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从现存的基督教前习俗,和口头传统并存的史诗世界中汲取了奇特的活力。
亚美尼亚虽然一直与罗马保持联系,但它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却向东看伊朗。伊朗的社会等级森严,由武士家族统治,他们最大的乐趣一直是狩猎、宴会和战争,他们的记忆(由吟游诗人承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中东。在传统的记载中,特拉达特四世曾被亚美尼亚人的使徒,光明会的格雷戈里所诅咒。他变成了一头野猪,作为悔罪者出现在教堂里,流下了极为丰富的眼泪。在展览中,我们看到这个耷拉着脑袋的人,站在五世纪亚美尼亚的一根大方柱上,在一份晚期手稿上,他跪在崇拜者中间。这个传说深深植根于亚美尼亚的传统中,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忘记,但在当时,它具有惊人的独特性。

《亚美尼亚:中世纪的艺术、宗教和贸易》(Armenia: Art, Religion, and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编者 海伦·C·埃文斯(Helen C. Evans),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18年11月
一场漫无目的的讽刺
加里·施特恩加特的作品,似乎都是一些漫无目的的讽刺作品,一只脚扎根在真实的纽约城周围,另一只脚却在前苏联的废墟和财富中挖掘。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俄罗斯社交新丁手册》中,他描述了弗拉基米尔·格什金在25岁生日前几乎平分的生活——他在俄罗斯生活了12年,又在纽约生活了13年——这就是他的生活,必须合二为一。在小说里,弗拉基米尔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都追求着爱情和成功,故事的跨度从女朋友上东区父母的温文尔雅、慷慨虔诚,到东欧城市布拉格那一群穿着运动服的黑帮那令人愉悦的贪婪和残暴。
《荒谬斯坦》是施特恩加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米沙和弗拉德一样,出生在前苏联,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体重325磅,是俄罗斯第1238位富豪的儿子。米沙喜欢说唱音乐,也喜欢一个自称有一半波多黎各和德国血统,一半墨西哥和爱尔兰人血统的女孩,“但我主要是在多米尼加长大的。” 施特恩加特的第三部小说《超级悲伤的真爱故事》中的主人公出生在纽约,在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名移民。这部书信体小说发生在未来的纽约,这个城市已经称为一个以金钱为权力的威权政权。
《成功湖》是加里·施特恩加特的最新一部小说,故事的发生场地在美国本土,特别是在灰狗巴士车轮下滚动的美国。巴里·科恩是一名对冲基金经理,为了逃离他在纽约极其富有的生活,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参加了一场“红州公路旅行”(red-state road trip)。《成功湖》以一部美国书自居,但巴里在美国,其实只是个游客,不过对于纽约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好故事。纽约的贪婪凌驾于巴里所到访过的其他地方之上。巴里用他所收集稀有手表的数量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所居住的公寓就在鲁珀特·默多克楼下,巴里几乎是一层一层的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在与三楼的邻居们共进晚餐时,巴里会抬头看看他们的两居室公寓究竟估价几何:区区380万美元,还不到他在楼上那套公寓的五分之一。巴里当然不是一个好人,就像施特恩加特笔下的大多数英雄一样,他那令人讨厌的品质是如此完美,以至于称为一种近乎令人同情的天真,他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表现在读者眼中成为了人性化的一部分。他的妻子西玛是一位律师,同其他新时代的模范妻子一样,她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把他描述为“孩子气的”、“傻乎乎的”、“事先演练好的”、“会拍马屁的”、“来自老虎旅馆”的人,但她也看到了“拼命挣扎”、“害怕犯错”、“总是提防受伤”的巴里,或许他们是同一类人。
有趣的是,巴里和加里·施特恩加特笔下的其他前辈不同,他更加具有魅力: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有着游泳运动员的体格,不像施特恩加特笔下的其他主人公,肥胖而油腻。当然,《成功湖》比他早期的小说更加情绪化,并不那么华丽,但这依然是一个精彩、有趣,又令人心酸的回忆。

《成功湖》(Lake Success)作者: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兰登书屋出版公司2018年12月
作者: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编辑:沈河西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