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3日是老舍诞辰120周年。老舍的一生, 大概可用几个片段草草概括:没落贵族,苦读成名,文艺斗士,入庙堂,投湖自尽。新中国建立以来,老舍被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在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他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通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很早就取得了文化秩序中的“经典”排位。
有关老舍的研究如今多不胜数,资料繁多,角度亦丰富。除了他的文学及语言本身的魅力,我们透过老舍的写作关怀及人生际遇演变,亦可窥见上世纪文艺人士与大历史之间缠绕的关系。而老舍之死,在上世纪80年代又成为知识分子命运的神话叙事之一。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老舍研究里,有一本很“灵”的出自香港导演胡金铨之手,叫做《老舍和他的作品》。这本书非常任性,作者放言不论分析或评论“完全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不理别人的意见”,“立论只凭个人好恶,不理’思想性’如何”。然而成书却才气侧漏,颇有神韵。

《老舍和他的作品》,作者:胡金铨,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0月
“考据狂”粉丝写老舍:“北京怂人”
熟悉胡金铨的人都知道,他号称“文人武侠”大师,拍电影时就对场景、历史细节锱铢必较,有“考据狂”之称。1949年,胡金铨去了香港,偶然在邵氏公司做起演员、编剧和助理导演。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眼见香港报刊上关于老舍的文章错漏百出,吐槽无力,于是在朋友怂恿下自己开始写老舍。

胡金铨,中国香港电影导演、编剧。以文人武侠片大师著称,一生读书甚勤,酷爱钻研《明史》,影片大多以明代为背景。
1930年代生于北平的胡金铨,是老舍的小老乡,也是老舍的小粉丝。这个“考据狂”天南海北地自费搜罗材料,跑遍了伦敦东方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现代中国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最终成文九篇,在《明报月刊》上连载,1977年还在香港出了单行本《老舍和他的作品》。不过,这本老书的简体版是直到2018年才由后浪和北京联合出版社重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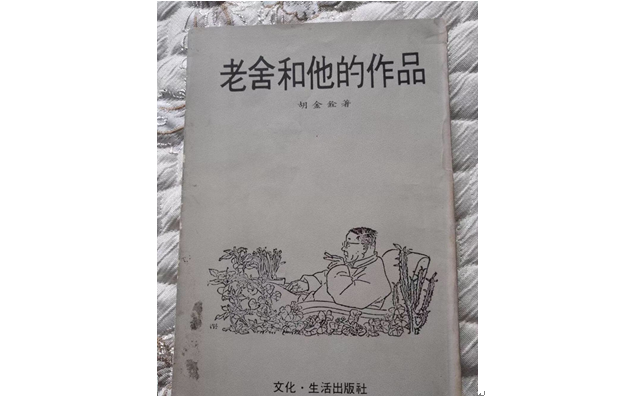
旧版《老舍和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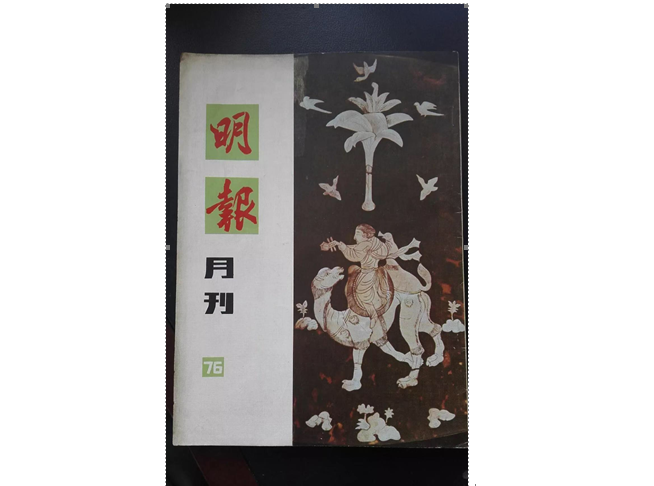 香港《明报月刊》
香港《明报月刊》
胡金铨这本《老舍和他的作品》,很快就能翻完,但读完后有手不释卷之感。粉丝写老舍,充满爱意,却又很不客气。挖苦人不带脏字儿,准、狠又好玩——他以老舍的调调写老舍,净说大实话,这就很有意思了。
一上来,胡金铨先劈头盖脸损了一番老舍研究者的不得其魂,亮明自己的家伙:
老舍的作品最接近北京的劳苦大众,豆汁儿是北京劳苦大众的食品(很多有钱的北京人不喝)。根据我的理论:能喝豆汁儿才能体会出老舍作品里的趣味。这只能意会,无法言传。有志于研究老舍的诸公,不妨先练练喝“豆汁儿”。
谈论老舍的文章,我也看了不少。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感,很少有“正中要害”的。当然,有人的确下过很大的功夫……资料相当丰富,可是太偏重于“做研究”,没有描绘出老舍作品中的精神。就像批评一张水墨画,只分析了它的纸质、用笔、用墨、师承、流派,而没有体会出它的神韵。
从小说到相声看了四百多篇老舍的胡金铨是真爱,还有天然的“老北京资格”,他和老舍有“共同的语言”:“这不是指我会说’北京话’,而是说我能体会出北京话里的神韵,了解它的幽默,明白它的’哏’”。杨早评《老舍和他的作品》时说,“对老舍这么一个大作家来说,其实把他写复杂不难,难就难在把他写简单。”他最看重胡金铨跟老舍的“位势差”与“共时性”——他们差了33岁,后辈胡金铨也经历过民国那个时代,于是一边评述老舍生涯,一边摘引时事来作为对照。

老舍,原名舒庆春,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等。
胡金铨“黑”老舍是“北京怂人”。什么是“北京怂人”?本分、窝囊、有正义感,但好耍小心眼、自私、好面子;做事任劳任怨,但无进取心;无惊人成就,可也不大作恶。胡金铨说,历来的造反、革命,都没北京人的份儿,往好里说是“有修养”,其实就是没出息——这简直是“北京人的性格天花板”了。用胡金铨的话来说,老舍在“怂人”里头算是出类拔萃的。
老舍爱哭穷,他给朋友的信里写在“文协”工作的经历:“我穷且忙,并无薪俸可言也……”,但又说“穷得有精神”。胡金铨做考据时发现老舍本人自述式的资料不大可靠(比如他其实也没那么穷),这里头既有记忆错误、疏忽,也有故意夸张,过分谦虚,言不由衷;而对他创作上的缺陷也毫不留情地指出,比如,“没有诗才”;说他往小说里掺进相声、鼓词和京戏等佐料,能妙趣横生;可一旦创作相声、鼓词和京戏又非常失败;还说他向梁实秋发起的檄文信啰嗦无力拖泥带水,吐槽“战斗性的文章非绍兴师爷不可,’北京怂人’不行。”
胡金铨清楚老舍的“文才”,是求知的过程决定了他后来写作的技巧和形式。老舍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师范,所受到的正规教育大概有七年半左右,此后全凭自修去获得知识。他对旧学下过功夫,这奠定了他日后作国文教员的基础,也对他后来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旧小说和通俗读物,都是老舍汲取知识的源泉,比如《唐人小说》《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啼笑因缘》《三剑侠》等,还有一些公案小说。此外,“标准北京小市民”老舍熟悉京戏、大鼓、相声、评书、单弦等,这些地方曲艺对他写作的风格也有很大影响。老舍作品熟练地运用文字技巧,半文半白的体裁,字句间俏皮和巧妙的安排,都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一个作家的养成史,得过些荒唐日子
老舍写过一篇叫《习惯》的文章,叙述任何一个主义、一种理论都不能使他永远相信。有时候一篇文章,一场电影,或者和朋友谈一席话都能改变他的整个思想。而生活习惯则不易改变:如抽烟、喝酒和种花之类。知识分子的风雅趣味和软弱摇摆,都包含在老舍出生、求学、写作、异国辗转、回国教书以及抗战时主持“文协”的经历之中。这里面不乏趣事,比如17岁还是“半大孩子”的时候就当上了小学校长,后来晋升“小教育官儿”,27岁又跑去英国“漂”了几年,还跑去南洋考察,一度想写“华侨奋斗史”之类的故事。胡金铨保持了饶有趣味的观察距离,来看待一个作家的养成史。
21岁,老舍混在北洋政府里当“小教育官儿”时,做北京学务局的北郊劝学员,每月“正俸”有两百大洋。这比起他当小学校长时,算“暴发户”了。职位虽低,大小是个“官儿”,看到了很多离奇古怪的现象。
学务局“公事”清闲,颓废青年老舍整天地豪饮,通宵打牌,听戏,学戏,吊嗓子,上杂耍园子……有时候喝得酩酊大醉,“饮罢归来”,把钱包和手绢一齐给了洋车夫。照惯例参加无聊的应酬,学会了抽烟、喝酒、打麻将。虽然不嫖,但也像他所说的“尝尝禁果”——“接触”了女人。不过一年后,就把这活儿给辞了。这段经历后来成了写《老张的哲学》的素材,而正是《老张》令老舍名声大噪。
后来,老舍在英国混了五年。他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过中国语讲师,也趁机学英文,见世面。那时出国也算潮流,他的国内旧识许地山当时也在牛津进修。他的朋友圈里有老华侨、留学生、学者、生意人、中国驻英使馆人员。老舍的幽默底色里,除了北京底层旗人的出身,也染上了英国式幽默传统的启发。
初到伦敦时,老舍住在两个老姑娘家里。两个老姑娘一个病,另一个扶持照顾病号数年,老舍佩服她们的“独立精神”,并且写道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逼出来的”。胡金铨写到这里时赶紧纠正老舍这个农业社会出来的国人,对于工业社会人理解的偏差:“其实他不明白,所谓’独立精神’,是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会因血缘关系彼此照顾,互相倚靠;宗族之中,提拔、牵扯,常常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胡金铨对老舍的思维评述颇有不少。比如在英国遇到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时常失业的工人青年,以及半失业状态的学贯中西的老博士时,老舍觉得这体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学非所用的情形如何严重。胡金铨则评:其实他不知道,任何“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英国算好的了。
在异国“漂”的老舍想家。所谓的“家”,就是国内的一切。后来他去了齐鲁大学教书,在济南做教授时,度过了一生之中安逸高产的好日子,他成了校园的“明星教授” ,后来跟冯玉祥有过一段“泰山讲学”的香火缘。
齐鲁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的大学。据说,有次教育部派人来视察,老舍正在讲课,这位特派员听入了神,坐在教室后面跟学生上了一堂课。不过老舍超强的表演性,却也阴错阳差使他丢了“齐鲁”的教职。1934年夏天,他在课堂上谈起民间曲艺,越讲越起劲儿,为了举例,爬上桌子表演了段“大鼓”。正好洋校长经过,大吃一惊,觉得这种“杂技式的教授法”太不成体统,有所批评示意。老舍也觉得不好意思,就递了辞呈。不过,老舍虽然好“耍滑稽”,可教书倒是极认真的。
左右立场的中间人,散淡而真挚的爱国者
1931年到1937年间,是老舍一生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六年里发表了一百五十多篇文章。彼时,动荡的时局、复杂的文艺思潮和生活环境都影响了他的写作情绪。
国共分家之后,“左、右”派的文化人也展开了斗争。在文艺界,左联、林系(林语堂)、民族主义文艺刊物、中间派、新月派、复古派各执一词,而实际情况比这些分类更为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楚。
老舍是当时“叫好又叫座儿”的作家,但不属于任何派系。反而成了各方力量争取的对象。他没什么立场,于是左右中的刊物都载他的文章。话说老舍虽然没参加当时的文艺论战,但“三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都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
从北伐到抗战前是动荡年代也是文艺高潮,全国文艺性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为“供求”的需要,老舍的写作就“大力增产”,“量”一多“质”就差了,相当于从零售精品干起了批发“行货”。老好人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碍于情面、应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当时,老舍写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自己觉得很对不起文艺”。而当教师的“粉笔”生涯也令他厌倦,因为教育和写作在时间上起了冲突。1933年,他还得了腰病。虽然辞职了一段时间,但由于卖文无法糊口,于是又重操粉笔生涯。
高量产期的老舍在《宇宙风》上登了个声明,题目叫《磕头了》。文章内容就是跪求编辑别再约稿了,非常搞笑:
“在抗战中,我写了许多不像样子的东西。所以,去年我决定写一部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以赎粗制滥造之罪。
朋友们,让我在病痛的煎熬中写完那个要不得的长篇吧!一个要不得的长篇,在我看,总比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地乱写短文更有点意思哟!在这里,我向肯帮忙我的朋友磕头致谢!”
“北京怂人”老舍虽然散淡无立场,但是个当之无愧的爱国者,尤其在那个民族主义最为浪漫的时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领导权落到了老舍这个“散淡的人”身上。从30年代他与文坛不同阵营的友好交往,再到40年代在抗战后方,老舍又因左、中、右各方势力的角力不下,写作与交际都左右逢源的老舍又成为呼吁团结统一的领导者。他对文协有两大贡献,一是促进作家们团结,二是推进通俗读物,“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这一点是当之无愧的。
最无聊的写作大概是“总务报告”“会务报告”之类的命题文章,不过老舍执笔写时就能写得生动有趣,不像流水账,还塞进去了不少珍贵史料。当一伙儿爱国文青组成“作家阵地访问团”、“前线慰劳团”出发北上南下时,老舍又成了“慰劳团”里最出风头的人物。每到一个地方,大家都嚷着:“老舍在哪里,请站出来!”于是他就上台给大家讲个笑话,或唱一段,宣传一下抗战的意义。他的小说和曲艺在军中也很流行。

《老舍和他的世纪》,作者:孙洁,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孙洁在《老舍和他的世纪》一书中指出了老舍自身的矛盾性,他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但根本上又是一个“写家”,他无法忍受文学在“理论批评”下越发狭仄或被“政策指导”呼来喝去,但同时,他为了国家至上主义的理想又甚至可以牺牲对自己有生命之喻的文学,更无法忍受自己的国家至上主义受到无端的嘲弄。“八·二三”殴斗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将老舍推入无边的绝望深渊的情境。不过,胡金铨在《老舍和他的作品》这本书中的记述,尚未涉及到老舍去世的60年代,个中原因今日已不得而知了。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悦东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