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诗歌读者来说,裘小龙的名字往往和T.S.艾略特、叶芝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裘小龙翻译的《四个四重奏》《当你老了》《丽达与天鹅》等作品被广泛阅读,对当时国内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77级”大学生,裘小龙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了半年本科,便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师从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研究英美文学。卞之琳先生给裘小龙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试写几首诗,再决定是否让他修西方现代诗歌,因为卞先生认为,“只有自身对诗歌写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体会时,才会真正深入地去从事诗歌研究。”就这样,裘小龙走上了写诗、译诗的道路,延续至今。
1988年,为写作艾略特的专著,裘小龙来到艾略特的故乡圣路易斯,后因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决定留在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生存环境变了,写诗的习惯没变。裘小龙在美国时用英语写诗,屡获奖项,后又用英语写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销量很高。不仅如此,他还将古汉诗翻译成英语。将英语译成汉语,又把汉语译为英语,且用双语创作,这需要对两种语言都有极好的把握,并将两种语言的特性恰当融合,不得不说,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
近期,裘小龙的诗集《舞蹈与舞者》出版,是其原创诗歌与译诗的合集。借此机会,我们专访了裘小龙,和他聊了聊关于诗人译诗、在两种语言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为什么会写侦探小说等问题。

裘小龙,1953年生,早年以翻译西方印象派诗歌知名,叶芝著名的诗篇《当你老了》就出自他优美的译笔。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现居住在美国,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
新京报:先从新书《舞蹈与舞者》开始吧。这是一本比较奇特的诗集,由原创和译作共同组成。诗人译诗是一个传统,但也有一些小争议。你如何看待诗人译诗?
裘小龙:这是漓江出版社所出的“双子星”丛书中的一本。丛书编得挺有特色,所收入的都是既写又译的作者。这在中国诗坛上其实也算得上一个传统,尤其在老一辈诗人中,如冯至、卞之琳、穆旦、王佐良等等,名单可以列得很长。至于诗人译诗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
说到底,在忠于原诗意义和意象的前提下,译诗在目标语言中读起来也必须是首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仅是在译文中机械地押几个韵就可以充数了。诗不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样说——怎样把一种语言的感性、节奏甚至音乐感都尽可能地加以发掘、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译诗与写诗或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庞德翻译李白的“长干行”,在不少英美诗集中,这首译诗是作为庞德的创作诗“河商的妻子:一封信”被收入的。在《舞蹈与舞者》中,我只能加注来加以说明。
新京报:写诗与译诗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彼此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裘小龙:这也可以说是比较文学中的一种影响研究吧。至少对我来说,译诗是特别细的细读,自然也是学习写诗的一个过程,这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自己的写作。在翻译中所接触到的技巧、风格等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借鉴、模仿,或进一步发挥。
但与此同时,写作也在加深对所译的作品的理解。就像卞之琳先生曾对我所说的那样,只有在自己诗创作的感性体验和实践中,才会真正地去深入领悟所译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写。

《舞蹈与舞者》,作者/译者:裘小龙;版本:漓江出版社 2019年4月
新京报:在亲自编选这本诗集中,有哪些选择的标准或倾向?
裘小龙:我自己的诗创作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现在,虽断断续续,却一直在写。期间更经历了种种变化,用中文、用英文、用两种文字掺杂着一起写,或通过书中的人物——戴着人物的面具来写,如我的《陈探长诗选》在欧美各国出版,就不妨说是戴着陈探长的面具写成的。在不同的阶段,对技巧、风格、韵律、诗艺等多少有着不同侧重的追求。在编选这本集子时,想尽可能地把不同时期的一些特点客观地加以呈现,当然,在这样做时,难免会有太主观的取舍。
新京报:诗集中收录了你翻译的T.S.艾略特、叶芝等人的作品,也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品,之前翻译这些诗的契机是什么?
裘小龙:我早年师从卞之琳先生读外国文学硕士时,研究方向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我因此翻译过艾略特、叶芝等人的诗;也翻译了在他们之前影响了现代主义感性的一些诗,如“多弗海滩”等这样的作品;同样,这自然也延伸到了在艾略特、叶芝等人之后较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与诗作。这本集子收入的,既有在我1988年出国前译的,也包括我到了美国后新译的作品。这次在编选《舞蹈与舞者》集子时,对过去的译文也借机做了校正。
新京报: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老师卞之琳先生,他对你的创作具体有哪些影响?
裘小龙: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读研究生的日子里,我每星期都去他在干面胡同的家,听他给我单独“开小灶”讲课;这与其他老师在教室里上的课很不一样。于我,卞之琳先生首先是个诗人,他言传身教,讲课时天马行空,理论与具体写作实践并行不悖,时时闪烁着他特有的诗意灵感。例如他给我布置的第一份作业,就是要我自己先写几首诗,然后再决定是否让我跟他修西方现代诗歌。
按照他的说法,只有自身对诗歌写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体会时,才会真正深入地去从事诗歌研究。创作与批评的兼顾在英国诗歌中是一个传统,他身体力行地继承了下来。在诗歌写作外,他还跟我分享了他在四十年代末写一本英语小说的经历,分析了小说与诗歌创作的异同,以及他跟英美作家如Isherwood 等人关于怎样进行双语写作的探讨。当时姑妄听之,可在许多年后,恰恰又影响到了我自己的英文小说写作。
新京报:从事诗歌创作、翻译,是否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有关?
裘小龙:这肯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有关。在卞先生的关照下,我自己写诗,也与其他年轻诗人有种种交流,参加了不少诗歌沙龙活动,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当时的年轻诗人中,既写又译的不多,他们因此希望我能多翻译一些;老一辈的诗人如邹笛帆先生等,也在这方面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从那个年代能这样一路走下来,我真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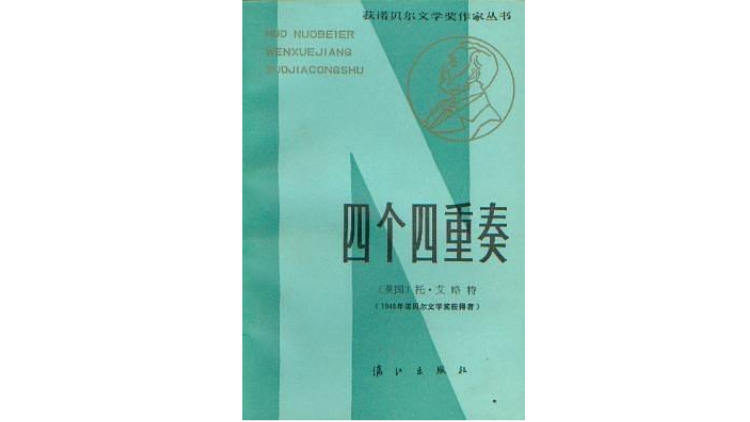
《四个四重奏》,作者:T.S.艾略特,译者:裘小龙,版本:漓江出版社 1985年
新京报:诗集中有一首诗,名为《我诗歌的组成部分》,感觉是你对自己诗歌源头的剖析。你在中国写诗、译诗,后又定居美国,环境和语言都产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诗歌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裘小龙:“我诗歌的组成部分”是根据我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写成的。我当时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课程。诗中写到的和子是我的日本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都比较穷,她在回日本收集论文资料前,特意将我叫去,把她喜欢的几件家具送给我;唐纳尔德是教我英语创意写作课的教授,尽管我读的是比较文学学位,他特批让我选修他开的写作课,当他要退休搬离时,坚持把他定制的书桌留给我;元鹿是来自国内的访问学者,离开时也把他心爱的毛笔赠给我。
对于我,这些不仅仅是师友们的馈赠与期望,这一件件物件更一直象征着,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怎样直接或间接地与我的生活经历交织在一起,时时在提醒我不可放弃,必须要继续写下去。说到底,诗不是我一个人写成的,而是像多恩曾说过的那样:没有一个人自身就能成为一座岛屿,谁都只是大陆的一小片,大海的一部分。移居美国后各方面的变化很大,这首诗中写到的正是这些变化对我的诗创作的一部分影响吧。
新京报:定居美国后你开始用英语创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母语应该是极为重要的。用英语创作,如何把握它的特性,如节奏、语调等?是否遇到很大的困难?
裘小龙:对一个诗人来说,母语确实极其重要,在用一种外语进行诗创作时,也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劣势。可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者就一定得把母语弃之脑后,从零开始。相反,在双语写作的探索中,母语的存在或潜在也能转化成一种优势,可以把母语中独特的语言感性或表达引入外语的写作中,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韵味。
新京报:为什么会开始写侦探小说?
裘小龙:我写侦探小说是个意外。1997还是1998年的时候,第一次回国探亲,目睹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化,我开始构思写一部反映社会变迁的小说,但在此之前我没有写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遇到了困难。我平时喜欢读侦探小说,因此想到不妨利用这一文类的现成框架,来讲我的中国故事。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侦探小说有着约定俗成的结构组成部分:尸体或案情的出现,探案过程中的曲折和悬念,破案与真相大白。在这个框架里,可以穿插进我要讲的内容。当然,在这方面我也受到了欧洲“社会学”流派的侦探小说的影响,换句话说,这是侦探小说,同时也是社会小说。
新京报:你的侦探小说销量很好,还获得了世界推理小说大奖,你认为小说得到广泛认可的原因有哪些?
裘小龙:这应该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在其中重要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世界各国的读者对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他们也通过选择阅读侦探小说来了解中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都组织了“跟着陈探长来中国”的旅游团。
另外,这也可能与怎样全球化时代写作的策略有关。我们曾习惯说,要为某个特定国家的读者写作,这样说自然无可厚非;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不能说我们要为全球的读者写作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带来许多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不过,怎样对在中国之外的读者讲中国的故事(当然也包括中国之内的读者)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课题。
新京报:你也把一些古汉诗翻译成英语。和把英语译成汉语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你的第二语言。两种翻译之间,有哪些异同?
裘小龙:以前把英美诗歌翻成中文,这毕竟是我的母语,自己的感觉要相对有把握一些。不过,要把中国古典诗词翻成英文,而对象读者是习惯读现代英语诗歌的读者;要让他们把译文作为可读的英文诗来接受,难度显然要高得多。那天在人大的讲座中,顾彬先生在现场互动中详尽引用、探讨了我在译诗中的一个具体处理手法,也说明了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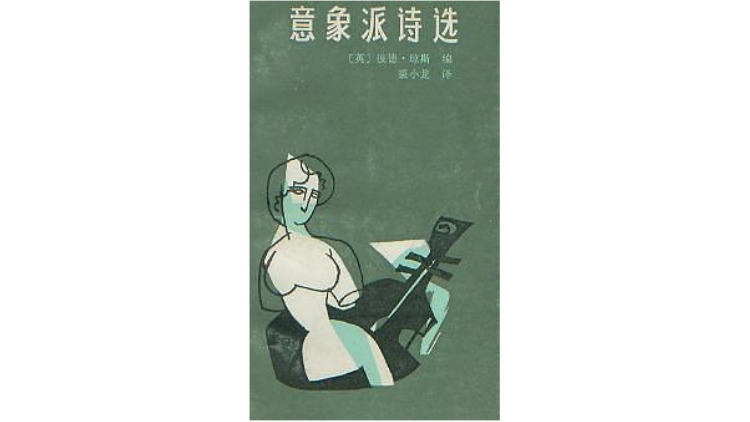
《意象派诗选》,编者:彼得·琼斯,译者:裘小龙;版本:漓江出版社 1986年
新京报:语言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两种思维之间,你如何做到兼容,且维持平衡?
裘小龙:这个问题有意思。按照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的“语言相对论”,不同的语言因为其独特的感性与结构会对该语言的使用者在认知的过程中产生框架式的作用,导致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照世界,带来不同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也影响与制约着思维,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是语言在说人,而不仅仅是人在说语言。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局限就是我世界的局限”,也包含这样的意思。
回到你的问题上去,在两种语言思维中怎样做到兼容或平衡,或许还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即把不同语言的感性或思维方式相互介绍并融合到自己的写作中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这样做或许也可以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
新京报: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主要教哪些作品?据你的观察,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现状如何?
裘小龙:我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时,主要还是讲一些经典的作品。最近几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中的译介有了一定的进展。譬如说像金宇澄《繁花》那样较难翻译的严肃文学作品,也正在好几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这些都是以前很难想象的。希望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
新京报:去国三十年,你对中国当下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哪些想法?
裘小龙: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变化不言而喻。我以前主要是写诗的,在离开中国七八年后第一次回国,正是感受到这种种变化的冲击,从而开始写起了小说。因为长期生活在国外,我回国时经常会有震惊、困惑等感觉。“刘郎已恨蓬山远, 更隔蓬山一万重。”在一定程度上,写小说也是在帮助自己理解这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切的一种努力。
作者 张进
编辑 张进 校对 翟永军
原标题: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丨专访裘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