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感受不会轻易叛变的话,对于遥远而古老的拜占庭帝国史,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冷眼旁观的角色和态度。就我个人而言,拜占庭帝国史更像是一份太过于模糊但又似乎特别重要的文化遗产,尽管可以用一无所知来替代这种感受。在阅读拜占庭帝国史的时候,既无法激发帕慕克式的呼愁,也无法像布罗茨基般的戏谑吐槽,更无法像叶芝晚年那样叩问灵魂。这个漫长而古老的帝国所赐予我们的,或许是那一连串无法记住的人名和无法厘清的战争,似乎无从理解西方人对那段历史的幽灵之感。
在已过花甲之年,叶芝写下过向拜占庭致敬的诗歌《驶向拜占庭》;近六十年后,另一位诗人布罗茨基却写下了略带愤懑的《逃离拜占庭》。在叶芝看来,拜占庭曾经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及其精神哲学永不衰竭的源泉,所以他把朝向这座城市的旅程,看作是追寻精神生活的象征;于是,他要“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来到了这一个圣城拜占庭”,“歌唱那过去、现在和未来,唱给拜占庭的老爷太太听”。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拜占庭帝国史的肇始、诞生和死亡,让他成为了“地理的受害者”;于是,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昔日子民,他注视着历史文化和伦理政治的浩瀚谱系,将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所见所闻一一变成笔下的尖酸刻薄,与拜占庭帝国的文明遗产做个了断。然而,这篇入选了“1986年最佳美国散文”的长文,让素来欣赏布罗茨基的索尔仁尼琴大为不悦……

拜占庭地图
无论是拜占庭,还是君士坦丁堡,似乎都没能像叶芝、布罗茨基或索尔仁尼琴那样,激发我们内心的特殊情绪,更不会形成他们那般的“文化内战”。反而是后来取而代之的“伊斯坦布尔”这个名词,让我们自信地装作真的陷入了奥尔罕·帕慕克的呼愁情绪。或许,布罗茨基才是对的: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对于当下人而言,历史上的“我杀故我在”早已让位于“我拍故我在”,拍下的也不是拜占庭的帝国斜阳,而是美图秀秀中的自我陶醉。
然而,正如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在某些地方,历史就像高架桥上的车祸现象,注定了无处可藏的命运,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历史意义,比如伊斯坦布尔,或者唤之为君士坦丁堡,或者称之为拜占庭。”尽管如此,无论是文明的重装,还是帝国的陷落,抑或它充斥着乱伦与诱惑、复仇与谋杀的荡气回肠, 拜占庭帝国史在地理和历史中都显得那么的遥远,犹如教堂墙壁镶嵌的马赛克图画,既显得辉煌不已,也显得模糊不堪。在这种文明的隔离下,会让人有种生恨般的无能感受,会激发着人们向同样没有这般文化传统的其他人去索取他们的感受,去获取某种遗憾的补偿和无聊的肯定。
在拜占庭的魅影下,如今的那座城池,更像是叶芝笔下那个“垂死的时代”。在伊斯坦布尔的喧嚣中,奥斯曼帝国的教训也好,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罢,历史就像是污秽街道上的流浪汉一样,在野心家的现实欲望面前,新苏丹的拥趸们信奉“无神论”般,不再留意到它鬼魅般的存在。
当理查德·菲德勒抵达伊斯坦布尔的第三天,就见证了土耳其动荡的社会局势。埃尔多安的军队,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逐塔克西姆广场上的示威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神秘感,总会对人类的想象力进行或多或少的蔑视。因时间而导致的提问未遂,竟然在第二天的新闻里给出了答案:新西兰清真寺遭滥射影片成为了土耳其选举工具。为了激起保守派的支持,同时也借此抨击反对党的懦弱,埃尔多安在数个选举造势中,播放着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恐怖袭击影片片段,并将土耳其反对党领袖的声明与立场极右的澳洲参议员安宁相比,因为安宁把滥射事件怪罪给穆斯林移民,煽动着选民的情绪。
“我从未在学校里学习过有关拜占庭的知识。”作为英国后裔的理查德·菲德勒,并没有接受澳洲土著成年礼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吸收拜占庭帝国文明的文化影响。他想着带儿子一起进行一次历史文化之旅,从意大利的罗马城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通过寻觅罗马帝国遗迹的方式来完成儿子的成年礼。最终,理查德·菲德勒将这次父子之行纂述成书,也就是最近引进出版的《幽灵帝国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传奇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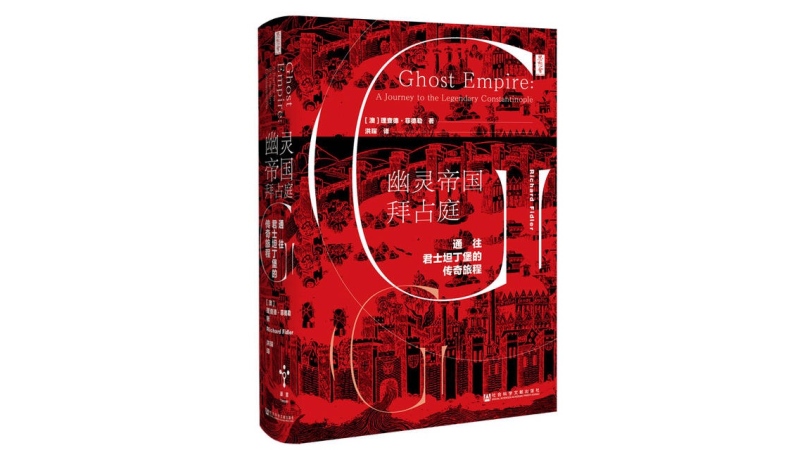
《幽灵帝国拜占庭: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传奇旅程》, [澳]理查德·菲德勒著,洪琛译,思想会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3月版
也许,理查德·菲德勒对拜占庭帝国文明史的感受和困惑,能够弥补那股无聊的心理补偿。作为孤岛国家的澳大利亚,在那个年代比中国更加隔绝于世。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的大航海时代,澳大利亚才逐步地进入欧洲世界的视野之中。这种远程所带来的隔绝式命运,曾被澳大利亚人称为“距离的暴政”;再后来,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梳理着大英帝国的流放史,将澳大利亚称之为“致命的海滩”;而如今,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了华人移民的伊甸园。作为后发崛起的现代国家,澳大利亚人会如何去看待一段自身并不传承的帝国史呢?
在《幽灵帝国拜占庭》里,明显也能看出这种文明的隔离,如同旁观者一样回溯着拜占庭的千年杀戮和昔日荣光。除去夹杂在内的父子旅行内容之外,拜占庭的帝国史就像是给睡前的儿子讲述白天观看过的《权力的游戏》。澳大利亚的“距离”也给理查德·菲德勒一种特殊的视角,去看待君士坦丁堡的千年嬗变。
同样让人感到嬗变的,是他自己的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时,早期的理查德·菲德勒是道格安东尼全明星(DAAS)成员之一;进入21世纪后,他当选为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全国委员会成员,并担任宪法问题委员会主席;再后来,他加入ABC主持一档叫做 Conversations 的对话节目,成为澳大利亚乃至英语世界家喻户晓的主持明星。
在前往采访的路上,恰好新西兰枪击案的嫌疑犯被捕。作为澳大利亚的著名主持人,除去他对拜占庭帝国史的旅行感受之外,很想听他谈谈澳大利亚兴起的民粹主义和右翼声音,以及他怎么看待土耳其这些年的闹剧。当然,他在2011年还获得丘吉尔奖学金,调查欧美公共广播的新形态。在当下,逐步兴起的播客和各类知识付费型播客节目不断冒出,他会如何理解广播和播客这种公共角色呢?

一、澳大利亚没有反移民政策
新京报:据说你妻子的家族与中国有关系,不知你是否熟悉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历史渊源?
理查德·菲德勒:其实,我妻子是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在十岁时便移居到了澳大利亚。所以,她从小是在新加坡南洋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南洋文化比较多元,糅合了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葡萄牙、英国甚至是荷兰等多种文化。这种多元性,也体现在食物方面。
我妻子不会说普通话,因为她从小在家族里说的就是英语。不过呢,她小时候还是会说广东话的。只是,移居澳大利亚后,由于澳洲没有粤语的语言环境,她就逐渐地只会说英语了。今晚她也会飞到北京来。现在,她又开始学习普通话了,因为她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我的小孩子也在学习中文,我们互相之间经常还会用少许的普通话开开玩笑。
新京报:日前由于新西兰的枪击案,澳大利亚也浮现了一些议员的反移民舆论,而今很多华人也移民澳大利亚。你如何看待当今的这种反移民舆论,或者说,如何看待当下的极右翼浪潮?
理查德·菲德勒:首先我需要说明的是,当今的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反移民之类的相关政策。澳洲的移民政策是一种无偏见的政策,不过的确拥有一些反移民的民间声音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澳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元化的国家,持有这种反移民腔调的群体也只是一小部分的人而已。在当今社交网络的推动下,可能会让这种反移民的声音得到助长和抬头。澳大利亚一国党的领袖宝琳·韩森是二十年前从政的,她以前的反移民论调是针对亚洲人,但如今她已经将目标转移到了穆斯林身上。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澳洲也发生了改变。然而,我再次需要重申的是,反移民的腔调在澳洲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就好比像我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背景所组成的家庭。所以,新西兰枪击案发生之后,澳大利亚人是深以为耻的。在澳洲国内也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和讨论,人们都试图去思考为何一个澳洲人会做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
然而,正是因为澳洲无偏见的移民政策,才会让澳洲繁荣富强。我们强大的支柱,就是因为澳洲拥有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人口。当然,我们澳洲还有一些相关政策,比如接受大量的各国难民或者政治方面的避难者,可能政府在某些程度对待这些人的态度并不是很好,这也是一种事实。但是呢,澳洲还是依旧拥有大量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移民人口。现在的澳洲社会由非常多的不同背景的人组成。比如我来自于爱尔兰血统,我的妻子来自于华人血统,当然还有来自越南、索马里、俄罗斯等不同国家的移民及其后代。
新京报:我记得,澳洲总理曾想通过反移民或反穆斯林的声音来获取选票。你是否想象过澳洲有一天也像其他国家那样,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在澳大利亚抬头呢?
理查德·菲德勒:如你所言,极右势力或民粹主义在澳洲的抬头,其实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呢,它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澳洲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不太可能有民粹领袖出现,不会像美国那样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也不会出现类似于土耳其、匈牙利和巴西这样的国家首脑。即使有这样的声音出现,但持有类似舆论的议员在议会中的比例是非常小的。
不过,不得不承认,澳洲的确长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种族歧视问题。尤其是在年轻的穆斯林群体中,对极右势力抬头这件事情,有着很大的顾虑和担忧。如果澳大利亚真的发生诸如美国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我心目中的澳大利亚。因为我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之根本就是多元的文化,而且这样的文化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不同国家的人组成的家庭所传承而来的。所以,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的互相隔阂或者互相讨厌的现象,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就让澳大利亚不太可能广泛地出现民粹主义的声音。
二、用共情的叙事方式书写拜占庭历史
新京报:我们回到你的著作《幽灵帝国拜占庭》。近些年来,全球范围内关于拜占庭历史的图书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一些经典著作。为什么你要重写一本拜占庭帝国史?
理查德·菲德勒:这也可以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上来。 说到土耳其,其实很多年以来,伊斯坦布尔是非常多元包容的世界城市,虽然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群体,但同时也有基督教人口和犹太教人口。在最近一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土耳其的统治者总是竭力想着把其他种族或者不同信仰的人进行不断地边缘化。正是这种狭隘的社会政策,导致土耳其变得越来越弱小,国家的边界也越来越少。当一个国家不再多元,而只剩下单调的文化时,它就失去了繁荣的基础,失去了对不同文化产生好奇心的内在能力。所以,这也是为何我刚才说,澳洲如果变得单一化的话,就不是我心目中的澳大利亚了。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首先,我是一名历史爱好者,我儿子也非常喜欢历史,历史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共同爱好,我们可以一起探索历史背后的故事。与此同时,我也发现,拜占庭的历史在西方人心中也逐渐地被遗忘了。当我发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国家的历史时,周边竟然这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甚至最初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一段西方史。我写这本书,首先是希望更多的英语读者去了解这一段历史。现在呢,这本书也出了中译本,这也让中文读者有机会去了解这一段历史了。当然,西方读者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背后,其实也是大有原因的。
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也深深地改变了我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看法。在深入了解拜占庭历史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一段历史不过是一段欧洲史而已。当我去了解这一段历史之后,我才发现,它是西方文化比如波斯、阿拉伯、印度、蒙古和中国不断碰撞的文化史。在当时,拜占庭帝国欣欣向荣发展,实际上西方经历了一段长期的黑暗史。但正是在这个时期, 拜占庭帝国和上述的文明之间有了思想、物质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各国之间虽然也会不断地攻城略地,但同时也不断有新的城市在世界上拔地而起,各国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交流。我在写作的过程发现,即使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相隔这么远,但两者之间却一直都有着很深的交往。
另外,澳大利亚总是被说成西方国家,但实际上澳大利亚是南半球国家。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欧洲作家那种文化沙文主义。我写的角度,是从澳大利亚人的角度出发的。
新京报:尽管如此,我们会发现,不同时代或者不同立场的人,在书写拜占庭史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态度。近些年来对于拜占庭或地中海史的书写,或许也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有关?又或者,比如十九世纪西方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之后,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也随之分化。你自己又怎么看待拜占庭这一段历史的呢?
理查德·菲德勒:我写作此书,并非想要进行历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也没有想过要把它写成学术著作。我仅仅是写下了我自己的个人观察,这一点在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我写作此书时,更多的是把视角还给生活在那个年代那座城市的人,以一种共情的叙述方式来写作。尽管我们生活在二十一世纪,难道就可以说我们的科技比古人更加发达,我们自己比古人更加聪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活生生的人。
我想写下那个年代的人的生活是怎样的,那个年代的人也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独特的世界观和宗教观。比如,他们以为自己的城市就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们自己的经典著作也会由此为中心来展开。正是有这样的想法,才不断地自我激励般铸就新的伟大文明。
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体现在诸如艺术、建筑等多方面的追求之中。希腊有一个词汇:神性。拜占庭时代的城市建设,也体现了对神性的追求。当人们在建筑这座城市的时候,就认为这座城市像是天堂的镜子一样,能够照见神性。这种神性之美,不仅是对艺术的追求,更是对诗意的追求。
新京报:我知道,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带着儿子一起寻觅君士坦丁堡的历史遗迹。在你看来,14岁的小男孩能够理解一个被遗忘的帝国的意义吗?
理查德·菲德勒:我儿子对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经常会向我询问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会问我关于中国的历史、文革、希特勒、二战等,甚至还有金正恩的问题,虽然朝鲜是当今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最陌生、最遥远的国度。他成长于澳洲的民主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可以直接开政府玩笑的。所以,对他而言,对领袖的崇拜是非常可笑而荒谬的事情。再比如,在拜占庭的历史中,帝王身穿长袍头戴皇冠,所有觐见的人都得对他磕头,这也让我儿子非常好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此外,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自己就身在欧洲,不仅见证了柏林墙的倒塌,也见证了苏联的解体。对于我们当今生活在民主世界的人而言,以前的这种集权主义或君主制度,既陌生又熟悉。哦对,我下一本书所写的,就是关于布拉格的历史……
三、“幽灵帝国”的遗产经久不息
新京报:在伊斯坦布尔寻觅拜占庭史迹时,是否能够体会到帕慕克所说的呼愁?我们知道,地缘容易产生某种文化情绪,比如,爱尔兰之于英国,就会有种在大国阴影之下的感受。澳大利亚曾是罪犯流放的孤岛,澳大利亚人在面对历史和当下时,是否会像帕慕克那样有什么触动?作为一个汪洋中的孤独大岛屿,澳大利亚是否会有某种孤立感或孤独感?
理查德·菲德勒:其实,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澳大利亚人也并不会感到孤立,因为我们喜欢四处游历。当然,澳大利亚在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一段处于比较孤立的时期。
有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历史书,就叫《距离的暴政》,讲述的就是澳洲与其他地区和国家之间的远距离隔绝,造成了某些孤立的情绪。但是,澳洲原住民其实在这片土地上拥有非常长的生存史。当然,澳洲的现代历史最初是由一部殖民史开始的。但是在殖民之后,在短短五十年内,就有大量的人口来到澳洲土地。在19世纪50年代,澳洲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到了70年代,更是如此。
但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的澳洲领导人认为我们可能太过于多元化了,就制定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启了当时所谓的“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联邦反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1901年,白澳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只许白人移居。在此政策下,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压、被迫离开澳大利亚。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再后来,澳洲就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国力和经济持续衰落。但在60年代,我们又打开了国家的大门,重启了无偏见的移民政策,然后澳洲重新繁荣富强起来。所以,澳洲发展的历史是与世界共同发展融合的历史 ,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并不会感到孤立或者孤独的情绪。
我们生活在当下的世界,由于媒体的发展,我们每天读到的新闻都是一样的,包括枪击案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都能在最快的时间内读到同样的新闻。可能跟美国人不一样,他们不愿出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里,但澳洲人更愿意用自己双眼的眼见为实,来验证世界的真相。
新京报:在一次访谈中,你认为当下的知识分子已经背弃了君士坦丁堡的遗产。这里的遗产指的是什么?
理查德·菲德勒:拜占庭的遗产当然是非常恢弘壮观的,主要可以通过两方面来体现。
首先在144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当时非常多的古希腊学者把多年来藏在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典籍带到意大利去了,促成了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君士坦丁堡的沦陷,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文艺复兴。第二点呢,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各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大量密切的商贸往来。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像欧洲比如威尼斯的商人,不再愿意经过这座城市去往其他国家诸如中国。这也是为何1492年哥伦布会去发现新大陆,从而开启大航海时代。
与此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帝国的文化影响又是比较隐秘的。当时的文化价值对于现实价值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了。二十年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个关于拜占庭文化艺术的展览。与北京一样,纽约作为一个繁忙的大都市,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拜占庭时期早已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当年在《纽约客》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这个展览对现代纽约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灵冲击。拜占庭艺术品的壮美、安静和神圣,让他们意识到,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朽的,我们终究都会死去,唯有文化遗产能够长存而不朽。
同时,在伊斯坦布尔,如今的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早已被边缘化了,比如天主教的影响就早已式微了。我在书的末尾也提道,某次我在巴黎的时候心情不是很好,无意之中就闯进了一座东正教教堂,当时教堂内正在唱诵,那种氛围有种庄严之美,把我带入一个既有秩序又有神性的世界。瞬间之内,我心底的不快就被一扫而光,立马就变得平和宁静。这也是拜占庭艺术的力量所在。
这也是为何我把这本书叫做“幽灵帝国”,因为帝国虽然早已灰飞烟灭,但它的文化艺术对后来人的影响无处不在,如星星之火,长久不熄。
四、共情能够弥补当下的分裂
新京报:除去作家身份之外, 你最知名的身份就是ABC主持人了。你的节目如此受欢迎,在你看来是什么决定的?你的节目叫 Conversations with Richard Fidler,你如何理解Conversation的精神?
理查德·菲德勒:尽管我在节目中经常采访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但如果要说我的节目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并非缘于节目中会出现这样具备世界影响的名流人物。因为,在我的节目中,同样有大量的平民草根出现,他们之前都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或者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通常呢,当事人或许在上电视的时候,往往因为需要露面而感到害羞,但在广播电台说话时,这些困扰就不复存在了,完全可以放开自我,尽情地抒发己见。
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们节目组经常会营造某种环境,主要围绕着作为主持人的我、嘉宾和听众所形成的良好氛围,让他们更好地讲述自己的故事,说出自己的心声,引发听众的内心共鸣。当然,绝大部分人的故事,或许会让人感到无聊或者枯燥,对听众而言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这些平凡人的故事,自有其意义所在,也自有其力量所在。
在这么一个一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叙事弧:首先是让嘉宾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然后通过诸如哲学或其他方面的思想,来呈现生活和思考的丰富多样。通过这样的节目和内容,我们可以探讨大家所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甚至于最为普通的比如我该如何成为更好的人、我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我该怎样平衡自己的私人时间和他人的时间,等等。
另外呢,节目也经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我们平常人所无法经历的事情,由形形色色不同背景的人来讲述给大家听。比如说宇航员会分享他在太空舱中的经历和体验,或者经历过伦敦恐怖袭击的女士,会讲述她在恐怖袭击时失去了自己的双腿。也有的时候,嘉宾所讲述的故事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些小事一旦被讲述出来,就会变得非常有力量。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可以通过电台的方式,通过嘉宾的讲述,来影响更多的人。
对于当下而言,播客这种新的节目形式,也算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可以营造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在开车、通勤、购物、健身、打扫家务时,随时都可以聆听。在短暂的时间内,通过播客的声音,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当然,也可以轻易地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来,就好比阅读小说一样。这就是播客的意义和能量所在。而且,在西方诸如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播客已经越来越火了。
我以前只专注于做电台,如今专心做播客了。我的播客听众也在不断地攀升。你想想,澳大利亚的人口总共也就2600万左右,但我的播客每月下载时长已经长达350万小时之久。一年算下来的话,就有超过4000万小时的时长了。这也体现了现代人对于播客这种形式的强烈需求。
其他媒体诸如社交媒体,通过发布爆炸性的新闻,在吸引眼球的同时,也在分化我们的注意力。但是,通过一小时的播客节目,去倾听你素昧平生、无法遇见的人所讲述的故事,能够让我们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产生某种理解之情。播客或电台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与全世界听众之间营造某种共情的体系。对于我们当下分裂的世界而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萧轶
编辑:木子;校对:翟永军
原标题:专访理查德·菲德勒:通往幽灵帝国拜占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