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语堂的作品在内地长销不衰。但与《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和《京华烟云》等林语堂作品有多个版本同时在市面上销售的热闹景象不同,林语堂研究在学界一直不是热点。他的双语写作似乎给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设置了语言上的障碍,而他一生辗转多地的生活也给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造成了困难。
近日,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前大部分林语堂传记不同,《林语堂传》使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主要是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通信——向我们展示了林语堂享誉世界的多本英文著作的诞生经过;另外作者宣称此书着重于对林语堂思想的考察,他更在全书的开篇章节里提出,我们应将林语堂视为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上的一位标杆性人物,与鲁迅和胡适三足鼎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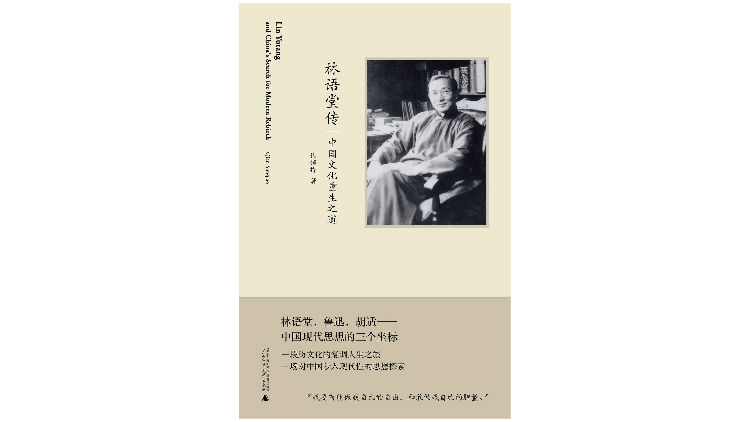
《林语堂传》,作者: 钱锁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4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学文研院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知识思想遗产——《林语堂传》研读会”上,与会专家分享了各自对林语堂的看法。
林语堂在文化层面拓展了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
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毛亮看来,林语堂是一个具有极强文化感受力的人。这一感受力让他在中西方文化间找到了一个接驳点,从而以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消化了现代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让这套实际上是异质的价值体系,可以为中国人所理解。
18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初兴,随之涌现的是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像Richard Steele, Joseph Addison和Samuel Johnson。他们通过自己的写作,奠定了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毛亮在林语堂和这批英国文化人之间发现了相似性。比照阅读林语堂和这批英国作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中找寻文化资源,用来消化对中国人来说陌生的观念的。
比如林语堂为人所熟知的“幽默”这一概念,毛亮认为,如果我们仔细加以辨析,就能看到林语堂所谓的幽默,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个“幽默”的概念,而是英国人所讲的mirthful and convivial way。在英国传统里面,这是一种能够让大家和谐相处的、促进人们友善交往的漂亮的说话方式,而中产阶级生活需要这样一种避免激烈争论的态度和技巧。
又如“性灵”这一林语堂从明代文人那里拿来的概念,可以和西方的wit相对照。再如“闲适”,闲适是中国人所熟知和喜爱的,林语堂用它来对应leisure这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典型的生活观和价值观。
“林语堂创办的《论语》,很像Tatler或者Rambler,而《人间世》像Spectator。”毛亮说。此外,林语堂的文章内容也多有和英国18世纪作家相合之处。比如林语堂曾经细致记述过他怎样买牙刷,怎样躺在床上、坐在椅上,这让毛亮想到Richard Steele的文章也是如此这般无所不谈,小到如何穿衣服、如何挑选衬衫、有人欠钱不还可以怎么办,大到如何对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表态,Richard Steele都写。“文章讲的事情有小有大,但其实质是在构建一整套中产阶级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

林语堂创办的杂志《论语》。
毛亮指出,这套价值观念或者说英美传统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特别是在林语堂用中文写作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时的中国充斥着左翼的和右翼的革命话语,在这两套话语的中间地带,林语堂用自己的努力将对中国来说陌生的英美传统——其实质是现代的、新兴的、中产的、市民阶层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化入到中国的文化话语里来。而在这一过程中,林语堂拓展了汉语的表达能力,用明代文人性灵、闲适的话语,包容了一个异质的传统,使其能够在中国的传统里扎根,让人看上去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东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毛亮说。
作为世界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中国和文化中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从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所可能给予我们的教益这一角度展开论述。在牛可看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是中国一直在追问的,尤其是去年以来,在外部环境的逼迫之下,有更多的中国人重新对这一问题进行思索。而文化生活——特别是跨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逼迫我们在新的情景之下来考量我们是谁。
牛可认为,“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来考虑。从内部来说,是思考我们由谁构成;从外部来说,则是通过和被我们认为是他者的人进行对比,来界定和认知自我。林语堂在“我们是谁”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世界主义者的立场和态度,所谓世界主义者,在牛可看来,就是化用他者来充实自己,而这样一种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正是当下中国需要的。
当下中国文化“封闭性太强”,“用David Hollinger的话来说就是母文化天然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过大”,不容易认可、吸纳、包容别人,而倾向于把别人说得不如自己,甚至关于他者的知识也是用来伸张自己的主体性。但是牛可同时认为,和很多美国的欧洲移民比起来,包括林语堂在内的在美华人,对其母国的情感和认同是更为强烈的。他引述某学者的观点说,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美国人;而中国人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一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不能成为别的国家的人了。对此,钱锁桥表示,作为世界主义者的林语堂同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并不矛盾;而对于母国的情感,不仅中国人有,美国的德国移民、日本移民,都有对他们祖国的情感。
对此,牛可认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是有着天然的、内在的矛盾的,比如早期科学史上的很多人物,在移民美国之后,都要面对民族主义和科学无国界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形成的冲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刘文楠以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相关论点切入对林语堂的讨论。在列文森看来,儒家中国在现代崩解了,结束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现在这个完整的世界不复存在了。为了中国能够作为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之林,作为文化的儒家传统、中国传统必须成为历史。只有当儒家中国成为历史的时候,现代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把它抢救出来——作为独特的中国文化抢救出来,而与此同时,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作者:(美)列文森,译者:郑大华、任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在刘文楠看来,林语堂在英语世界里呈现出的中国,很可能并非传统的中国——传统中国在林语堂看来应该终结,林语堂的努力在于构建一个文化中国,它是现代的,重生的,是可以在世界文化中被用作资源的。但林语堂想要的这样一个文化中国,又受到现实中处于困境的政治中国所拖累——先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继而又面临国共的对峙。林语堂晚年在台湾,思考的仍是中国文化如何重生,重生可以落在何处的问题,他的这些思考有何得失,是否行得通?刘文楠表示希望听到作为林语堂研究专家的钱锁桥的看法。
钱锁桥回应称,“我不赞同列文森的断裂说,文化不需要断裂,文化为什么要断裂?”在钱锁桥看来,林语堂正是列文森命题的一个反例,林语堂证明了中国文化可以重生,“关键是看在哪个方面重生”。他说。
然而,如果林语堂做的,是选择中国原有的文化资源中的特定方面加以重构,来作为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钱锁桥《林语堂传》的副标题正是“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那么他做的不正是打造一个“文化中国”吗?而这不也就证明了列文森关于“儒家中国”必须成为历史的论断吗?
《林语堂传》的出版是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研究方法的契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丽华认为,《林语堂传》一书给现代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跳出了民族国家的视角,而从跨文化的视角对林语堂进行再认识。
据张丽华介绍,在内地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主流论述中,林语堂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被低估了,而这和长期以来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采取的民族国家视角有关。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出发的主流论述会着重强调鲁迅、胡适和周作人等作家,往前追溯则有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等,林语堂在这个脉络里面,最多被放在第二层级。而从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林语堂,会发现他在现代中国以及现代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文学活动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是一个在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都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双语作家——同时还是批评家和发明家。
张丽华说,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对于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上以英文写作的系列文章关注较少,但正像《林语堂传》所展示的,如果对林语堂的英文散文和中文小品文创作合而观之,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其间有个一以贯之的写作态度和风格:把读者当成亲密的朋友,用老朋友聊天的口吻写作。这让张丽华想起钱锺书和周作人关于小品文的争论,争论中钱锺书主张小品文应采取“不衫不履的家常体”,反映了钱锺书受到的英美传统的影响。而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林语堂对散文的贡献、他对小品文的提倡,通常都处在周作人的阴影之下,即将林语堂和周作人同时视为晚明小品文脉络的继承者,但同时认为林语堂对晚明小品文的认识没有周作人的深刻。而正像毛亮在之前的发言中指出的,林语堂的散文另有其所承继的文化资源,重新审视林语堂可以丰富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小品文之争的理解和看法。
张丽华认为《林语堂传》取得的另一个成绩是利用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的通信,还原了他在美国的写作的具体经过,我们由此了解到林语堂的多本英文作品,如《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是如何在赛珍珠和华尔西的策划下共同制作出来的。借用福柯在《何为作者》中提出的概念,张丽华认为林语堂在美国的这批作品,“作者就不仅仅只是林语堂,还包括赛珍珠和华尔西”。而正像《启蒙运动的生意》勾画了一个百科全书出版史的鲜活图景,让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启蒙运动一般,《林语堂传》通过对于制作出版林语堂英文著作这一段历史的再现,不仅有助于丰富对文学史、思想史上的林语堂的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史和出版史的新资料和新视角。

《吾国与吾民》,作者: 林语堂,译者: 黄嘉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2月
林语堂的跨文化书写还让张丽华想到陈季同。她认为19世纪下半叶陈季同在法国的写作和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在美国的写作,是有可比性的。他们分别承担了向法国和美国介绍中国文化的使命,还不约而同地翻译和改写了唐传奇。但在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文学史叙述中,他们都没有得到准确和恰当的定位和评价。张丽华表示,《林语堂传》的出版是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界限和方法的一个契机。
对于张丽华将林语堂在美国写作的多部作品的作者说为林语堂、赛珍珠和华尔西三人,钱锁桥表示他不能完全赞同。因为赛珍珠和华尔西只是做了好的编辑应该做的事,而作为编辑和出版方,他们做事是有分寸和边界的;另一方面,林语堂的创作是有自主性的,而且和他之前在中文文章中的很多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近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视角下的林语堂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院李珊将林语堂放置在近代中国人英文书写这一视角下加以考察,发现林语堂和其他很多作者具有共同点。
林语堂向西方阐述中国,而这是近代中国英文书写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在论述这一主题时,作者多倾向于向西方表达中国进步的一面。比如在《林语堂传》中被钱锁桥描述为林语堂论敌的汤良礼,就曾写有China in Revolt(《反叛的中国》)一书,讲述中国是怎样从“文明”转变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与林语堂一样,汤良礼也视民族主义为中国进步的原动力。林语堂、汤良礼等人对中国民族主义的阐释,和他们拟想的对话对象有关,在他们写作的二三十年代,有一派人物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刺激和煽动而兴起的东西,他们否认中国有内生的寻求民族平等和国家解放的要求。这是林语堂和汤良礼等人所反对的。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立场问题,也是近代中国人英文书写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比如学界的研究已经普遍指出,胡适在用英文写作时,对于中国文化的回护和民族主义立场,与其中文写作中的那种自由主义立场是不一样的。李珊认为对此要将问题放回到近代中国所处的中西方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的语境下去理解,更有历史感地处理这一问题,关注其间的张力。
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可能和西方的人文科学接榫,也是林语堂那一代中国人的英文书写所常处理的问题。比如陈衡哲就曾尝试以西方学术框架来收纳中国传统文化。而江亢虎也有两本英文著作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
尾声
整场活动结束后,新京报记者向毛亮请教林语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译本译名都作《生活的艺术》而没有直译为《生活的重要性》)一书,书名何以采用importance(重要)而不用art(艺术)。
毛亮表示,尽管没有使用art这个词,但整本书的理路和18世纪时人们谈论的art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是一致的,都是关注日常生活,强调生活是可以用特定的价值观去形塑的东西。“他讲的是市民生活,其背后的概念是individual life(个人生活)和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为什么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政治的重要性)?因为18世纪中产阶级最早占领的并不是政治领域,所以他这里讲的其实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as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作为市民社会的一员生活的重要性)。”
如何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员生活,可能是不少国人都仍要学习或补习的一课。
作者:新京报特约记者 寇淮禹
编辑:李妍;校对:翟永军
原标题:林语堂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