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徐悦东 实习生/梁雨如
“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波拉尼奥的作品是在一家书店,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送一个杯子,杯子上有只小狗我很喜欢,所以当时就为了凑单买了一本他的书,读了之后发现还蛮喜欢的。”范晔这样介绍他与罗贝托·波拉尼奥作品的“初次相遇”。
4月23日,为纪念世界读书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了名为《波拉尼奥与视听文化》的圆桌会议,范晔和郝邵文(Javier Fernández)作为嘉宾参与会谈。范晔是北京大学西语系副教授,也是知名的西语文学译者,他的翻译作品中最著名的要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传世经典《百年孤独》。郝邵文现任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顾问,也是教授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的大学教师、漫画小说作者。2014年,郝邵文于巴塞罗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波拉尼奥和美国文学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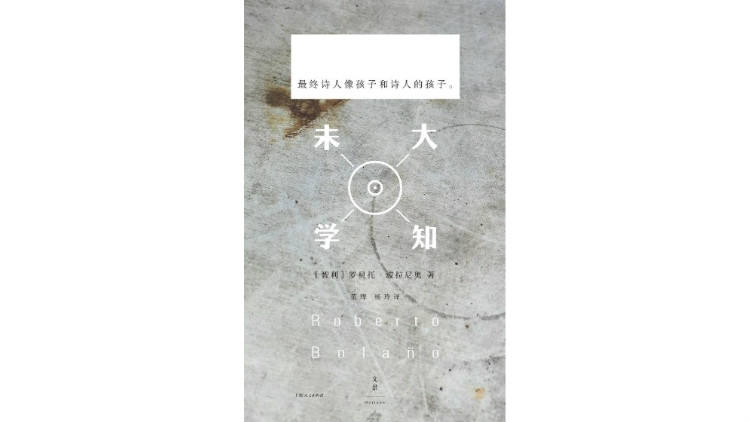
《未知大学》,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译者:范晔、杨玲,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范晔翻译了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La Universidad Desconocida),对他来说,翻译波拉尼奥的作品比翻译马尔克斯要稍容易一些,因为翻译诗集时范晔正在西班牙,和波拉尼奥这个“自愿的流亡者”一样,都是异乡人。范晔笑侃他是在“借着波拉尼奥的酒杯喝自己的酒”,“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某种心态上的对应,也就成了自己翻译的动力。通过翻译波拉尼奥的作品,范晔读到很多其他作家和诗人的作品,若不是借此机缘,可能无法接触到。

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2003),智利诗人、小说家
波拉尼奥是“新一代的文化英雄”
在拉美的文学爆炸之后,可能再也没有一个拉美作家像波拉尼奥这样引起大众的关注。范晔用“文化英雄”来概括波拉尼奥在中国的成功: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上一代拉美文学中的文化英雄应该是博尔赫斯,因为他几乎被塑造成了远离一切社会现实,完全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文学圣徒”的角色。
博尔赫斯“失明的智者”(Sabio Ciego)的形象,在范晔看来是带有隐喻的选择性失明者——不去看一切社会的现实。波拉尼奥是第二代“文化英雄”形象,是中国文艺青年的新偶像:最浪漫的绝望者,最成功的失败者,最受欢迎的边缘人。他给读者们带来了一些拉美文学爆炸之后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拉美文学新的一面。

波拉尼奥
波拉尼奥的作品,就像沙盘式的角色扮演游戏
范晔不止一次用游戏里的术语来形容波拉尼奥的作品,郝邵文将其视为范晔提出来的一个有趣的理论:RPG(Role Playing Game/角色扮演)游戏可以粗略分为两大潮流:一类是日系RPG,往往跟着一条主线走到底,支线选择和任务也是存在的,但是一般不会影响主线叙事;另一类是沙盘式的欧美系RPG,游戏主线只是个引子,玩家置身于一个遍布地下城和怪物的架空世界,面前是自由的成长选择和开放的冒险环境。前者给你一个故事,而后者给你整个世界。
波拉尼奥式的RPG看似属于前者,其实是后者。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支线,有时你经过这些支线时,并不知道这条线在整个故事里起什么样的作用。等你把游戏打通关了,可能发现还有很多情节和支线你并不知道,还在等你去重新探索,所以这个游戏你还得玩很多遍,甚至是换一个角色。读波拉尼奥的小说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妨把波拉尼奥的作品多读几遍,把其中的一个NPC(Non-Player-Character/非玩家控制角色)当作故事主角,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和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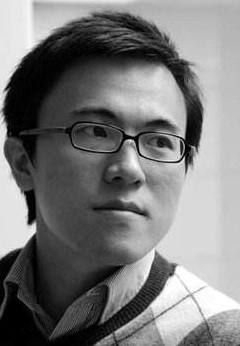
范晔
新京报:现在西语文学在国内越来越受欢迎,中国读者对许多西语作家都非常熟悉,比如马尔克斯、聂鲁达等。我们这次聊到的是波拉尼奥,你翻译他的作品的时候,这个作家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他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范晔:我只翻译了他的一部诗集,可能其他老师翻译了更多他的作品,他主要还是一个小说家。可能我个人和波拉尼奥之间有一些缘分吧。如果说我们性情相投的话,可能会有些夸张,但他的作品确实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感动和其他作家不能带给我的东西。
我理解的波拉尼奥的特点,比如他是一个“21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但他并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而是真正能把诗歌当作人生来活的人。今天我们说的“诗和远方”里,这个“诗”可能是装饰性的作用,在物质条件充裕之后需要诗歌来装点,但是对波拉尼奥来说可能不是这样,诗歌和文学是他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可能对很多文学青年来说是一个吸引人之处,包括他的小说作品几乎主人公都是诗人,这一点也挺独特的。
新京报:你翻译了波拉尼奥的《未知大学》,这本书里诗歌的部分不管是标点、内容、排版,还是装潢都不走寻常路,甚至还包括诗人的手绘符号,所以有不少读者读完之后觉得不知所云。作为译者,你认为该如何去欣赏这部作品?
范晔:是的。实际上波拉尼奥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打破了我们常见的对抒情诗比较狭窄的定义。我们觉得抒情诗应该是很优美的,意象美、情感细腻。但波拉尼奥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他让我们看到诗歌的定义并不是那样狭小的、优美的模样,也可以是别的样子,所以我们说,这是“大颗粒”的诗歌,一种更加粗糙的东西。他的诗里面有一些口语化的、叙事性很强的东西,看起来甚至不像诗。
我认为读者觉得不知所云有两个原因:首先,他的诗和他的其他作品有一些很强的互文关系,如果没读过他的其他作品,一上来就读诗可能会有点门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的诗和我们对抒情诗的预期不大一样。所以我翻译的时候也希望故意做成更加粗糙的、“大颗粒”的诗歌,或者“反抒情”的诗歌。“反诗歌”的概念是智利诗人帕拉(Nicanor Parra)提出来的,“反诗歌”有意将诗歌进行口语化、讽刺和幽默化,跟传统诗歌有一定差别。其实这也不算是非常新奇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不过我觉得这是好事,不管阅读诗歌还是别的文学作品,眼界扩大一些不是坏处。
新京报:你提到过拉美文学的译介其实是有大片空白的,不管是在文学爆炸之前还是之后的作品。那么,你对新一代的译者有什么样的期待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翻译首先特别难,就像你微博里也写到过“译到昏厥”之类的感想;其次文学翻译的收入又不是那么可观。
范晔:是非常地不可观。我也不敢说有什么期待,也并没有什么资格谈期待。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给文学译者一个相对体面的、有尊严的报酬。现在翻译一本书,都不好意思跟人说自己拿了多少稿费。
据我所知,至少在西语领域,光靠文学翻译能养家糊口的人恐怕没有。这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而且也许短时间内并不能改观。但我希望年轻一代译者们,还是能够得到和我们付出的劳动相对称、相适应的报酬。这个东西,喜欢就是喜欢,热爱是强求不来的。虽然我是做文学的,但我也不会去强求我的学生热爱文学,不过作为一个读者去欣赏还是非常好的。当然,作为一个读者,遇到好东西忍不住要分享,那可能就一步步走向“不归路”了,就像我这样。我最初是出于分享的冲动,比如有朋友不会西语,但是你希望他能读到,这可能就是我做翻译的初心。
记者:徐悦东 实习生:梁雨如
编辑:徐伟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