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安全”也许很重要。还记得去年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200年馆藏付之一炬令全球痛心。火灾当天,有学者赶回博物馆,看着已经不受控的火势,看着被烧成灰烬的纸质藏品飘散到附近的居民区,毕生心血毁于一旦有多痛苦,并非外人所能真正理解。
做到了安全,接下来要想怎么做到让更多人与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相连接。文物虽然藏着过去的故事,但只有与更多的人接触,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博物馆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它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智识权力的平民化,伴随着理性启蒙的抬头,可今天的人们似乎对博物馆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把它矮化为了“藏宝阁”。
陈平原在《大英博物馆日记》里记了这样一件事。一日他去参观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未见展品,先闻乡音。
男高音:“这算什么宝贝,比咱们故宫差多了!”
男中音接道:“别说故宫,连省博都比不上。”
女中音更有把握:“单是上回从香港买回的那几件圆明园的东西,就比这强!”
如此斩钉截铁的评价让陈平原大吃一惊。“不说起码的文明礼貌,单是面对如此深邃的知识的海洋,总该有点敬畏之心吧,为什么总想着争强好胜?博物馆里,偶尔也有人窃窃私语,但像‘咱老乡’那样高谈阔论者,已近乎在中国也会被立牌禁止的‘大声喧哗’了。”
这个片段细究起来很有意思。首先,在我们身边,用“珍宝”来衡量、阐释博物馆展品的人,到今天依然不少。其次,在博物馆不能大声喧哗,几乎成为了全世界的共识。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博物馆史中找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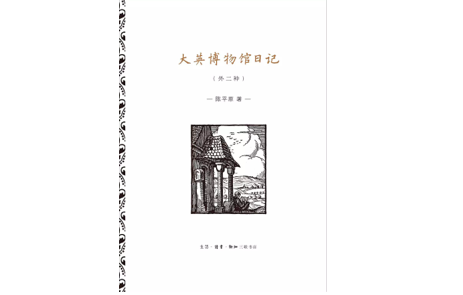
《大英博物馆日记》,作者:陈平原,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2月
智识与权力
现代博物馆因何而生
现代博物馆属于公共机构,它的诞生和发展都与政治紧密相关。1793年8月10日,法国卢浮宫成为最早向所有公众开放的皇宫,艺术品、文物再也不是特定阶层的人才能接触的珍藏。在博物馆真正成为公共机构之前,18世纪的英国贵族可以因为受不了“底层阶级”的粗鲁行为将他们拦在自家博物馆大门之外,除非他们能够从与贵族相熟的绅士或女士手中获得一张入场券;1785年,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抱怨为了获得参观大英博物馆的凭证,他要等上14天。
大革命的到来让博物馆中的藏品脱离了私人所有物的属性,归全民所有。在旧时代,它们与特权联系在一起,新时代,它们成为启蒙公众的工具和体现民族、国家价值的载体。法国内务部长在卢浮宫开放前夕写到卢浮宫将展示国家巨大的财富,向每个时代展现法兰西的繁荣,博物馆将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最佳例证。
伴随着博物馆启蒙属性的发展,人们开始试图用博物馆来复制世界。在《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中,作者史蒂芬·康恩提出,19世纪末,人们建造博物馆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物品和文字一样,是智识和价值的源泉,博物馆中的任何物件,都应该在人们(未经专业训练的参观者)第一眼看见它时讲出自己的故事。博物馆不能只展现展品,还要能让参观者管中窥豹,探知系列展品背后的文明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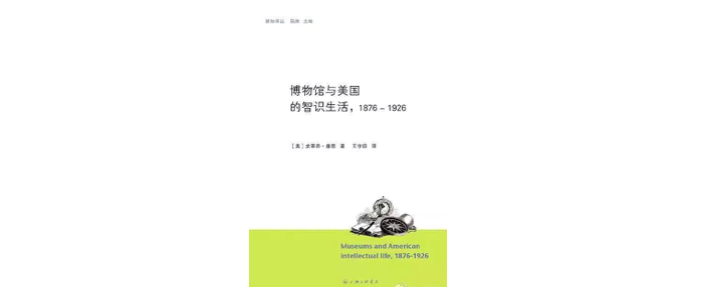
《博物馆与美国的智识生活》,作者:(美)史蒂芬·康恩,译者:王宇田,版本: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从这个意义讲,博物馆成为了文明教化仪式的场所。它一方面象征着知识权力的平民化,另一方面也在通过仪式化的布展、观展来强调背后的智识崇拜和国家价值崇拜。在古老的文明面前,在崇高的集体价值面前,我们都是渺小的待受熏陶的个体,所以我们需心怀敬畏、轻言低语。大声喧哗之所以是无礼的表现,在于破坏了这种仪式化的传授知识的氛围。
在这种理念下建造的博物馆,需要万物各居其所。如奇异的蝴蝶标本虽然能让参观者眼花缭乱,但展出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理解自然背后的规则,更重要的是表现科学可以通过理性来揭露、控制规则。所以博物馆中的展览与纯粹的艺术展览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更看重视觉的冲击力,更关心如何调动感受力而非秩序。
“混乱是自然界的规则,秩序则是人类的梦想。”博物馆的兴起伴随着人们对理性和启蒙的推崇,美国学者称“中世纪属于教堂,20世纪属于博物馆”,正是因为它象征那个智识爆发的时代。
中西碰撞
中国语境下的博物馆
卢浮宫向公众开放后,有不少写作者向它表达了诚挚的赞美。1855年,英国游记作家贝尔·圣约翰记叙了他第一次游览卢浮宫的经历,说卢浮宫不再是上演权力悲喜剧的场所,不再是阴谋、猜忌和邪恶的战争计划的诞生地,它成为为数众多(主要是艺术品)的物品的庇护地。
“我们在那儿至少看到了所有文明残骸的一鳞半爪。”
1855年的这句“所有文明”,倒是点出了后世被很多人忽视的尴尬,虽然文明无国界,但世界上许多知名博物馆中令人叹为观止的收藏,建立于常年对他国的殖民侵略之上,建立于贪婪的物欲之上。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战中他搜刮艺术品到自己的故乡企图建造一个最大的艺术博物馆。(艺术品在二战中的命运,可能比想象中更复杂|《劫掠欧罗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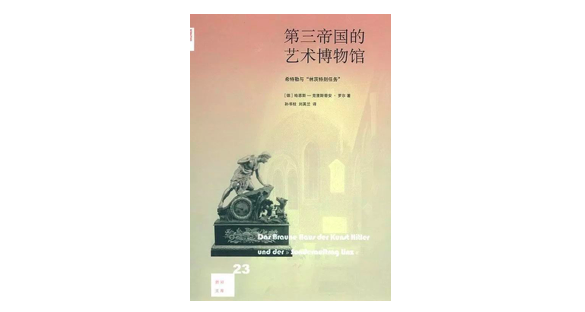
《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作者:哈恩斯-克里斯蒂安·罗尔,译者:孙书柱 / 刘英兰,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4月。多数艺术品并非来自盗抢,犹太人为求自保积极卖画、第三帝国人民主动捐献、欧洲艺术商人为了赚钱纷纷向纳粹抛出橄榄枝……历史并非非黑即白。
因成为半殖民地而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弱势的一方,但也在接纳“博物馆”理念时,通过思想碰撞加深了启蒙。中国古代没有“博物馆”,有的珍品收藏处,属于私人收藏。文物、艺术品品鉴是贵族士大夫的专属活动,象征着统治阶级的文化趣味。
打开国门后,第一批到国外“取经”的国人,对博物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大多是文士,对商品经营的兴趣,当然不如对文物的大。然而当时清政府派出的官员,大多“睡眼惺忪”地看世界,如果把外国夸得太好,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而夸也要显得自己更有“款儿”。1841年出国考察的陈逢衡,在《英吉利纪略》里这样夸英国:英国有书画,有图籍,有大学,有博物馆,都是国王命令建造的,看来这个国家也挺重视文教的嘛。
第一个把“museum”翻译成“博物院”的人,是近代改良主义政治家王韬。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要建立“博物院”,如梁启超。二十世纪最初一二十年,全国建立了多处“陈列所”和博物馆。近代实业家张謇认为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留存往迹,启发未来”。他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收购藏品,不要官方强迫,需藏家自愿。张謇的南通博物苑的自然标本,便包括日本的三叶虫化石、南洋群岛的猩猩、俄罗斯的斑鼠等。
辛亥革命后,建立博物馆被更多地提上议程,此后博物馆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教化任务。中国博物馆的数量也大幅度提升,二十世纪初仅有几家,1929年有10家,1936年有72家,1949年受战争影响减少到21家,1980年有365家,1990年有1013家,截至2016年,全国注册在案的博物馆共有4873家。(数据转引自故宫博物院研究者吕济民论文《中国博物馆事业一百年》;段勇《当代中国博物馆》)
博物馆的建立依然受着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博物馆的龙头老大“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于1925年,在此之前,为防止前清遗老觊觎文物,北洋政府将保存于热河避暑山庄和沈阳盛京故宫的文物运到北京,仿效外国将紫禁城前朝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后来故宫博物院因战争一分为二,南北相立,从诞生、成长到离乱,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沉浮悲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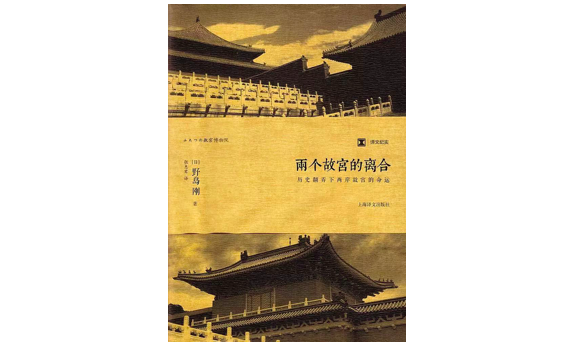
《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野岛刚,译者:张惠君,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1月
不只是“陈列宝物的建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展览
将博物馆视为“宝物”的收藏之地,还要在珍贵程度上彼此争个高低,大概因为博物馆在公众化之前,都是以私人收藏的“珍宝馆”形式存在,加之文物承载的文化、智识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让彼此较着劲儿人们忍不住要比上一比。
若真要比一比,我们的博物馆虽然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发展,但很多离真正的“高水准博物馆”尚有差距。陈平原在《大英博物馆日记》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所谓达到“世界知名博物馆的水平”,绝非仅限于建筑外观,更重要的是对于国内外观众的巨大吸引力。而这,既取决于藏品质量与编排水平,也受制于观众的修养和趣味。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高水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30座大型博物馆轻松。
这些意见是否勾起你参观某些博物馆的经历?草草浏览过后,无法留下任何记忆点,无趣。空有恢弘的地标性建筑外观,却失去了展品的历史内核。对于博物馆的建筑应该建成什么样是有分歧的,陈平原就对博物馆建筑所追求的“当代意识”不以为然,他喜欢大英博物馆保持原来的整体美感,不喜欢贝聿铭在卢浮宫前设置的金字塔所制造的古典与现代的尖锐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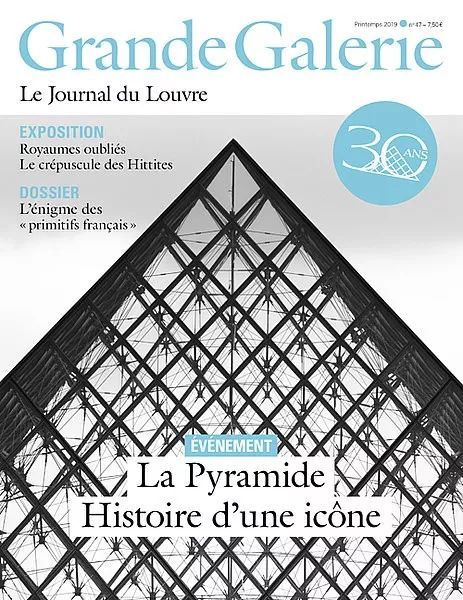
卢浮宫官方杂志第47期封面,庆祝金字塔建立30周年(图片来自卢浮宫官网)
建筑审美与个人喜好相关,需要我们反思的是,那些宏大的建筑物是否浪费了空间和金钱,是否成为了建筑师们的炫耀物而非实在的展览场所?重“建筑”,轻“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属于比较普遍的问题。
美国艺术史学家大卫·卡里尔在《博物馆怀疑论》的序言中指出商业逻辑下博物馆的恶性循环:建筑和临时展览越来越贵,布展者更费力去吸引参观者观展,而那些高质量的永久性展览却鲜少有人问津。但卡里尔也指出,如果因此抱怨买票参观的观众是很荒唐的,参观者众多说明学者在说服人们参观某些类型的展览是何等成功。抱着怀旧的态度,希望回到纯粹展览式的博物馆,鄙视博物馆中开设的书店、礼品店、饭店浪费空间,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面前是一种徒劳。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多少有点排斥围绕博物馆与艺术的“高雅叙事”所暗含的对受众的指责。与培养特定的“雅趣”相比,给予大众接触各种类型的艺术品、文物的机会和自由,或许才是关键所在。

《博物馆怀疑论》,作者:大卫·卡里尔,译者:丁宁,版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5月
所以问题还是回到博物馆的功能和本职问题之上了。博物馆如何丰富自己的展品,如何提升编排水平布置有吸引力的展览,如何制造机会让更多的人与展品相遇?丰富展品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强人所难,就像卡里尔所说,任谁再怎么努力,都不可能会有第二个大都会博物馆了。艺术品、文物虽仍有所流通,但西方博物馆不太可能出售自己的藏品了。不过,通过出借协议,通过策划编排来吸引人们走进博物馆是一条可行之路。这不免令人想起年初王羲之《祭侄文稿》引发的争议,情绪过后到现场参观的人们都不后悔为此一行。
近年来国内博物馆通过社交媒体,大大增加了普通人与文物接触的范围,并对文物给予了颇具当下感的解读,比如红遍网络的文物表情包。但这些都无法替代亲自走进博物馆观展。博物馆不只是一栋存有“宝物”的建筑,艺术品、文物线索勾连起来的全人类的文明史,才是它更大的价值所在。
作者:吕婉婷
编辑:徐悦东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