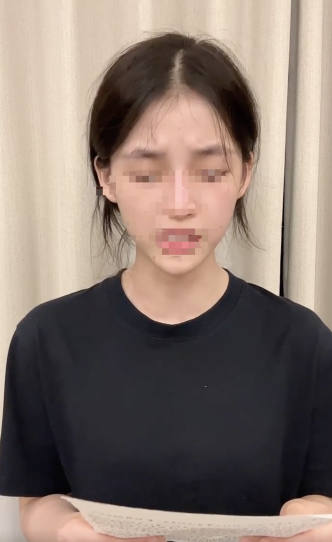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世界历史体系之中,非洲都被视为游离于历史和进步之外的存在。杰克·戈德斯通的《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1500—1850)》一书中曾经提到,“西方的崛起,曾被视为世界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历程之一。这一进程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出现,继之以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和骑士制度,经过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结束于西欧和北美对全世界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控制。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们,只有在遭遇欧洲探险或被殖民时才会被提到。他们的历史,也就是从欧洲的接触和征服才开始的。”

长久以来,在迪士尼卡通等动画形象中,穿着十分简陋的非洲食人族,在悬挂于坑火上方的巨型锅里炖煮着他们的受害者,这似乎成为人们对非洲人形象的直观认知。在欧美知识分子群体中,大量流传着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
比如,伏尔泰在谈到非洲人时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这些‘动物’们将懂得如何好好耕种土地,用房屋和花园美化土地,了解星星的运行路线。对于任何事情来说,这都是一个必须的时刻。”黑格尔对非洲的看法更为宽泛:“我们对非洲的正确理解是,非历史性的、不发达的精神,仍然处于单纯的自然条件中,而且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开端时,才必须在这里表现出来。”
即便在今天,类似的观点也会出现,比如2017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表示,与欧洲相比,“非洲面临的挑战与欧洲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而且更深”,“这是文明的(挑战)。”
但一个可能仍然算得上鲜为人知的事实是,非洲从未缺少过文明,也绝非像人们通常所描述的那样与世界进程截然相反。在一些通俗易懂的学术新作之中,呈现了非洲的过去和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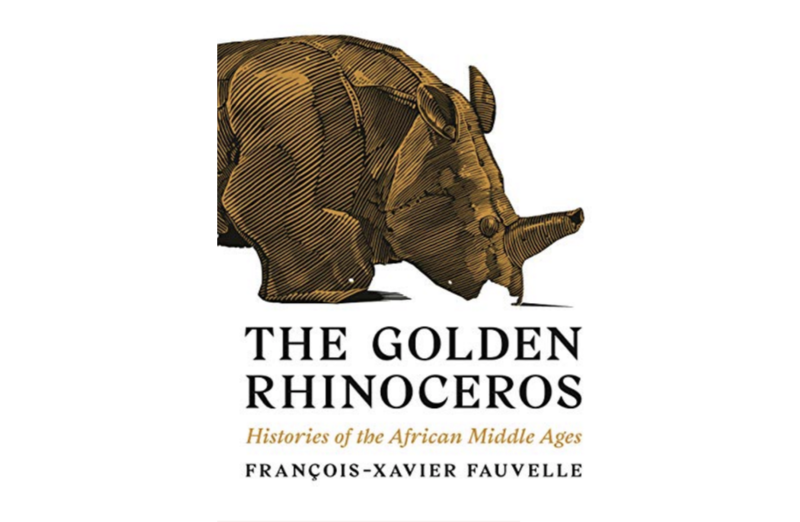
《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The Golden Rhinoceros: Histories of the African Middle Ages),F.富威尔-艾玛尔(François-Xavier Fauvel)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年12月版。
法国著名学者F.富威尔-艾玛尔的新作《金犀牛》一书终于认识到非洲在中世纪的重要作用,他首次向读者揭示了越来越多历史学专家开始形成的一个共识——中世纪非洲的存在。
艾玛尔认为,中世纪是非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一个介于埃及、努比亚和阿克苏姆等古代文明之间的时期,这些地方都留下了极为壮观的考古遗产,大约在1500年以后,奴隶贸易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深深地伤害了非洲。
在一系列轻松有趣的章节中,艾玛尔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中世纪的非洲并不缺乏文化成就。例如,早在9世纪,就有证据表明,北非定居点与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奥达格霍斯特(Aoudaghost)等商业城镇之间,就存在长距离贸易。许多制造出来的铜制品被送往南方,以换取金沙,这些金沙被铸造成锭,再铸成阿拉伯世界快速崛起所需要的大量铸币。为了说明这些商业交易在10世纪晚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艾玛尔描述了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一位商人给摩洛哥西吉玛萨镇的一位商人开出的一张总额为42000第纳尔的支票。
在艾玛尔书中,最有趣的故事来自于十四世纪早期的马里王国。在哥伦布远航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位名叫阿布·巴克尔二世(Abu Bakr II)的马里统治者被认为装备了一支由200艘船组成的探险队,试图发现“大西洋的最远界限”。除了一艘船外,远征队没有返回。幸存者说,“在公海上出现了一条湍急的河流……其余的船先走,到了那地方,就不见了。”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迈克尔·A·戈麦斯(Michael A. Gomez)、托比·格林(Toby Green)和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人认为,这意味着马里船只是在大西洋的加那利洋流(Canary Current)中被捕获的,加那利洋流在马里所在纬度向西横扫一切。
据推测,阿布·巴克尔二世的回应并不是放弃探险的梦想,而是装备了一支新的、规模更大的探险队,这次有2000艘船参与,而且由他亲自指挥。那是他最后一次露面。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故事,只是因为当阿布·巴克尔的继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24年至1325年前往麦加朝圣时,马穆鲁克王朝(Mamluk Dynasty)的大臣问他是如何掌权的,并记录了他的回答。除此之外,并没有阿布·巴克尔的这一企图的任何记录痕迹。
艾玛尔花了很大力气,试图去推翻人们普遍怀疑的、将阿布·巴克尔的探险与哥伦布(Columbus)航行前非洲人存在新大陆的未经证实的说法相联系起来的努力。他用一系列贯穿其中的史实,交替解释为什么穆萨会讲述一个如此非凡的故事。神秘的阿布·巴克尔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似乎超出了现代历史调查的能力。
然而,1312年掌权的曼萨·穆萨在他的时代留下了如此强大的印记,今天的人们却对他知之甚少,这是很不寻常的。最近有人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关于他的财富规模的猜测几乎完全是基于他在前往麦加途中在开罗停留的三到十二个月。阿拉伯语的来源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给人留下了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这样的财富在任何地方都是罕见的。
比如,Badr al-Din al-Halabi写道,穆萨“(在开罗)穿着华丽,骑在马背上出现在他的士兵中间”,有一万多名随从。另一名消息人士称,他“带了14000名女奴来为自己服务”。第三个人谈到了这次朝圣的“盛况”,说穆萨“率领6万人的军队在他之前骑行,还有500名奴隶,每个人的手中都持有金质的手杖。”

1934年,于南非北部靠近津巴布韦边境的马普古布韦发掘出土的金犀牛雕像。
显然,《金犀牛》一书终于认识到非洲在中世纪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了解这位历史学家的技艺提供了一扇窗。从七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到十五世纪欧洲人的探险之旅,非洲一直是商品和思想交流的中心。这是一个属于非洲的黄金时代,加纳、努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地成为文明的十字路口,非洲皇室、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中世纪的全球化世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金犀牛》将这个未被歌颂的时代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把读者从撒哈拉沙漠和尼罗河流域带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和非洲南部。
凭借零散的文字资料以及多年的考古学家经验,艾玛尔煞费苦心地重建了一个非洲的过去,这个过去在历史上常常被否定,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他研究了红树林中被毁的城市、精美的艺术品、珍贵的手工艺品,如马普古布韦的金犀牛、古代地图,以及地理学家和旅行者留下的记录——这些非凡的发现对政治和建筑成就、贸易、宗教信仰、外交事件和个人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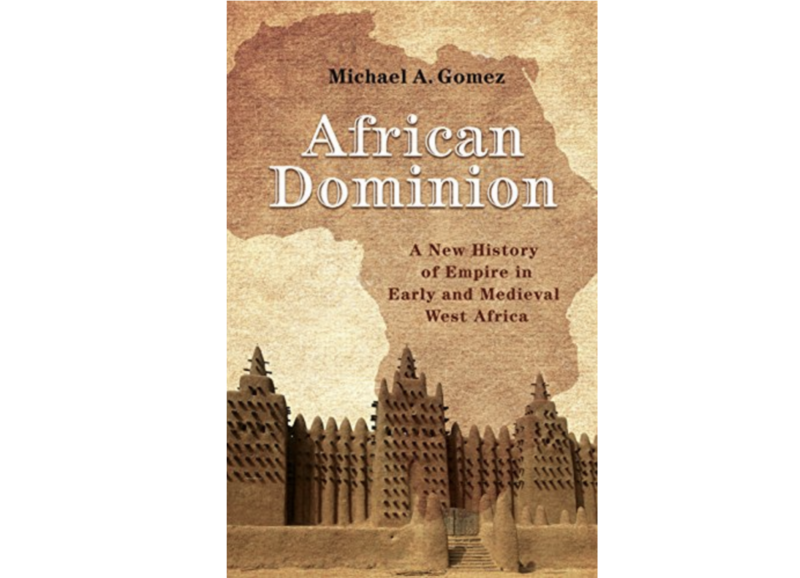
《非洲统治:早期和中世纪西非帝国的新历史》(African Dominion: A New History of Empire in Early and Medieval West Africa),迈克尔·A·戈麦斯(Michael A. Gomez) 著,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年1月版。
这是一段开创性的历史,把西非和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全球背景联结在一起。纽约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A·戈麦斯发现了极为有趣的一点,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马里王国领袖穆萨极尽铺张的使用黄金时,他庞大的奴隶随行人员可能已经将非洲的形象定义为一个黑人劳工取之不尽的地方。长期以来,非洲的一些地区一直是近东奴隶市场的供应地,穆萨朝圣后一个多世纪,它就开始向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供应奴隶。
同时代的消息人士估计,这位马里皇帝带着13吨至18吨的纯金,完成了2700英里的开罗之旅。这些黄金在清真寺和沿途各级官员手中分发,并施舍给穷人。穆萨个人向开罗的马穆鲁克统治者纳西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捐赠了大约400磅黄金,造成了该地区的黄金价格大幅下跌。根据一些说法,这导致该地区的黄金价格多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而穆萨也因为挥霍无度,不得不借钱回家。
戈麦斯希望可以通过穆萨的故事,寻找其中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穆萨朝圣的十年内,马里及其王国开始出现在欧洲地图上,其中最著名的是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它引诱伊比利亚的淘金者沿着非洲海岸寻找穆萨的金矿。
最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布洛克艺术博物馆(Block Museum of Art)举办了一场名为“黄金商队,时光碎片”(Caravans of Gold, Fragments in Time)的大型新展览,曼萨·穆萨的身影赫然出现在了展览中心。就像最近许多关于中世纪非洲的文章一样,《目录》指出,撒哈拉沙漠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为一个屏障,将一个名义上的黑人非洲与同样名义上的白人或阿拉伯人非洲分隔开来。
在现实中,沙漠不仅是可渗透的,而且有大量的交通,就像海洋一样,贸易以及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来回传播,并对世界产生影响。传达该地区历史重要性的部分困难在于缺乏文献资料,而此次展览及其目录通过展示该地区的文物遗产——从陶器碎片到雕塑、黄金砝码和硬币——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过去,中世纪早期世界历史的书中,西非的身影只会出现在外围,但这本《非洲统治》却讲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显然,这是该地区历史上第一本关于这一时期的图书,戈麦斯将政治和社会历史交织在一起,利用丰富的资料来源,包括阿拉伯手稿、口述历史和最近的考古发现,揭示了种族、性别和种姓如何在非洲和更广泛的全球历史中出现的新愿景。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这种差别产生于殖民时期,但戈麦斯指出,它们的发展要早得多。
戈麦斯以萨凡纳和萨赫勒地区为重点,通过商人、学者和朝圣者的方式,追溯了西非与北非和中部伊斯兰地区的思想交流和影响。伊斯兰教在西非的发展,伴随着包括奴隶在内的商业活动的不断加强,导致了该地区特有的一系列政治实验,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崛起。
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谁可以合法地成为奴隶,这一问题连同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关于种族、性别和种姓的新观念的形成,而这些观念早在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出现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有关于全球历史中早期非洲的全新故事,将成为未来许多年这一主题的标准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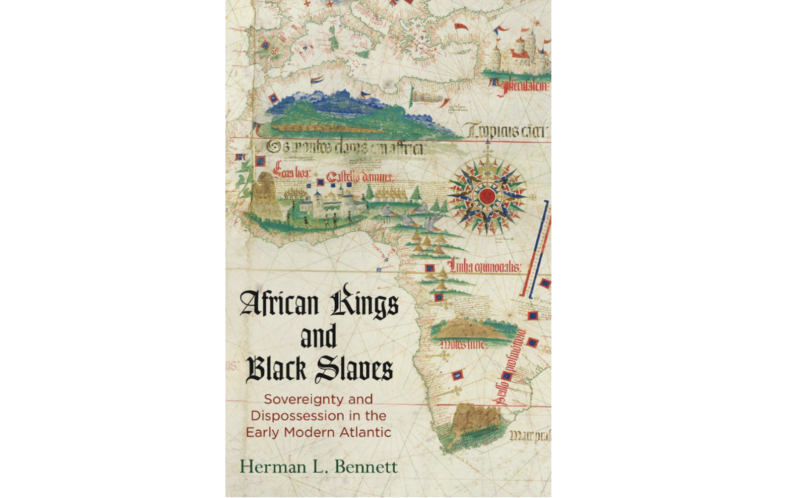
《非洲国王和黑奴:近代大西洋早期的主权和剥夺》(African Kings and Black Slaves: Sovereignty and Dispossession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赫尔曼·L·班尼特(Herman L. Bennett) 著,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8年11月版。
早在1441年,早在其他欧洲国家遇到非洲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小型商船就已经在西非海岸航行,在那里他们与拥有大片领土和权力的非洲王国做生意。在这个过程中,伊比利亚人发展了对非洲政治格局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他们承认特定的君主,绘制他们的政治范围和性质,并根据他们的统治者将臣民分组。
在《非洲国王和黑奴》一书中,赫尔曼·L·班尼特将注意力延伸到了殖民以前的非洲外交:葡萄牙早期与非洲王国的关系。班尼特从一次被他称之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业典礼”的事件展开了这一主题。
1441年,一支由安唐·贡萨尔维斯指挥的葡萄牙远征队在今天的毛里塔尼亚的卡波布兰科附近登陆,在与一名骑着骆驼的男人发生冲突后,抓住了第一个俘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摩尔人(不是种族名称)。几个小时后,在夜幕降临时,葡萄牙人抓住了他们的第二个俘虏,一个被他们称为“黑摩尔人”的女人,这将对欧洲对待奴隶制和非洲的态度产生巨大的、持久的影响。
正如班尼特所指出的,在欧洲与非洲的接触初期,新来者对他们遇到的土著民族的认知还非常混乱,新开发的西非土地被各种各样的人认为是圭恩、埃塞俄比亚甚至印度。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成为了黑暗的开始。

黑奴贸易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急剧增长、欧洲殖民和种植园农业在新世界站稳脚跟之后,我们显然远离了一种观点,即非洲人只是生活在近乎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班尼特把这些早期的邂逅赋予了重大的意义。他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搅乱现有的西方及其崛起的叙事”,在这本书中,早期现代非洲的历史传统上被框定为从“野蛮人到奴隶”的直接飞跃。班尼特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长久以来,人们忽视了“非洲和非洲人在1492年前伊比利亚主权演变和帝国扩张中所扮演的角色。”
班尼特挖掘了欧洲和非洲的历史档案,重新诠释了非洲与欧洲持续互动的第一个世纪。这些遭遇并非简单的经济交易。相反,据班尼特说,这些冲突涉及对外交、主权和政治的冲突理解。班尼特揭示了非洲国王是如何要求伊比利亚商人参加复杂的外交仪式,建立条约,并与自治领土谈判贸易惯例的。他还展示了伊比利亚人是如何将他们对非洲主权的理解建立在中世纪欧洲以罗马民法和正典法为基础的政治戒律之上的。在伊比利亚人看来,非洲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准则,在决定谁是或者不是主权人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判断决定了谁可以合法地成为奴隶。
通过对早期现代非洲与欧洲的接触的研究,非洲国王和黑奴重新评价了主流的描述,即这些交流完全是通过奴隶贸易和种族差异进行调解的。通过询问欧洲人和非洲人是如何配置主权、政治和主体地位的,班尼特提供了一种对移民身份的新描述,这种身份对美洲奴隶的经历产生了影响。
记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吴鑫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