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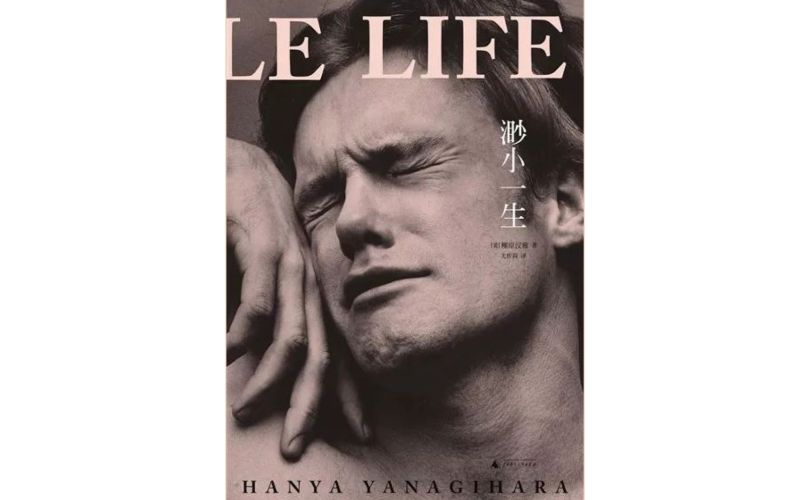
《渺小一生》,作者:柳原汉雅,译者:尤传莉,版本: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在大学毕业之后,裘德和他的朋友们进入到了一段真空的人生当中。他们成了所谓的“后男人”,怀揣着艺术理想和年轻人的激情,但是没有任何社会资历。同时,裘德还缺乏对自身的认同感,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种肤色的族群,身体残疾也让他陷入痛苦,怀疑自己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裘德和另外三个朋友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新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接触彼此的秘密,帮助对方,偶尔也会产生些误会与矛盾。他们既在一个缥缈的美国梦想中奋斗,又在迷茫中寻求自我。将友情视为最后精神寄托的裘德,最后还是向朋友们吐露了自己曾遭遇性侵和虐待的过去。但在两个朋友因为一场车祸去世后,裘德再次陷入到充满压迫感的陌生环境中,最终选择自杀。
小说作者柳原汉雅用了60万字的篇幅来缓缓讲述裘德生活中那一点一滴的痛苦,让读者感受到了裘德那渺小一生中经历的噩梦、希望、欢愉以及与朋友和同性恋人之间难忘的故事。整本书的叙事视角非常狭小,完全局限在几个男性朋友的活动与回忆中,但这种情感真挚的小圈子生活,正是许多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宫照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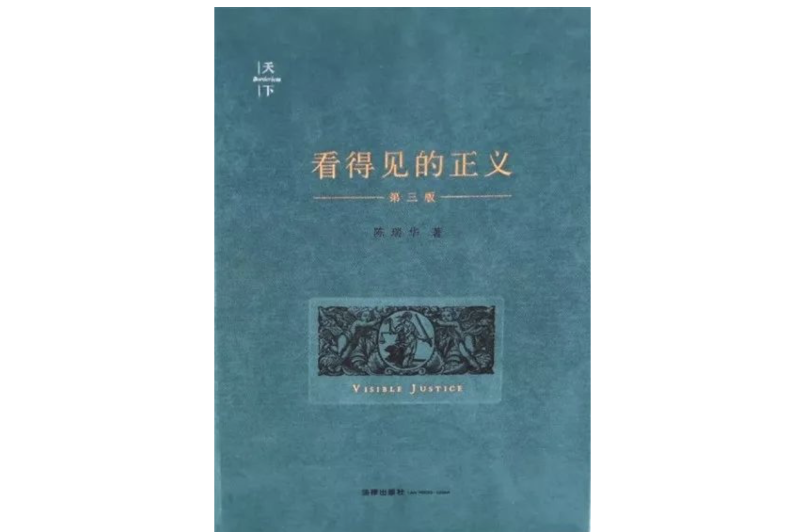
《看得见的正义》,作者:陈瑞华,版本:法律出版社·天下 2019年5月
在当今观念世界,极少有一个概念能像“司法正义”那样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或观念立场上大相径庭,甚至彼此冲突,一旦他们个人成为受害者,都会渴望司法正义的实现。当然,价值目标相同并非就意味着司法制度、司法观念也必然相同。而在那些不同之中,“程序”在审判中的地位如何是最大的不同。
法学家陈瑞华与他的诸多同仁一样,将“程序正义”视为司法正义最重要的部分,没有程序正义,正义就可能只是偶然或部分实现。如果追求结果,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实现,而是难以保证持续实现。在《看得见的正义》一书中,他通过论述“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不能证明的事实就等于是不存在的”“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等司法警句和常识阐释“程序”的重要性。他简练通俗的文笔使该书与众不同。《看得见的正义》目前已经出版三版,此前分别由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一版、第二版。同以往一样,陈瑞华根据一段时间内的司法案件和司法讨论作了修订。(罗东)

《梅耶荷德谈话录》,作者:(俄)梅耶荷德,编译:童道明,版本:商务印书馆 2019年6月
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喜剧之王》,让中国观众记住了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大作《演员的自我修养》。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生、戏剧家梅耶荷德的作品在中国却有些鲜为人知。在20世纪初的俄国剧坛,梅耶荷德也是戏剧表演界的大IP,他提出了与写实主义戏剧分庭抗礼的假定性戏剧理论,从梅兰芳的中国传统戏剧中看到了“未来戏剧艺术”的方向。大师级导演爱森斯坦说,“没有梅耶荷德就没有我。”实际上,他为苏联培养出了一整代的电影、戏剧导演和演员。
上世纪20年代,苏联剧坛各种流派斗奇争鸣。梅耶荷德的舞台艺术令人耳目一新。梅耶荷德的戏剧深受文学、尚且年轻的电影、音乐、绘画、杂技等艺术门类影响。不过,十月革命的风暴及其“严峻的美”,对他的冲击则如同风暴。这风暴令他的经历独一无二。翻开这本1986年后首次再版的《梅耶荷德谈话录》时,苏联先锋艺术的时代感扑面而来,“艺术的火药时代还没有过去,而眼泪会把火药浸湿。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伤感主义的艺术。”不过,到了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号一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很快被奉为正宗,梅耶荷德的标新立异的戏剧主张
逐渐被视为异端。梅耶荷德之死令人唏嘘,1955年苏联最高法院才为其恢复名誉。许多人并不知道梅耶荷德的一生,却谙熟他的戏剧手法在今日的存留。比如,写意的、不用大幕的舞台布景、框式舞台的突破、演员下剧场表演、道具特技、插入电影片段、艺术性的谢幕、灯光特写等今天的戏剧日常,仍有趋力让我们回到梅耶荷德的美学以及他所身处的波澜壮阔的时代。(董牧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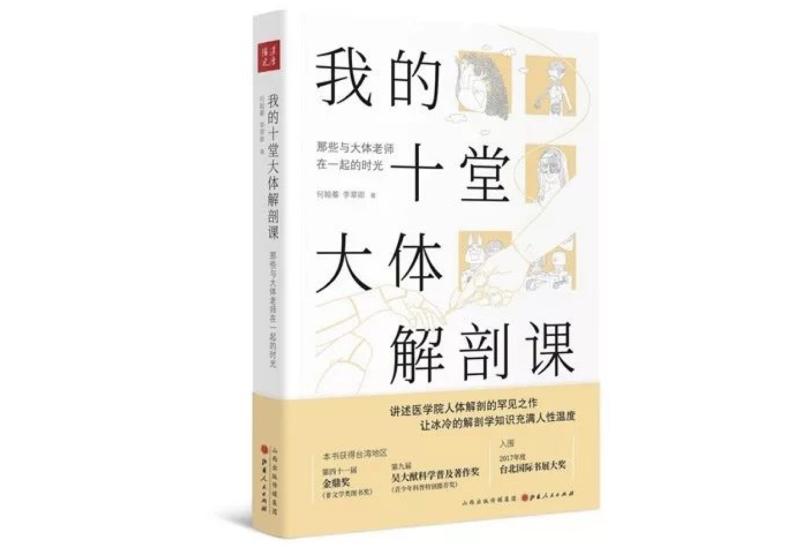
《我的十堂大体解剖课》,作者:何翰蓁、李翠卿,版本: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5月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与大体老师在一起的时光”,“大体老师”是谁,对医学院有适当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是那些捐出自己的躯体供医学院进行解剖教学的人们。作者何翰蓁在台湾地区慈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人体解剖课,这本书首先是一本科普书,作者按一学期解剖课的顺序,讲授了从手部、胸腔,直到生殖系统、颜面、脑部的构造和功能,简明通顺,可读性不错。但它最能打动人的内容显然是那些有关大体老师的故事,是学院和师生对待大体老师的尊重和情谊,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生与死的思考。是这些内容,赋予了这本薄薄的小书独特的温度。
书中讲述,他们将大体老师的奉献视为“深情又沉重的一份托付”,为了让学生们能以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对待大体老师,学校要求学生在课程开始前进行家访,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属,了解他们的故事。而在期末考试结束后,绝不允许将支离破碎的大体直接火化,要求学生必须将器官、肢体一一缝合,让大体老师“恢复原貌”,再举行送灵典礼。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作者是真切地将大体老师视为一个人、一位无语良师,而非教学道具。捐献遗体这种特别的处理死亡的方式,也在作者的讲述中显得更为神圣和可敬。(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