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袁剑
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外部世界哲学,因为在构筑自身的世界知识图景期待中,存在着一个从理解式获取到自主性创造的过程。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主编的《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外部区域与国家民族历史叙述的必要知识与可能。
国家认同与民族历史总是相辅相成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民族历史叙述赋予民族国家以一种地位,使之得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稳定下来。……这种现代性源于西方,并从那里扩散开来,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扎根。在西方首次获得凯旋的历史性民族宏大叙述,并未在各地被简单复制。他们遭遇到书写与叙述民族历史的其他形式,并以各种方式得到调适、拒斥和重整。”
这段话实际上就提醒我们,曾经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无往不利的西方民族历史叙述框架,正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逐渐失去其普遍性意义,欧洲殖民帝国之外的民族历史书写,正在呈现出新的路径。
欧洲
民族历史书写的发源地
作为所谓的近代民族历史书写发源地,欧洲知识界的道路可谓曲折而多样,其中既有英国叙述所呈现的文明化进程,同时也存在着以法国为代表的进步启蒙话语,更存在着多民族帝国的复合型框架。虽然时代在变,在政治结构与共同体认知方面,如今的欧洲已经跟数百年前的欧洲有了很大差异,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21世纪初,民族历史与民族标准是否真的已经不可挽回地属于过去?今天,在欧洲,许多历史学家们都在寻求把历史书写欧洲化和地区化的方式,以期克服民族范式的许多限制。但是,几乎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民族范式仍然继续成为最为强大的历史叙述的建构动力。”
作者认为,在欧洲的语境中,民族归属感和认同问题,作为民族历史当中极为重要的因素,都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欧洲的新民族观逐渐形成,并认为“只有在欧洲‘鞍型期’(Sattelzeit,1750-1850),随着现代性的到来,对于本民族的忠诚感才成为使国家合法化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只有到那个时期,民族才取代并混合了宗教、王朝观和封建主义,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中,提供了关键的黏合剂。”这种“黏合剂”不仅重塑了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在当代依然发挥着巨大的认同性影响。

反映苏格兰与英格兰民族冲突的经典电影《勇敢的心》。
在这个过程中,关于地缘政治的认知与想象,为国家特质与合法性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可以说,那种全欧洲最为成功的民族历史,把各种科学性学科的发现联结起来,并给出一份对民族特征的详尽描述。例如地理学,瑞士、英国和俄国的民族叙述,都受到下列界定的深刻影响:即瑞士民族是被阿尔卑斯山所塑造的,英格兰民族是被海洋所决定的,俄罗斯民族是被俄罗斯帝国的广袤疆域——东抵太平洋,西至欧洲的中东部,北接北极圈,南邻亚洲次大陆——所锻造。”当下我们对于诸如“高山之国”、“千岛之国”甚至“马背上的国家”的想象与认知,实际上都与这种地缘政治层面的认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作为一个霍布斯鲍姆所谓的“革命的时代”,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为欧洲的民族历史书写的多样化提供了外部背景。“当法国人把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在18世纪90年代的革命战争和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中输出时,在欧洲的其他地区,民族历史却成为它们保卫本国特性的一种重要工具,以抵制法国的普世激情和帝国扩张主义。民族历史现在成为一种针对启蒙普世主义的回应。”德国与法国之间在民族历史与认同方面的不同路径也随之形成,并影响到周边的其他区域。为此,要更全面地理解欧洲当代国家与认同,就有必要理解欧洲民族历史书写的阶段性过程。
在作者看来,当前的欧洲依然无法脱离民族历史的叙述。例如,在东欧和中欧的历史叙述中,“疆域冲突和民族历史中的重叠,时常成为民族叙述建构中的核心因素。那里的一座城市可能不仅拥有一些不同的名字,而且还可能属于不同的民族叙述。例如,奥地利的莱贝格(Lemberg)就是波兰的利沃夫(Lwów)和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更不用说这座城市的犹太名和亚美尼亚名了!”
到了当代,“在欧洲内部,民族(意义上)的他者仍然大量存在,甚至欧洲的‘他者’正以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形式加以建构。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和许多南斯拉夫历史学家的命运,应该是一种警告。它提示我们不要忽视一种本质化和激进化的民族历史所拥有的凶猛性。”我们当今看到的乌克兰东西部之间,在历史认知与民族叙述方面的冲突,实际上正是这种“阶段性”与“凶猛性”所导致的后果。
北美
从浪漫主义到进步主义
作为当下世界地缘力量的主要区块,北美的历史书写,是我们当下理解这一区域历史与现状的重要切口。总体而言,由于独特的区域历史与政治环境,北美的历史叙述是一个概念持续变动的过程,并在这些变动中形成了诸多叙述模式。
首先出现的是一种浪漫主义民族叙事,它由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导入,例如,加拿大的历史书写,就将本国看成是诸如英国占领整个法属加拿大的1760年征服战争,以及美国试图吞并英属加拿大的1812年战争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冲突的产物。而以乔治·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美国历史学家,则将美国民族的成长历程看成是一种逐步生长的有机过程,这些最初的种子植根于新英格兰的精神资源,最终成长为一棵巨大的橡树,并在18世纪70年代以美国独立的方式开花结果。
浪漫化叙事之后,紧随而来的则是进步主义的叙述框架,正如一部当时的美国作品所说,在19世纪下半叶,“地球上的老民族缓慢爬行,而共和国却如快车冲刺般迅速移动。合众国在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后,已位于各民族前列,并注定很快在这场竞争中超越其他民族”。随着认同构建的推进,地缘政治学成为北美学者思考本区域土地、空间相关问题的思想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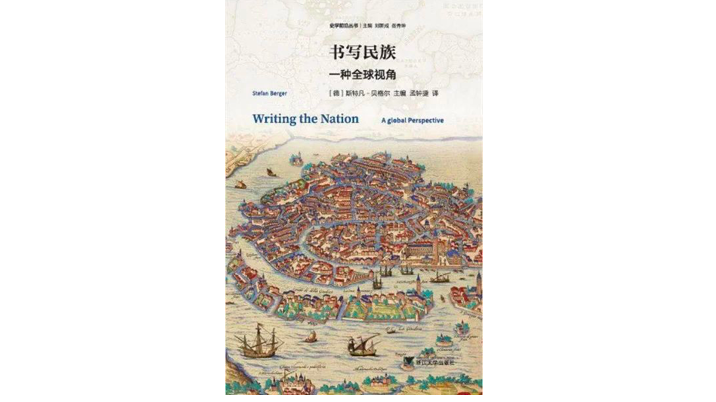
《书写民族:一种全球视角》,主编:(德)斯特凡·贝格尔,译者:孟钟捷,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以加拿大的历史叙述为例,“地理位置、气候与‘北方特性’,很快成为界定加拿大特点和认同的因素,而空间及其控制(‘我们勇敢而壮观的扩张’)则成为民族叙述中的主要话题。测绘河流与土地的探险者,在现今提供给公众的画面中占据着新的核心地位。……遍布大洲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被视作民族生活的首要黏合剂。”
而在美国,以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更是将边疆区域视为美国发展的关键与根源。在一战之后,随着欧洲作为世界中心力量的衰退,北美开始进入世界地缘互动当中,“新世界”话语开始成为塑造北美认同与定位的关键所在,并促成了关于加拿大的重新定位、美国例外论的增强,以及魁北克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的额外关注。到二战之时,北美更是从经济和政治层面取代了传统的欧洲,开始成为北美塑造内部边界与认同的关键契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在经历了全球化、安全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之后,更为强烈地支持其自身的原则与价值观,并将其贯穿在整个冷战过程当中。进入70年代,随着北美社会的内部分化,这一区域对于民族特征和总体认同的关注,逐步转向民族多样性、少数群体和亚群体等方面;到20世纪最后十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界研究开始成为北美民族书写的重要内容。
拉美等地
殖民遗产与自身传统
作为欧美之外的区域,巴西的民族历史书写,与其自身及外部“他者”有着密切关联。“巴西的独立绝非是一次与葡萄牙的断绝之举。事实上,它完全是由葡萄牙掌权王室阶层所为。其代表强调延续性、一种共享的历史存在及共同过去。”在这种所谓的“共享历史”背景下,巴西的历史又经历了细节方面的调适与再造。
而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民族历史叙述,同样反映了知识分子阶层和政治家在接受其社会的不同族群聚合模式时所面临的困境。在这三个国家中,“民族历史之构建都对国家驱动下的民族主义极为关键。它们试图培养民族归属感,但又时常忽视去提升公民理想。不同种族出身的人,在尚未平等地获得政治权力之前,被(国家)以爱国主义之名团结起来。这让拉丁美洲对20世纪的父权主义、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毫无招架之力。”

历史学家斯特凡·贝格尔
作为外围世界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印度、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民族历史叙述,同样呈现出自身的区域性特质,但始终面对着如何处理曾经的殖民帝国遗产与自身的主体性叙述的关系问题,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如何认知民族历史叙述的整体性、边缘性与跨界性特征。
在一个所谓“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代,文明的和谐共生显得如此宝贵。理解国家认知与民族历史书写之间的内在关联,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更为重要的图景。当然,在本书所论述的诸多区域之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等区域的民族历史叙述,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内容。书中所提供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关联性思考,对我们认清自身的民族特性具有重要启示。
作者:袁剑(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编辑:徐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