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徐悦东
库尔德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问题,宗教与民族纷争使得中东是当今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追其溯源,这些问题都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一战。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及其遗产的分割是今天中东乱局的主要根源之一。
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和《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 : 1516年至今》的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认为,一战变成世界大战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奥斯曼帝国的参战,而一战也彻底影响了现代中东的形成,理清楚奥斯曼帝国的衰亡是理解当下中东问题的关键。
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民族主义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个多民族帝国在面临内忧外患时,是否必然没有办法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依然认为穆斯林对宗教更加狂热?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中东问题,我们又有什么好办法?而中东问题所制造的难民,又跟今天欧洲极右翼民粹崛起的政治氛围息息相关。我们又能从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当中得到些什么经验教训呢?新京报文化频道记者就此采访了尤金·罗根,与大家聊了聊中东问题的现状与过去。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教授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战中东,1914-1920》等。
民族主义是如何导致奥斯曼帝国衰亡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青年土耳其党靠要求哈米德二世重启议会民主制和恢复宪政而名声大噪。但他们很快发现,恢复议会民主制并没能让奥斯曼帝国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和对其主权的尊重,反而使国家更加脆弱。最终,青年土耳其党为了防止国家分裂,不得不放弃先前的自由主义理想,变得更加专制。你怎么看待维系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完整和民主化之间的张力?
尤金·罗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青年土耳其党来说,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是非常糟糕的。因此,青年土耳其党想通过恢复法治、恢复议会民主制来制衡苏丹的权力。
但是,就在这场青年土耳其党发起的革命运动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邻国对其领土有了更大的野心,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希腊。青年土耳其党很快发现,议会解决不了这些有着侵略野心的邻国。若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奥斯曼帝国将会非常脆弱。因此,为了帝国领土的完整,青年土耳其党从主张宪政,走向专制。
当然,有人批评道,青年土耳其党这样做是一场历史错误。他们相信,假如奥斯曼帝国贯彻了议会民主制,继续深化改革,这样反而能将帝国中的不同族群联结起来,使奥斯曼帝国更加强大。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都在恢复宪法和议会民主制时大肆庆祝。因为恢复议会民主制,给了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个民族在政治上都有发声的机会。当青年土耳其党开始变得专制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分离倾向就开始加强了。所以,他们应该靠法治去建立一套让各民族联结得更加紧密的政治文化。而这个机会,却丢在青年土耳其党的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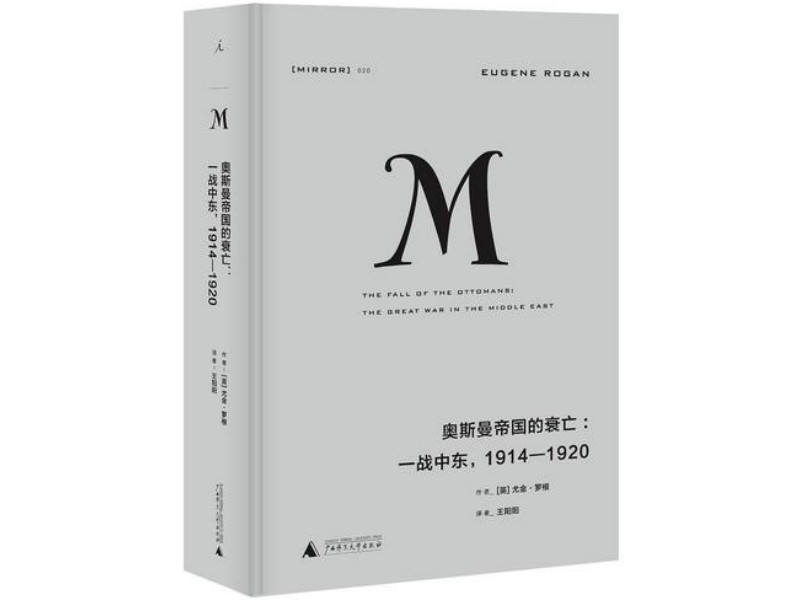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英)尤金·罗根 著,王阳阳 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新京报:民族主义让许多民族摆脱帝国的统治独立建国。但是,有人认为,中东各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成为了像英法等欧洲列强,肢解奥斯曼帝国大国角力的工具,使这些地区陷于持续的动荡,并产生了极深的民族创伤,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尤金·罗根:民族主义曾是19世纪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潮。直到今天,民族主义思潮依然非常强劲,奥斯曼帝国当然也受到这股思潮的影响。在一些地方,民族主义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意识形态;在另一些地方,民族主义则很狭隘、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和对多元文化充满着敌意。
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多民族帝国来说,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当然给了外国势力借煽动民族主义,搞民族独立,干预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机会。欧洲列强想肢解奥斯曼帝国,并让这些独立的小国家成为列强在那个地区的政治代理人。比如俄国支持的泛斯拉夫运动等,便有此目的。
因此,你的确可以说,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它没法在20世纪存续下来。
西方对穆斯林的想象来自于历史经验
新京报:为什么马克斯·冯·奥本海姆和德皇威廉二世,当时会相信奥斯曼帝国能发动一场全球圣战来挑战英法的殖民统治?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西方人依然相信穆斯林有可能同仇敌忾,做出狂热举动,延续着对伊斯兰圣战的想象?
尤金·罗根:当时,许多欧洲列强认为,宗教是一种能用来控制社会的力量。他们相信人们深受宗教的影响。
在当时的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眼里,伊斯兰教的狂热是动员人们的一种方式。当然,这是一个许多西方人会犯的经典错误,就连马克斯·冯·奥本海姆和德皇威廉二世都相信,奥斯曼帝国因此要被拉到德国的这一边来。他们期待全球穆斯林的领袖、被尊为哈里法的奥斯曼苏丹能发动圣战。而圣战能号召在英法的殖民地,如北非、西非和印度等地的穆斯林起来造反。但是,这只是一个误解,穆斯林跟其他人一样理智。

威廉二世
所以,让苏丹鼓动印度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起义对抗英国只是一种妄想。到二十世纪,有些西方国家依然持有这样的信念。美国就曾相信,他们能利用伊斯兰教来对抗苏联在阿富汗的侵略,所以美国支持塔利班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当然,在2001年,塔利班很讽刺地成为了美国的敌人。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想用宗教来对抗民族主义思想,或者想用宗教来操纵人们是不可取的。这是个错误的东方学观点,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给许多大国造成了麻烦。
新京报:你认为这种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是如何产生的呢?
尤金·罗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这个职业首先是要对此负责的。我在牛津大学研究伊斯兰教。在百年以前,有些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会被这样的观念所影响。但现在,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们已经不会再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误解也是来自于西方殖民者对一些殖民历史经验的反思。英国曾面对苏丹人民的反英起义,他们在马赫迪主义的影响下反抗英国殖民者。他们在一个宣称自己是救世主马赫迪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这使得苏丹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十几年。

苏丹马赫迪起义。
在1871年,法国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反殖民起义。在东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周边,成千上万起义军被苏菲派所领导,并宣布起义为圣战。这些在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经验,使得西方人对全球穆斯林群体有一个宗教狂热的想象,认为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差不多,然而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但很有意思的是,德国无法利用他们对穆斯林圣战的想象。德国所期待的一场全球穆斯林大起义的场面并没有到来。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也曾害怕与奥斯曼帝国打仗。随着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越来越深入,他们也越来越害怕奥斯曼帝国能号召在其殖民地上的穆斯林发动圣战。因此,在某种角度上,这种想法也是有作用的,但不是如德国人想象的那般起作用。
殖民者在划定边界时遗留下了今天的许多问题
新京报:你在书里认为,如果在战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能够利用凯末尔发起的运动抵制《色佛尔条约》,现在立于土耳其版图之上的也许还是奥斯曼帝国,接受苛刻的和约是奥斯曼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为什么那时奥斯曼帝国会相信,除完全屈从战胜国要求之外别无选择?
尤金·罗根: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完全失败的。从1911年到1918年,奥斯曼帝国输了四场战争,它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在先前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也失败了,还输了一场对意大利的战争。
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士兵能够再次战斗了。对此,凯末尔并不赞同。凯末尔认为,他能激发奥斯曼士兵的民族精神来抵制这个分裂帝国的条约。奥斯曼帝国政府也知道,这些条款将会把奥斯曼帝国分割成许多小国家,就如同奥匈帝国解体之后一样。但他们想,若他们接受了欧洲列强的要求,以后还会有机会重新获得以前的土地。
而且,假如奥斯曼帝国不满足条约里的任一款项,协约国就要武力夺取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而奥斯曼帝国觉得自己无力战斗,假如他们不签这个条约,他们会输得更惨。所以,他们宁愿接受这种糟糕的和平。
但凯末尔觉得,若这些土地都分割出去了,它们再也回不来了。选择接受条约的苏丹政府和反对接受条约的凯末尔,都互相指责对方出卖了土耳其民族,奥斯曼帝国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中衰亡的。最终,凯末尔在赢下与希腊的战争后,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新京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中东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国境边界的划定就极具争议性,也导致了现代中东的许多冲突。你认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尤金·罗根:一百年多年前,中东地区只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后来,经过不同殖民政府的统治,中东地区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殖民者在划定边界时,并没有跟当地人民商量,这给今天的中东各国遗留下了许多冲突。
其中,有些民族还没有实现独立,比如库尔德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库尔德人并没有主动寻求独立,他们被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整合得很好。但是,在《色佛尔条约》里,西方列强打算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这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喜欢库尔德人,而是他们想在俄国和他们的殖民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
但是,这个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承诺,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之后就被打破了。库尔德人很快发现,他们被分散在了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的国境内。这些流散的库尔德人开始了寻求身份认同和民族自决的斗争。直到今天,库尔德问题都没有被解决。

分散于多国的库尔德人。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他们的土地被用来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贝尔福宣言》是他们苦难的来源。英国殖民者也不是全为了犹太人而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英国人是希望在巴勒斯坦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和同盟。他们不只是想短期占领巴勒斯坦,而是将它视为大英帝国利益的一部分。英国人还认为,他们的统治会持续很久。
当然,巴勒斯坦的土著站在了英国政府的对立面。巴勒斯坦的原住民主要是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之后,他们很快与原住民的关系变得紧张。直到今天,巴勒斯坦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伊拉克脱胎于英国的托管地,其民族和宗教构成十分复杂。这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在今天,若伊拉克贯彻民主制的话,那么占大多数的什叶派将会掌权,而逊尼派就会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的自治倾向越来越浓。这使得伊拉克这个国家很难被很好地整合和管理,总有着分崩离析的倾向。如今,伊拉克还没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整个国家的氛围依然紧张。
而自从叙利亚从法国殖民下独立以来,经历了两次内战。历史表明,叙利亚政府若太过依赖某个宗教派别来统治的话,都会难有良好的执政表现。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内战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继续撕裂着叙利亚。
这些问题都该怎么解决呢?假如一战后的战胜国认为,中东地区是一个对于全球局势来说非常特殊的区域,他们要跟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一起商议,一起寻找一个合适的政治解决方案,建立符合当地居民愿望的国家,那么欧洲列强是可以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中东的。
可惜,法国和英国只想着他们自己的帝国秩序。那时他们的这种行为似乎是“自然”的,当时白人可以殖民亚洲人生活的地方。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这样做了。20世纪的历史主题围绕着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展开,殖民帝国的寿命其实非常短。假如英国和法国知道他们的殖民帝国在20世纪持续的时间不长的话,他们或许会建立出更好的中东秩序。而对于现在中东的冲突,国际组织的共同合作是解决之道,让某个大国独自去解决中东问题是不妥的。
反击埃尔多安的时候到了
新京报:最近土耳其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在重新举行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以明显优势胜出,这给埃尔多安和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带来沉重的打击。有人说这表达了选民对埃尔多安的专制路线的不满,也有人说这是选民对埃尔多安的经济答卷的不满。你是怎么认为的呢?你怎么看待土耳其今天和明天?
尤金·罗根:土耳其如今正在转型当中。其实,在埃尔多安早年的政治生涯里,即他担任土耳其总理期间,埃尔多安为土耳其做了许多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比如经济增长等。
在土耳其,伊斯兰教在世俗化中已经边缘化了。但是,其实许多土耳其民众是反对世俗化的,世俗主义者和其反对者存在着很大矛盾。正义与发展党能够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其实也缓和了这个矛盾。许多西方人认为,这证明了土耳其其实原本可以建立某种包含法治和民主选举的伊斯兰民主政体。
在埃尔多安早年的政治生涯期间,土耳其在经济上非常繁荣。经济繁荣增加了大家对埃尔多安的支持。但是,埃尔多安让伊斯兰文化在土耳其占主导地位所采取的方式,让许多世俗化了的土耳其人感到不满。这些世俗化了的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在伊斯米尔、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大城市里。其中,伊斯坦布尔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的开始之处。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伊斯坦布尔市长。
于是,知识分子、世俗化了的土耳其人、自由主义者,开始表达对埃尔多安统治的不满。比如,在2013年的伊斯坦布尔,他们抗议为兴建一座购物中心而砍伐戈兹公园里的树木。他们还试图指控埃尔多安贪污腐败。此外,埃尔多安显示出长期执政的打算,并有为他的政治盟友和家庭成员输送利益的嫌疑,这都是民众反对埃尔多安的理由。
2016年的军事政变是埃尔多安执政的转折点,埃尔多安开始展露出专制的势头。他开始针对地清洗居兰运动的参与者。现在,埃尔多安似乎已经悬置了法治,变得非常专制,他抓捕记者、关闭大学,让法庭变成他让异见者闭嘴的地方。
在乡村,埃尔多安有着极高的支持率。但是,在议会上,由于反对他的党派比较多,暂时还没有一个党派能打败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市长选举中,反对埃尔多安的共和人民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使埃尔多安不接受第一次选举的结果,再选了一次,结果他发现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反而输了更多。

埃尔多安
我认为,这次市长选举鼓励了反对埃尔多安的政党,还有那些反对埃尔多安的世俗主义者。我不觉得正义与发展党因此会消失不见,他们依旧会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土耳其人毕竟能用民主选举换掉他们的政府,这能够解决许多上一任政府执政留下来的问题,包括他们该如何选择他们的政治价值观等。我不觉得土耳其人会让一个党执政太久,我觉得这也应该是共和人民党或者其他的反对党,挑战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的时候了。
“阿拉伯之春”后的阿拉伯世界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阿拉伯之春”是一场要求问责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的运动,你觉得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转型到问责政府的难处在哪里?你怎么看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未来?
尤金·罗根:“阿拉伯之春”展现了阿拉伯人民对他们政府的不满。他们反对他们政府的恐怖统治。他们在城市中心的广场聚集起来,互相给对方勇气来反抗政府。正如我喜欢的一句话,“人们不该惧怕其政府,而政府应该惧怕人民”。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很难被控制,是因为这是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政府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抓起来。这场运动把长期执政的独裁者们赶下了台。但是,这场运动并没有最终形成一个合适的政治改革方案。假如你要立宪,你需要大家都组织起来,让不同的观点互相竞争,征取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是,在独裁者下台之后,这场运动变成一盘散沙。填充权力真空的不是有着政治理想的政治家,而是军人。
唯一的例外是突尼斯。突尼斯的示威最终能形成对话,他们用了两年起草宪法,容纳了许多政治光谱的政党,并最终成功立宪。他们的行动也受到突尼斯人民的支持。

“阿拉伯之春”
当宪法生效之后,他们根据宪法选举出议会成员和总统,这是“阿拉伯之春”后,唯一一个能成功转型的阿拉伯国家。突尼斯的例子给了阿拉伯人希望,也许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建立问责政府,政府能够害怕人民,并能依照人民的意愿做出改变。
今年,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人们回到街头要求改变,改变也正在发生。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已经吸取了阿拉伯之春的教训。在革命之后,要填补一个独裁者的权力真空,他们就要组织有真正意义的政治组织和单位。假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苏丹都成功了,这就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开启问责政府的新篇章。这是他们应得的,因为他们的人民都很有勇气。这也是我对阿拉伯人民的希望。
欧洲正在经历着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
新京报:你对欧洲的难民问题和极右翼政党崛起有什么看法?
尤金·罗根:叙利亚内战给欧洲带来了许多难民,他们想离开暴力的环境。还有一些劳工移民想进入欧洲,这增加了欧洲难民和移民的数量。关于如何安置和对待有关这些难民和移民,欧盟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法律。但是,欧盟表现出在遵守法律时,又想改变法律,尤其是极右翼政党。极右翼政党操纵着人们的恐惧,这让他们在欧盟议会选举时,形成了一股势力。
我觉得欧洲正在历经着民粹主义盛行的时代,政客们能利用人们的恐惧获得选票。他们把移民和难民当成获取其政治权力的工具。但真正的问题是,欧洲各国得依靠移民,来维持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这些移民和难民也是他们帝国时代的遗产。
如何去对待那些因经济原因或战争原因,来到欧洲的难民就变成了欧洲的责任。这些难民需要人道主义关怀,还有救助。因此,我们应该要一起解决这些冲突地区的问题,重建他们的城市。我希望通过国际间的协助,中东最终能达成经济上的繁荣,这样难民们自然也能回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反对这些极右翼政客和他们的种族主义政治。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 何安安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