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曹南屏
1904年的甲辰科会试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那一年,湖南人陈继训(1878-1962)高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之一。
回首他的科举生涯,着实堪称成功:26岁就成为进士,授户部主事。1907年,他成为驻俄使馆的参赞,不久之后,转而担任度支部军饷司司长。正当“官秩日显”之际,他的政治生命却在1911年戛然而止,此后他解职归里,“以诗文自娱”,不仕民国。民国年间,在陈继训给他人撰写的墓表、传记等文字中,他常常刻意标明自己在前朝的为官履历,以此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认同。像陈继训这样的例子,在癸卯科、甲辰科的进士中还有不少。
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1905年,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在此期间,共举行了两次会试,即癸卯科与甲辰恩科,共计产生了588名进士。这两科的乡、会试将“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四书义、五经义”等分别列为三场考试的内容,无论文体还是知识,对于长久浸淫于旧的科举体系的读书人群体而言,几乎都是全新的。
在成为进士以后,癸、甲进士中的许多人进入进士馆肄业,进而又被遣派出洋游学。这些经历都使得癸、甲进士或多或少沾染了些许“新学”的色彩,因而不同于他们的进士前辈。
由于很快科举废、学堂兴,经科举选拔而来的他们又都成为“过渡”色彩明显的一代。癸、甲进士群体的特殊际遇还在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经历了辛亥鼎革,因而才会出现不仕民国或再仕民国的不同选择。进入民国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化态度上也有着引人瞩目的表现。
韩策的新著《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就将目光聚焦于1901年科举改制后所产生的最后两科进士,既展现了这两科进士如何被改制后“新”的科举制度“生产”出来,也追述了癸卯科、甲辰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废除乃至辛亥鼎革以后的命运浮沉与文化怀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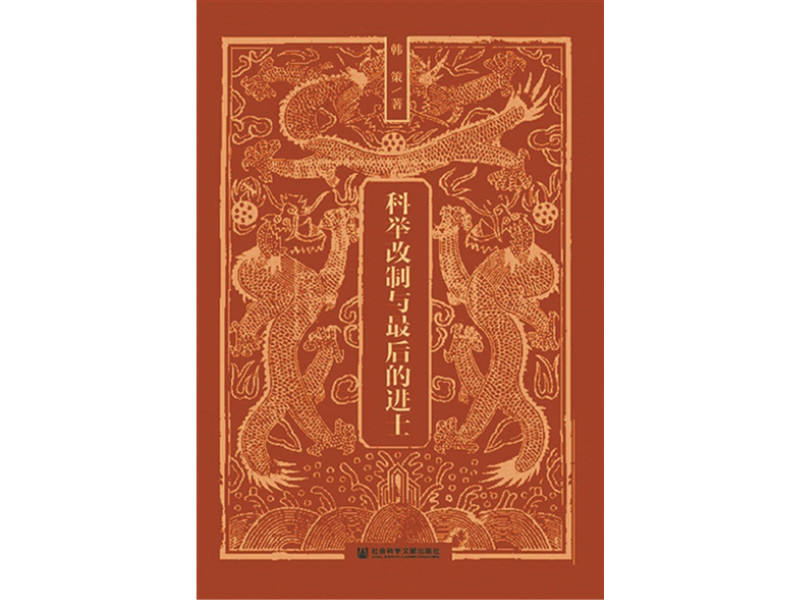
《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韩策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版。
科举改制的高层博弈
陈宝琛在甲午后感知到的朝堂之上的“声无准”和“事可知”(《感春》)似乎在清末的不同场合一再应验。《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令人信服地为读者展现:无论是改科举,还是到后来的废科举、兴学堂,都是清末朝堂之上不同官员势力的博弈结果。
1898年,康、梁一派推动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而最终提出改制方案的却是张之洞和陈宝箴。戊戌维新失败后,科举改制之议很快消歇。至1901年旧事重提,提出方案的是两位东南督抚——刘坤一和张之洞。若将两度科举改制方案加以对比,可以发现提出方案的核心人物都是张之洞。然而,最后真正颁行的科举新章,却是由政务处、礼部所奏定。不同官场势力的博弈,带来的结果是折中与妥协。如,张之洞为求“除弊”而提出的“分场去取”方案被否决,而张之洞新提出的、后来被证明带来很多“新弊”的“废除誊录”的建议却被保留。这一折中与妥协的产物,使清末科举改制的效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进而也贬损了科举的声价。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清末朝堂之上并没有展现出政见的一致性,不同官员势力之间政见的多歧性与差异性不时显现。1900年的乡试展期之争,相争的双方是东南督抚势力和在西安随侍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行在大臣。1901年科举改制新章的出台,也透露出改制方案的提出者张之洞与具体章程的制定者政务处、礼部之间的微妙关系。以瞿鸿禨、荣庆等为代表的部分西安行在大臣则提出了开进士馆的方案,将科举选拔的“已成之才”投入名义上隶属于京师大学堂的进士馆肄业,借此也表露出提倡者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意思。不同的官场势力在持续地表达自己对“学务”的见解,也都试图影响到清廷的决策。
韩策在书中指出,“趋新督抚在改、废科举中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于是乎,1901年初,袁世凯还在提科举改制不废八股、增加实科的主张;到了1903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衔上奏,提议科举中额分三科递减、直至减尽的方案,即约用十年时间将科举停废;而仅仅一年多以后(1905年),袁世凯、端方等人又联络六大督抚,干脆直接联衔奏请停废了科举。清末中国从科举改制到停废科举,速度越来越快、方案也越来越激进。也由此,不管是改制后的科举考试,还是此后兴学堂、派游学等教育新政,不仅效果都难称理想,对废除科举后的善后之策也缺乏较为周致的考量与安排。
最后的进士群体的出处进退
癸、甲进士群体恰逢清末新政这一大变动的时代,在清廷改革举措频出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刚中进士之后,他们就接连遭逢开进士馆、废科举、派游学、改官制等多项与其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变动。科举虽经改制,考试内容一新,但他们多半还是旧有科举体系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其观念还多有科举时代的印记。“旧人”身处“新制”,难免生出许多窒碍与冲突。例言之,甲辰年(1904年)进士馆宣告开张、新进士们入馆肄业时,学堂与科举之间的紧张很快显现——受科举时代“师生”关系的影响,进士群体并不承认以日本教习和归国留日学生为主的教员群体是他们的“师”。
师生关系的重新调适与持续紧张,既体现出由科举所塑造的传统的惯性,也影响到了开进士馆的实际效果。“旧人”与“新制”之间的不协,也使得清廷在进士馆开学不久就颁布了《更定进士馆章程》,以资调和与补救。此后,在进士馆内肄习的癸、甲进士开始陆续有人出洋游学,其留洋的目的地则多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
1905年9月2日,在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刚刚举办两科,进士馆刚刚开学一年多后,清廷批准了袁世凯、端方等人积极促成的停废科举奏请。科举制度遽然停止,进士馆没有了新的进士来源,这一机构也很快面临存废去留的问题。由此带来的主要结果有二:一是进士馆在1906年将以甲辰科进士为主的新一班学员整体遣派日本游学;二是进士馆于1907年改设为京师法政学堂。进士馆已经难以为继,也只好成为“过渡”的机构。
在清末中国,新与旧成了一种常见的人群分野,癸、甲进士群体依违于新、旧之间,其个人表现亦是新、旧互现。一方面,从教育经历与知识储备而言,癸、甲进士群体相比其进士前辈显然较“新”。因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新政中广泛投身于各地兴学堂的热潮,推动了新式学制的落实与发展;他们中还有不少人成了清末新政时期各省咨议局的议员乃至咨议局的议长、副议长,投身于清末的立宪运动,甚至活跃于辛亥革命。也因此,癸、甲进士中“再仕民国”者大有人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则是这批癸、甲进士中的不少人在辛亥鼎革后对于旧朝的态度,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辛亥以后,部分癸、甲进士参与续纂了《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德宗圣训》等旧朝文献,也有部分人选择成为“遗民”,不再出仕民国。另有不少人在进入民国以后,或者任教于高等学府,或者组织诗词社定期集会,成为维持中国传统文教的一支重要力量。
废科举以后,近代中国持续剧变,改朝换代,“日月换新天”。无论从旧时代走来的读书人如何维持文教,也难挡旧学沦亡的运命。不仅自信“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天下士”日益消散,“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也不再是一个具有社会共识的追求,因而读书人的群体特征与自我认同也面临新的蜕变。
“读书不为做官”既成为新时代教育目标的全新宣言,也标志着仕学传统的彻底终结。其后,商人、军人、党派等不同的新兴势力跃上历史舞台,自我调侃“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人们留在了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无论其个人际遇或隐或显,最后的进士群体,堪称是亲历并见证了“唯有读书高”在中国的最后岁月。
作者丨曹南屏(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辑丨何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