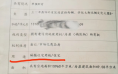撰文 | 张进
卡夫卡曾在1919年给其父亲赫尔曼写过一封信,《致父亲》。这封信后来成为研究者了解卡夫卡内心世界的重要切口。在信中,卡夫卡坦诚地细叙了父亲绝对强权式教育给自己的生活与性格造成的负面影响。
赫尔曼教育卡夫卡用的是“力量、咆哮和暴怒”,对他的几乎所有喜欢的事情给出否定性回复。对于本就极度敏感、孱弱的卡夫卡来说,父亲的回复像一次次判决,让卡夫卡失去了本就脆弱的生活的信心。而《判决》正是他与父亲紧张关系的文学化表述。
此外,父亲代表的家庭领域的极权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在卡夫卡之后的《城堡》等作品中扩展为公共领域的极权主义。因此,理解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是理解卡夫卡作品内涵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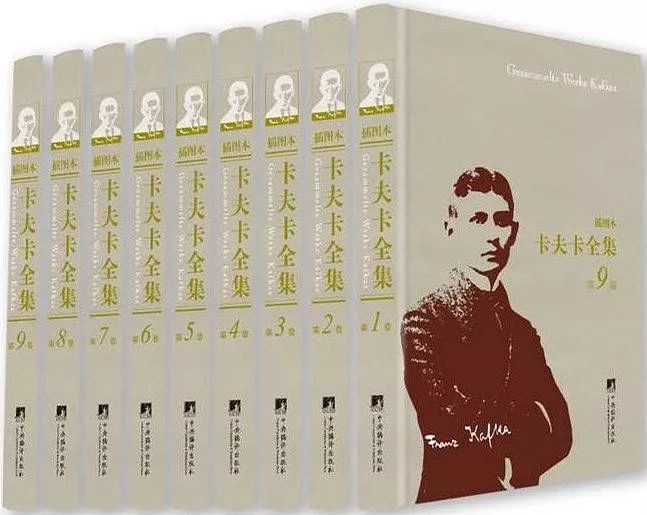
《卡夫卡全集》,弗兰茨·卡夫卡 著,叶廷芳 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读《判决》的时候,偶尔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与之相关的阐述是,“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一句话足以说明“君”和“父”的绝对权威。《判决》主要讲的,正是格奥尔格面对父亲威权时的无力,而当父亲判他跳河自尽时,格奥尔格毫无反抗地照做了。
《判决》是卡夫卡在1912年9月22至23日夜间,“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一气呵成的”,并献给了刚相识不久的女友费丽丝。
《判决》具有卡夫卡的自传性质。卡夫卡与父亲赫尔曼的关系极为紧张,乃至成为“敌人”。赫尔曼少年贫穷,靠自我拼搏成为一家妇女时装礼品店的老板。他“强壮,健康,胃口好,有支配力,能说会道,自满自足”,而儿子卡夫卡几乎正好是他的对立面。卡夫卡孱弱、羞涩、自卑,在赫尔曼面前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赫尔曼指责卡夫卡没有家庭观念,自私自利,对自己漠不关心;他教育卡夫卡用的是“力量、咆哮和暴怒”,而且对这种方式带来的影响毫无知觉。这一切对童年时期卡夫卡的性格产生了无法修补的负面影响。
童年时期,卡夫卡把任何一件使自己高兴的小事告诉父亲,得到的只是“一声嘲讽的叹息、一个摇头的表示”。来自父亲的无数次、无缘由的否定性评价,使卡夫卡成为有明显自我否定倾向的人,以至说出“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这样的话。

卡夫卡
在写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将父亲比作“暴君”和“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他说:“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和耻辱竟会毫无感觉……”面对父亲的指责和“精神上的统治权威”,卡夫卡在父亲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负罪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卡夫卡通过写作进行着“内心的逃逸”和独立的尝试,试图结婚是逃逸和独立的一种方式,且在卡夫卡看来是“最有希望的尝试”,但因为父亲的教育产生的“副产品”,也就是卡夫卡的“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让卡夫卡失去了结婚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判决》是卡夫卡与父亲关系,或者说是卡夫卡“父亲情结”的文学化表述。
年轻商人格奥尔格给俄国的朋友写完信,去看望父亲。“他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来过了”,晚上在家也是“各干各的”。以此看来,父子之间的疏离是由来已久的事。最近三年,格奥尔格在事业上取得了极速发展,因为之前父亲“在经营上独断独行,阻碍了他真正按自己的主意行事”,但两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不再事必躬亲”,格奥尔格因此似乎摆脱了父亲的束缚。但真的如此吗?
格奥尔格见到父亲的第一个念头是:“我的父亲仍然是一个魁伟的人。”对父亲体格的描述,立即展现出格奥尔格对父亲的畏惧。接下来,格奥尔格谈起把准备结婚的事告诉俄国朋友的打算。这个“俄国朋友”具有明显的虚幻性质,卡夫卡在日记中说:“那位朋友是父与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性。”也就是说,这位朋友是格奥尔格和其父亲共同的投影。最终,父亲成为这位俄国朋友的“代言人”,两人共同对抗格奥尔格。
说话期间,当格奥尔格替父亲脱衣服时,看到父亲内衣脏了,他“责怪自己对父亲照顾不够”。这则显示出格奥尔格除了畏惧父亲外,也关心父亲。但接下来,当格奥尔格把父亲抱到床上,替父亲盖好被子时,他的“弑父”心理也展现出来,因为在德语中,“盖”也有“埋葬”的意思。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就像卡夫卡一样,格奥尔格对父亲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即使这些反抗最终没起到真正的作用。
父亲对格奥尔格“埋葬”自己感到愤怒,“用力将被子掀开”,像赫尔曼指责卡夫卡那样,指责格奥尔格是个“没有人性的人”,并判他去投河淹死。正如卡夫卡一样,格奥尔格因负罪心理,毫无反抗地投河自尽了。临死前他说:“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卡夫卡也同样爱着父亲,但这爱与恨、惧怕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父子关系。父亲代表的家庭领域的极权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在卡夫卡之后的《城堡》等作品中扩展为公共领域的极权主义。因此,理解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是理解卡夫卡作品内涵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
作者:张进
编辑:徐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