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皮、蘑菇、东珠为什么得以成为备受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穿戴毛皮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满族式生活的理想型。一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北地区依然以穿“貂儿”(东北地区对于皮草的统称)为时尚。而追踪其缘由,显然与清以来的宫廷贵族风尚密不可分。以乾隆皇帝为例,这位以“圣主”自居的君王,用满洲最珍贵的物产丰富着自己:貂皮和水獭皮袍子、口蘑,以及镶嵌着东珠的帽子。

镶嵌有东珠的帽顶。
我们是否可以让清帝国的边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又应当如何理解清帝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地理?乌梁海人以捕猎毛皮动物为主,满洲地区是人参和珍珠的产地,蒙古人需要蘑菇、“扫雪”(学名叫石貂,也叫白鼬、岩貂)和鱼。清帝国的档案不仅仅关注人和土地,同样注意到了物品。特别是在农业核心区之外,高端商品受到密切关注。
穿在身上的毛皮、盘中的蘑菇,以及冬帽上的珠宝,这些物品的珍贵性,首先源于它们与清朝宫廷的联系。清廷对此类物品的生产活动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控制,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除物产本身的价值之外,这些物产还代表着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清朝宫廷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进而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帝国之裘》一书中,作者谢健把早期现代想象成一个自然与文化截然区分的时代;科学、治国或理性化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文明。在谢健看来,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是以采菇人、毛皮商、扫荡参田的兵丁的面目出现的。
谢健指出,“现代人到处抽干沼泽、砍倒树林、开垦土地。城市拔地而起,荒野后退,人类首次幻想一个遥远而未被打扰的大自然的存在。然而自然的元素比以往更多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脖子上围着貂皮;街上有马和骆驼;还有鲟鱼、鹿肉、蘑菇和珍珠。这个时代不仅仅见证了自然被浪漫化,也目睹了其商业化:野物手手相传,从帝国边疆运输到帝国中心。居于统治地位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这是个用貂皮镶边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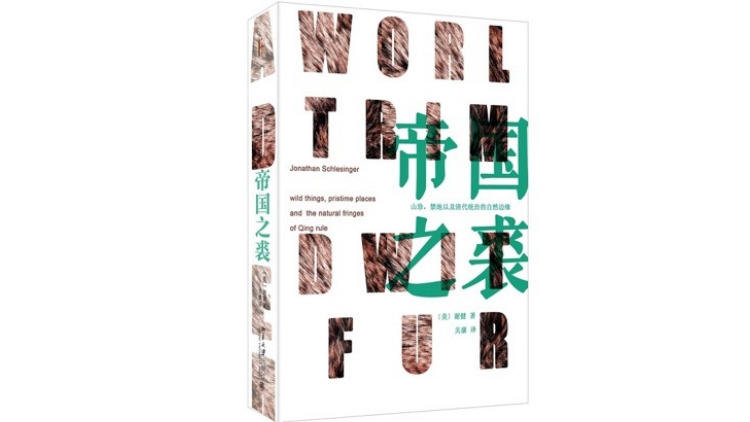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作者:(美)谢健,译者:关康,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撰文︱(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摘编︱何安安
18 世纪毛皮开始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
“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于斯焉。”
1780年来到中国的朝鲜饱学之士兼讽刺作家朴趾源(1737年-1805年)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人身穿文明人的衣服:朝鲜人和伶人。其他的中国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身穿毛皮。他参加从朝鲜王京到北京向清朝的乾隆帝(1736年-1795年在位)进贡的使团。皇帝本人的衣着似乎就是野蛮人统治的一部分:他不仅自己穿毛皮,还下令其他朝臣一体照办。实际上,当使团结束任务时,乾隆帝将代表大清慷慨好施的礼物貂皮赏给了朴趾源。作为满洲人就得穿毛皮,而到18世纪后期,不仅满洲精英,就连汉人精英也不能免俗。
朴趾源知道,世道已今非昔比:早在清朝入关之前,满洲人和汉人截然有别。他们外表迥异:汉人蓄发;满洲人留辫子。汉人妇女缠足;满洲妇女天足。他们的服饰也不一样:满洲精英穿毛皮;汉人穿丝绸。满洲人穿马靴和有马蹄袖的马褂;汉人精英对这种与骑马有关的时尚不感兴 趣。到一百多年后的 18 世纪,两个族群的外在区别开始消失:从外表已经不容易区分满洲人和汉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物质文明的变迁说明满洲人已逐渐融入了北京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对于汉人而言,毛皮不再是满洲意识的标记,而是辽阔帝国的象征。
其实,剧变产生于 18 世纪:像毛皮这种边疆地区的物产终于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到 1800 年,外地游客对北京这座城市能够提供的商品感到惊奇:蒙古地区的扫雪皮(marten,一种白鼬的皮)和银鼠皮马褂、口蘑(steppe mushrooms)、满洲地区的东珠。街上还有贩卖野味的商人,男男女女穿着有马蹄袖的衣服,有时候还能看到活的大象、虎和熊。

美丽的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在明代(1368年-1644年)的汉语中还没有“扫雪”“银鼠”这些词。而到了清朝,这个空白就被鉴赏家、当铺掌柜和朝廷填补上了:对市场的真正了解不光需要新词汇,还得有关于这些商品的意义和产地的故事。假毛皮、秧参和冒牌口蘑充斥街头巷尾,可是消费者想买到真货——来自原始边疆的未被污染的纯天然产品。
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被视为是时代变迁的标志
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技术和设计,当然还有时尚和物质都是时代的象征。不仅物件的外在标示着年代,就连它们的种类和质量也有同样的功能。然而回顾过去,我们也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便排除了最新的技术和时尚,即便缺乏物质财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算是返璞归真。实际上,人类的物质遗产既不是简单的也并非单向的,这一点与我们的书面遗产相比毫不逊色。差异和不均才是常态。
然而从年代的角度看,大体上从16世纪开始,我们生活中物品的数量才有了增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商业和生产核心区域。从15世纪末开始,明朝已臻繁盛。彼时消费激增、市场成长、土地紧张,工农业扩展到新的边疆地区。当时中国人生产、消费的物品和同时期西欧人一样多,甚至尤有过之。而和之前的汉族王朝相比,晚明时期的中国人在消费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也拥有更多的财富。奢侈品买家能够从整个明帝国和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产品:蒙古草原的羊毛、毡子,西藏的麝香,台湾的鹿皮,日本的白银和朝鲜的人参。1571年之后,明朝与统治今天内蒙古的俺答汗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明与亚洲内陆的贸易节奏因而加快。同一年,随着西班牙殖民马尼拉,这个贸易链还囊括了美洲的产品:墨西哥的白银和波托西(Potosi)银币成为现金和税收的新基础;吸烟如同病毒一般泛滥;农夫开始种植马铃薯、玉米和红辣椒。全球化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消费增长的同时,原先代表个人身份的标志越来越不重要了。想仅仅是对他或她看上一眼就判断出其地位已经不容易了:“近来……使女穿着丝绸,歌姬不以丝锦绣服为贵。”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只得求助于鉴赏家。像《长物志》这种教导人们如何过文雅生活的书成为畅销读物。它们告诉读者,一位绅士应当购买或者收藏什么东西;还证明一个人消费什么东西可以使他看起来更文雅。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揭示的那样,仅仅购买明朝的花瓶尚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高等身份,还要把它正确地摆放在来自日本的桌子上,还得插数量适宜的花(仅仅多出两枝,就会使房间看起来像酒馆一样俗气)。
1644 年,明朝崩溃,满洲人列队开进北京城,他们看上去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和关内的人一点都不像;他们的穿着像野蛮人(汉语所谓胡人)而非汉人精英。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他们说的、写的是另一种语言。男人剃光前额,把脑后的头发留长扎成辫子。妇女保留天足、拒绝缠足。满洲贵族骑马,赞美武士文化,穿毛皮、戴东珠。基于以上原因,来到清朝宫廷的欧洲观察者形容满洲人是容易接近且率真之人:“他们喜欢接见陌生人;不像汉人那样冷酷和酸腐,所以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显得更有人情味。”满洲人的出现在明朝遗民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有些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645年,清朝占领苏州之后,《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绝食而死。
坐拥富足财产的皇帝扮演着淳朴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皇帝们是生活在不断增长的财富中的消费者,他们挥金如土,住在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中心,身边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建筑、丝绸、天文仪器、钟表和用满、汉、藏、蒙古文写成的书籍。坐拥富足的财产,他们还扮演淳朴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努尔哈赤端坐在用鹿角制成、饰以虎皮和鹿皮的宝座上,被漆器和丝绸以及其他象征财富的物品围绕着。皇帝们也在菜单中专门给野味留了位置。朝廷消费着从帝国各个地区送来的美味,皇帝们把满洲野味和汉地城市化的、复杂的烹饪,蒙古酒,中亚的瓜果糅合在一起。不过,野味是最好的。占领北京之前,宫廷厨师就把虎、熊、狍、麋、山羊、野 猪、野鸭和野鸡作为食材;食谱记载了宫廷服务人员如何清洗肉类,并切成大块,然后用海盐、酱油、大葱、姜、四川辣椒和八角炖煮。研究宫廷饮食和满洲食品的学者吴正格解释道:“这种食法虽然原始一些,但也表现了满族人粗犷、豪爽和实惠的食风。”

清朝木兰秋狝。
它也反映出满洲人的健康观。康熙帝在这方面是最坚定的:“北方人强悍,他们不必模仿那些体质脆弱的南方人的饮食嗜好。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有不同的口味和肠胃。”他以满洲长者的身份推荐“鲜牛奶、醃泡过的鹿舌和鹿尾巴、苹果干和干酪饼”。
每年,皇帝都会把自己猎获的鹿肉分给皇后、妃嫔和宠臣。只要皇帝杀掉一头鹿,内务府就把它切成六份:尾、胸肉(满:kersen)、臀肉(满:kargama)、排骨、肉条、肉块(满:farsi)。尽管满汉大臣都会得此赏赐,但任何人都不会忽视这种食物的族群文化背景:汉语完全无法翻译“胸肉”“臀肉”和“肉条”这些概念,汉文档案只能采用音译:克尔森、喀尔哈玛、法尔什。似乎野味仅仅属于满洲人。在皇家菜单中,野禽肉也享有类似的地位;它们同样体现着“满洲之道”。每只被猎杀的野鸡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朝廷记录了是谁、如何弋获的,包括有没有使用猎鹰。内务府通常会把鹿肉和野鸡肉绑在一起制成礼物。宫中妇女会定期收到上述每种肉类,包括一份由皇帝赏赐的2斤鹿肉、野鸡肉和鱼肉组成的年例。避暑山庄同样拥有一个豢养着野鸡和鹿的动物园可供消遣。
某些野生植物和真菌也具有同样的魅力。因此宫廷厨师总是把口蘑和野味一起烹调(汉语的“口蘑”指来自 [长城] 关口外的蘑菇):它会增加菜肴的野性滋味。乾隆帝在巡幸满洲故乡盛京时尽情享受鹿筋烧口蘑和口蘑盐煎肉。其子嘉庆帝(1796年-1820年在位)也在狩猎的时候吃口蘑。实际上,口蘑在宫廷从未过时。1911年,在辛亥革命前夕,皇位仅剩一个月的4岁皇帝溥仪吃了4次口蘑。当然,御膳不可能是粗制滥造的;尽管其精神是粗犷的,但制作过程还需要厨师的本事和手艺。
毛皮时尚也印证了这种意识的存在。入关前,满洲统治者下令给从明廷缴获的丝制龙袍镶上貂皮——从明朝人的角度看这是野蛮人的做法;入关后,他们继续穿明式龙袍,但在领子、袖口缝上毛皮,还穿着貂皮裙。清初宫廷通过正式的舞蹈赞美毛皮的满洲特色,一群一群的侍从穿戴上豹皮袍子和貂皮帽子,高唱开国之歌。史家谈迁(1594年-1658年)目睹了这一场景,并在日记里详细描述了这种“满洲舞”:“凡二三十人北面立。衣文豹者持彩箕一……衣貂锦朱顶金带者四人,结队而舞,低昂进退有度。”
冬天,皇帝们戴黑貂皮帽子,到了每年阴历的最后两个月,再换黑狐皮帽子。帽子顶部是镶嵌着东珠的三重帽顶。此时还要配上冬装马褂:皇帝在初冬时节穿黑貂皮,新年前两个月穿黑狐皮。在冬季的其他月份,皇帝穿镶着海獭皮的龙袍。夏季,这些毛皮衣服就被收纳入库,但东珠仍然在全套衣装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包括帽子上的装饰品和由108粒珍珠串成的美丽念珠。亲王的穿着也有类似的元素:貂皮、海獭皮和东珠。

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貂皮龙袍。
清廷的这些物产象征着帝国的等级制度。虽然很多人穿毛皮,但是颜色、种类、裁剪方式体现着一个人在帝国中的位置。在努尔哈赤的时代,最高级的精英穿戴东珠、黑貂皮、猞猁狲皮,地位稍低的贵族穿松鼠皮和鼬鼠皮。在高级贵族中还存在差异:顶级贵族穿嵌毛貂皮袍、 黑貂皮袍、“汉人”式貉皮端罩(满:nikan elbihe dahū)、猞猁狲皮端罩;次一等的穿纯貉皮袍或黑貂皮镶边的衣服;第三等穿黑貂皮镶边“女真式”袍子。巩固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后,早期满洲宫廷还通过立法禁止奢侈行为,以便将社会阶层和政治等级制度化。1637年,朝廷下令所有满洲贵族男女佩戴饰以东珠的帽子和发钗;等级越高,戴的东珠就越大、越多。1644年之后,清廷再次颁布禁奢令,从此亲王在头上佩戴10颗东珠,郡王8颗,贝勒7颗,以此类推,最末一级贵族戴1颗。
被奢侈品连起来的世界
如果说,清朝的消费者重构了边疆特产的来源和悠久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了: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沙菌”或“北珠”和清代的“口蘑”或“东珠”是一回事。至少,它们在清代市场的普及性显示其价值在18世纪和之前时代存在区别。当然,即便在清朝,这些东西也一直都属于奢侈品,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得起。
然而,就算当时人对它们的讨论多于消费,18世纪末的市场需求也达到了相当强烈的地步,以致出现了遍及整个帝国的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甚至扩展至世界范围。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曾经雄辩地论证环境史的第一循环应当是食物的历史: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我们生产日常食物的工作相比不一定更有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日用品的历史最重要。然而还是有人在对稀有物品的追求中寻找意义,甚至为此送命。蘑菇和毛皮或许就是奢侈品,它们在物质文化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标准:它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尺度。最终,它们又为地方、清帝国和全球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联系。
1700年-1850年间,清帝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催生了新的贸易网络,后者改变了整个帝国,以及中国与看似迥异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很多地区出现了追求毛皮、蘑菇等奢侈商品的热潮,以致当地经济命脉都被控制住了。18世纪的最后25年之后尤其如此。世界各国与清朝的贸易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例如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在差不多整个18世纪的最初10年没有贸易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两国发生了争端,清朝分别于1764年-1768年、1779年-1780年和1785年-1792年三次暂停对俄贸易。1792年之后,恰克图贸易重开,贸易额以指数方式增长;仅仅1775年-1805年,利润就是过去的四倍。清朝与缅甸的陆上贸易发展过程与此类似。和北方一样,清廷西南地区与南掌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导致1765年-1769年的中缅战争,于是清朝同样暂停了边贸,结果贸易额暴跌。
当清廷于1790年最终取消禁运,玉石、燕窝、犀角、鹿角和鱼翅进口迅速增长。清朝和琅勃拉邦(今老挝)的陆上贸易同样在这一时期增速。这主要是由清朝对类似产品的需求促成的:象牙、孔雀翎、犀角和鹿角。在海上,中国人利用中式帆船与苏禄王国即今菲律宾展开贸易,贸易额于1760年-1814年翻了一番。1750年-1820年,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海上贸易增长四倍。在这些繁荣的贸易中,港口城市广州见证了美洲和不列颠商船数量的显著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太平洋海獭和夏威夷檀香贸易的高速增长。
居于新贸易中心地位的是毛皮、矿物、海产和森林产品等自然资源。这种贸易的崛起恰好是 18世纪战争结束的成果。追求新疆软玉的“玉石潮”于1776年和 1821年臻于顶点。中国和缅甸的玉石贸易也有类似的时间线:“爆发期”从1760年延续到1812年,缅甸玉价格“暴涨”。在新疆和蒙古方面,从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局竭力控制淘金汉人营地的增加势头。西南边疆的采铜业开始得相当早,可追溯至18世纪的最初25年。然而其黄金时期从1760年开始,当时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地铜矿的高产差不多维持到1820年。中国人经营的矿井在这时期越界进入越南北部,到19世纪初,越南高地的经济命脉就被中国矿主控制住了。同时,在东南亚的海上,中国新开挖的金矿和锡矿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婆罗洲、普吉岛、吉兰丹、霹雳州、雪兰莪州和邦加岛的大地上。
人们对珍珠、玳瑁、海参(也被称作 trepang或beche-de-mer)的追求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图们江和鸭绿江上的中国商人很早之前就在中朝边境的商业城镇庆源和会宁购买海参,而在整个18世纪,朝鲜商人把海参当作贡品带到北京。然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东北地区,盗采海参的行为仅仅在1785年-1818年间才成为一个问题,当时刚开始有人在海边定居。在南海,从18世纪 60年代开始,苏禄王国的海参收获量增加,苏拉威西和荷属东印度的丰收则始于18世纪80年代。19世纪初,该项贸易在两个地区达到顶峰:20年代,海参与胡椒竞争荷属东印度最有价值出口商品的地位。就在这些年,针对中国市场的海参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北部,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参捕捞业已经蔓延到遥远的斐济和大洋洲的其他岛屿。

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
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太平洋都经历了资源开发的狂潮。进入现代之后,尽管某些上述贸易仍然以缩小的形式保留下来,但过度开发使绝大多数繁荣一时的商业在 1840 年衰退甚至崩溃。燕子被“肆意掠夺”,终于在婆罗洲灭绝;苏禄的珍珠贝床被采掘一空;夏威夷檀香树被砍伐殆尽。
实际上,一如我们所知,在同样的时代,淡水珍珠贝、野生人参、海獭以及貂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有些被捕猎,有些被挖掘,有些被砍伐。有些货物是欧美水手运来的,有的来自中国商人。或来自内陆亚洲,或东南亚、大洋洲或美洲。然而,雷同的发展模式和挑战从这些商品的增长与衰落中浮现。当然,18世纪末之前,其他国家很难触碰中国经济的外壳。
不过这一时期消费热潮的“生态后果”是前所未见的。1700 年,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参贸易;没有太平洋毛皮贸易;没有东南亚之外的檀香交易;新疆和缅甸的大型玉矿,马来半岛的锡矿,蒙古、伊犁和婆罗洲的重要金矿尚未发现;中国铜矿也还没有主宰越南北部的经济。婆罗洲海岸以及菲律宾群岛有丰富的珍珠母贝;东南亚海域海龟和海参大量繁殖。受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清朝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影响,内陆亚洲、东南亚以及泛太平洋地区开始面对相似的挑战。
以上内容节选自谢健所著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