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严玉芳
19世纪以降,伦敦出现了一场持续的以公园建设、公地保护、墓地公园化为核心的绿色空间建设运动。其中,墓地公园化是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1875至1900年,伦敦的近百个废弃墓地被转化为供公众呼吸新鲜空气与休闲的绿色空间。
目前国内学界尚无人论及这一话题,国外学界对这一历史现象的主流诠释大致有三种:一是以社会史和医疗史学者为代表的“进步说”,他们认为这种转变对多数伦敦人(尤其是那些很少有机会接触绿色空间的工人阶级)是一种福利,同时社会改革者主导的这场运动把伦敦变为一个更为平等、健康的居住城市;二是以景观史和艺术史家为代表的“退步说”,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是无知的、多余的,因为它对墓碑等墓地纪念物造成了破坏;三是以环境史家彼得·托尔谢姆为代表的“观念转变说”,他认为这种转变主要源于这一时期人们对身体、疾病、环境和宗教的观念变革,并探讨了其转变过程。
其中,托尔谢姆的观念史与环境史视角最具启发性,但他并未指出墓地公园化与绿色空间建设之内在联系。本文尝试以《泰晤士报》、政府报告、议会法案等文献为基础,把伦敦废弃墓地的公园化纳入整个19世纪的绿色空间建设运动之中,从墓地公园化运动的发生缘由、转变过程中的争论以及转变实践等方面,重建托尔谢姆未涉及或语焉不详之处,以期梳理19世纪晚期伦敦废弃墓地公园化的整体演变脉络,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可行性方案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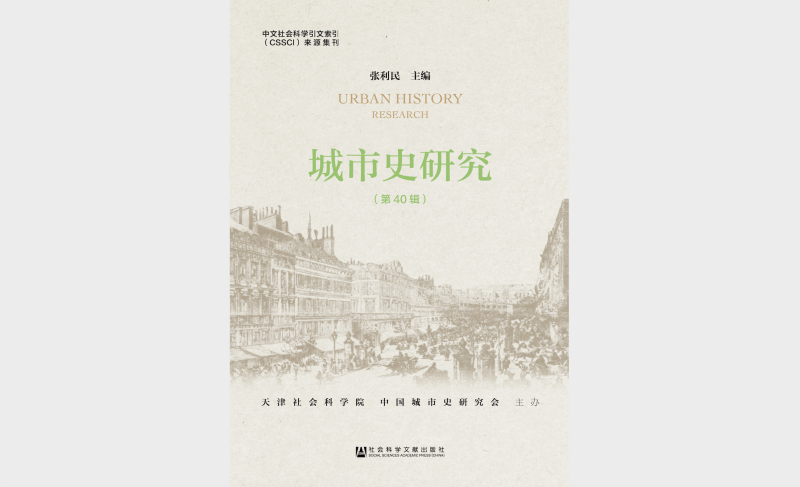
本文出处:《城市史研究》第40辑,张利民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废弃的墓地:19世纪伦敦绿色空间建设的新契机
19世纪伦敦的绿色空间建设运动肇始于1833年的《特别委员会对公共散步场所的报告》,其中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型城镇的人口增长迅猛,社会下层不断加入制造业和机械雇工行列,而城镇在蔓延并吞噬诸多绿地的过程中,却很少为中下层人士提供用作锻炼或休闲的场所,这对他们的舒适和健康尤为重要;不仅如此,为工人阶级提供散步场所可“推进文明和振兴工业”。可见,19世纪伦敦绿色空间建设运动主要指向社会下层人士(尤其是工人阶级),其目标是通过为社会下层提供自然休闲场所来稳定社会秩序和推进工业文明。此后,伦敦市政府在伦敦工人阶级人口密集而绿色空间不足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修建了少数大型公园,如1845年、1858年先后向公众开放的维多利亚公园(占地217英亩)和巴特西公园(占地198英亩),后者还是伦敦南部最大的市政公园。
19世纪60年代,在社会改革家乔治·约翰·肖-勒费夫尔(George John Shaw-Lefevre,1831-1928)、奥克塔维娅·希尔(Octavia Hill,1838-1912)等人的倡导与推动下,伦敦兴起了公地保护运动(commons preservation)。公地保护的支持者同公地的侵占者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抗争,最终才使位于伦敦周边离城区较远的公地大多被保护下来并转化为公园,供公众呼吸新鲜空气与休闲。尽管大型公园建设和公地保护过程十分艰难,也积极向公众开放,但是这些建设成果在付诸实践时却面临通达性与日常性的难题。对于大量居住于伦敦城中的工人阶级而言,或因距离较远、出行不便,或受时间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他们难以经常造访这些场所,这些面积广阔、新鲜空气充足的绿色空间对多数休闲时间有限的工人阶级而言,仍然显得遥不可及。
1877年,希尔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她在《我们共有的土地》一书中描述了两种景观:
可能很少的人能选择一个银行假日去旅行或到乡村漫步,因为他们居住在遥远的城镇中。……伦敦出城道路的数英里布满了各种交通工具——厢型车、二轮马车、有篷轻便马车、轻便双轮马车——被各式各样的驴子、矮马、马驱赶着,如果遇上一个干燥的日子,每条路都被一条厚重的令人窒息的、延绵不断的尘土带笼罩着。
我想很少有人知道闷热的八月傍晚在临近德鲁里街(Drury Lane)或克勒肯维尔(Clerkenwell)窄巷的样子。令人窒息的热气,遍地都是厚厚的尘土,肮脏居所充斥着恶臭,炽热干燥的太阳光照在低矮阁楼的西窗上,使房间如同“烤箱”一般难以忍受。……小孩在炽热的石头上和到处都是刨花屑、土豆皮和菜叶子的地面爬行,大点的孩子在街角无聊地嬉戏。
希尔刻画的场景,一个是节假日公众因交通不便难以轻易地抵达绿色空间,另一个是社会下层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用于休闲的绿色空间,这使社会改革者努力推动的绿色空间建设运动陷入了无效的窘境。希尔率先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把目光投向散布在伦敦城中被废弃的墓地之上。1877年,希尔在国家健康协会(National Health Society)的一次会议上谈道:“在伦敦的房屋海洋中,各地未被建筑的小地方——墓地——还不可思议地被保护着,它们可以被改造成美丽的户外休息室。”布拉巴宗勋爵(Lord Brabazon,1841-1929)也曾指出,无论为公众提供一些大型昂贵的公园多么重要,在其住所距离不远的地方建立小型公园和休息地都更加重要,因为前者由于距离限制只能在少数时间才能被造访,而后者却可以是日常的健康和娱乐场所。此后,伦敦废弃墓地的公园化设想逐渐被纳入绿色空间建设的新范畴。

纪念奥克塔维娅·希尔的森林小道。
19世纪上半期,受“瘴气致病”理论的影响,散布于伦敦城中居所附近的教区墓地、私人墓地等被伦敦人视为瘴气滋生地,认为它对周围居民的健康极其有害。19世纪50年代,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中,因伦敦人对瘴气、霍乱的恐惧,很多墓地停止了安葬活动并被关闭,直至19世纪70年代前期,它们仍然处于废弃状态,多数沦为无人管理的垃圾堆积场。
19世纪70年代中期,希尔等绿色空间建设的先锋者却主张把这种曾经因敬畏、恐惧或厌恶而被有意规避的墓地改造为供公众休闲的公园。在托尔谢姆看来,这一转折性的变化可归因于两个方面:首先是观念的变革,他指出,随着医学知识中“细菌学说”(疾病的根源是细菌而不是腐烂过程中释放的瘴气)的流行及自然环境观念(自然具有净化环境的能力)的进步,与那些“对尸体恐惧而选择隔离与阻止腐烂”的人不同,许多人“开始把腐烂过程视为平衡自然的重要过程”;其次是因缺乏管理与维护,伦敦的废弃墓地所造成的混乱景象有碍城市公共卫生的改善。
此外,伦敦人对土壤、植物等自然因子的新认知更能彰显观念的变革。1873年,担任伦敦城健康和公共分析师的亨利·莱瑟比(Henry Letheby,1816-1876)在健康卫生官协会(Society of 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正确使用消毒》(On the Right Use of Disinfectants)的文章,其中指出:古老墓地的最佳消毒方法是用新土覆盖墓地数英尺厚,并植树种草。英国外科医生弗朗西斯·西摩·黑登(Francis Seymour Haden,1818-1910)倡导一种新的埋葬方式,即“土归土”(earth to earth)这种自然的埋葬方式,他认为土壤能把有机物转变为无机物,把有害物转变为无害物,尸体可以通过转变成碳酸、水和氨等物质,最终成为植物的食物(植物可净化空气)并以新形式重返大气圈。
而传统埋葬用的厚重的封闭棺材隔绝了尸体与土壤的接触从而阻碍了转化过程,因此“我们不可能冒犯了自然而安然无恙,我们只有恰当地安葬死者,让土壤发挥作用,自然执行法则,它才可能惠顾于人”。
可见,在前期绿色空间建设收效甚微,以及新的卫生观念、细菌致病学说和自然循环思想等认知转变下,伦敦城区内大量被废弃的墓地成为绿色空间建设运动突破自身困境的新契机。19世纪70年代,伦敦的公地保护运动逐步拓展到城市的其他空地。例如,1873年1月9日,维多利亚公园保护协会(Victorian Park Preservation Society)的秘书弗朗西斯·乔治·希思(Francis George Heath,1843-1913)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明确指出:在伦敦市长的支持下,为都市居民的健康和休闲而创造、保护和拓展公地及其他城市空地的运动已然兴起。“其他城市空地”之中就包括被废弃的墓地。
废弃墓地转化为公园的推动力、阻力及争讼
墓地公园化的设想早在1843年就被公共卫生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提出,但由于传统观念因素的制约,直至1875年该想法再次被提出时才变成了现实。1875年,伦敦东区圣乔治(St.George’s-In-The-East)的教区牧师哈里·琼斯(Harry Jones)对该区拥有50000人口却没有近便的公园供人们平日里休闲的严峻现实颇感忧虑,由此他向教区委员会提出了把教区附近墓地改造为公园的提议并设计好了改造方案,经过多方努力,他才使教区委员会同意了改造方案。这一成功的转化案例被其他一些教区效仿,至1877年,伦敦已有7个废弃墓地被成功转化为公园。这时倡导将废弃墓地转化为公园的人士中以教区的开明牧师为主,他们作为绿色空间建设运动中一个正在兴起的新型群体,在墓地公园化过程中发挥了引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
几乎同时,希尔也开始积极推动墓地公园化运动。1877年3月,在劝说教友派(the Quakers)放弃出售邦西田园(Bunhill Fields)墓地作为建筑用地的计划遭到彻底失败后,她意识到唤醒公众关于绿色空间与新鲜空气观念的重要性。1877年5月,她在国家健康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绿色空间》一文,以期唤醒公众对墓地公园化的关注与支持。希尔甚至过于乐观地认为克尔协会的职能与公地保护协会这种富于战斗性的机构不同,“保护绿色空间和设计废弃墓地是一种不需要加入法权斗争活动的工作”。结果,如同首都公园协会(Metropolitan Public Gardens Association,1882)的重要成员巴兹尔·霍姆斯夫人(Mrs. Basil Holmes)评论的那样,克尔协会“除了影响公众的观念外,其完成的工作相当有限”。此后,墓地公园化的工作主要是在首都公园协会的倡导与推动下进行。
至19世纪80年代,当伦敦绿色空间建设运动拓展与高涨之时,废弃墓地也面临被铁路公司和建筑投机商因商业目的而占用,墓地公园化问题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并引发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19世纪伦敦的迅猛扩张使城区寸土寸金,而废弃的墓地因遭摒弃无人问津而价格低廉,由此便成为铁路公司与建筑投机商的争夺对象。如《泰晤士报》的编者所言:“铁路公司会尽可能多地利用墓地来设计铁路线,因为这比占用房屋廉价。”至19世纪80年代,伦敦城区内的一些墓地已经被铁路、街道和建筑物取代,如此便给新生的墓地公园化运动造成了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议会在修正1877年《首都空地法》(Metropolitan Open Spaces Act)时,专门增加了有关废弃墓地新用途的条文,其中规定要把废弃墓地转交给地方当局以期把这些土地改造为公园。

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Doré)版画中的1870年代伦敦。
1883年,伦敦西北铁路公司提交议案打算购买位于汉普斯特德路(Hampstead-road)的圣詹姆斯教堂(St.James’s Church)的两英亩墓地用以修建货站,出价15000英镑。墓地托管者欣然接受了这一价格,因为废弃墓地对他们而言原本是破败的、毫无收益的财产,而铁路货站的修建却使之身价倍增,反倒成为一桩幸事。这一议案很快就引起了首都公园协会主席布拉巴宗勋爵的关注并表示强烈反对,他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谈道:把废弃墓地交给铁路公司便意味着伦敦永远地丧失了“健康的呼吸场所”,它们对于窒息的城市人口而言是“健康之肺”;此外,如果该议案获得批准将会为其他建筑投机商提供觊觎之机。他还给上议院写信,恳请慎重考虑该议案,因为废弃墓地可以减少建筑物过度拥挤带来的危害,况且圣詹姆斯教堂的墓地位于人口密集的贫穷地区,更加可贵。
虽然布拉巴宗勋爵希望通过媒介引起更多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但反响有限,加入反对行列的依然主要是公地保护协会、克尔协会和首都公园协会这些伦敦绿色空间建设运动的倡导者。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在墓地上修建住宅不同,因其并未对个人健康构成太大威胁,况且铁路公司侵占土地的事件屡见不鲜,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尽管如此,在拥挤的城市里保护绿色空间已是一个对健康和精神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在政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帕尔摩报》的编辑曾分析道:“毫不犹豫地反对侵占绿色空间已成为公众人物(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的首要任务。”最后,该议案在议会两院均未获得通过,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有建筑商提议在墓地上修建工人住宅,该事件掀起了轩然大波。1883年2月,一位名叫乔治·钱伯斯(George Chambers)的建筑商同废弃的皮尔墓地(Peel-grove Burial Ground)的土地所有者签订了一份关于在此处修建一片容纳400人的工业住宅的合约。该墓地位于伦敦东区贝斯纳尔格林(Bethnal-green)附近,建筑商计划在墓地上覆盖一层混凝土而不移动地下的尸体。这一计划造成了多方政治当局无权干涉的窘境:由于建筑商是在铺盖的混凝土上而不是直接在土壤上修建房屋,这便不受1878年《首都管理法》(The Metropolis Management Act)的约束——该法案规定在填土上建房屋前需要移除动物有机残留物和垃圾,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自然无权干涉;卫生权威机构因不能提供存在有害物或有损健康的确切证据也无权介入;甚至连内政大臣亦因该计划未打扰人类遗体而无权干涉。尽管建筑商绞尽脑汁打擦边球,规避了公共权力的制约,但社会舆论界从卫生和得体的原则出发极力反对。

皮尔墓地
当地关心该问题的居民举行了一次公共会议,坦普尔牧师(Rev.T.Temple)断言,“那些抱持尸体早已腐烂观点的人是错误的,该墓地非常潮湿且水流速度快,了解土壤特性的人都知道当尸体遇上潮湿土壤便会残存多年”,他进一步从卫生防疫的视角解释道,1849年和1854年遭遇霍乱的大量尸体就埋葬于此。1883年12月18日,《泰晤士报》称其为“一个修建工业住宅的奇怪选址”,指出这与铁路公司占用墓地不同,这会让生者在其祖先的尸骨上吃喝睡和抚育后代,而当混凝土开裂后有害气体便会从地下释放出来,这有违健康和得体法则;使人群密集地居住在藏尸地,这对每位拥有礼教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感到厌恶,而处理这些地方最恰当的方式是覆盖上植被以吸收和中和释放的气体,让自然之风在地表自由地吹动。
不久,布拉巴宗勋爵积极响应《泰晤士报》的言论,并引用贝斯纳尔格林地区健康卫生官乔治·帕多克·贝特(George Paddock Bate)的话说,“如果棺材完好无损,人们会发现埋葬50年后的尸体与先前是同一状态——可以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与最初入土时的腐烂状态一样”,由此他主张任何试图侵占墓地的建筑活动都应该被禁止,以避免这样的危险。此外,布拉巴宗勋爵还向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建筑法委员会(Building Act Committee)写信寻求共同的反对,并求助这些政治机构利用法权对在墓地上的建筑活动加以禁止。
舆论界的压力促使政治当局迅速关注该问题。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一直反对在墓地建造房屋,它在给布拉巴宗勋爵的回信中声明始终在密切关注该问题并将在适当的时机采取措施加以制止。1884年它同被告方钱伯斯在法庭进行了对峙,但被告方的驳斥理由有二:其一,他认为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作为公共机构在干涉私人财产,如果要其放弃建筑计划,必须给土地所有者赔偿;其二,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制定的建筑法令中所指涉的令人厌恶的物质包括“死猫、白菜帮及其他腐臭物质”,但并不涵盖人体,所以并未违背法令。结果,首都公共事务委员会一方败诉。从这场争讼可以看出,由于当时伦敦在墓地上限制进行建筑的相关条款不够严密以及缺乏有关墓地用途的专门立法,所以才给了建筑商以可乘之机,墓地公园化运动遭遇了一次不小的挫折。

布拉巴宗勋爵(Lord Brabazon,1841-1929)
1884年8月,《废弃墓地法》(Disused Burial Grounds Act)正式在议会通过,从法律上禁止了利用廉价墓地进行牟利的经济活动,从此在废弃墓地上建筑均属违法行为。于是,墓地的托管者纷纷向克尔协会和首都公园协会提出转化墓地的请求。当伦敦的废弃墓地摆脱了铁路公司和建筑投机商的威胁而即将被公园化时,却受到了来自公众层面的质疑与挑战。
卫生质疑与情感挑战:废弃墓地转化为公园的争论
在伦敦绿色空间建设倡导者成功阻止在废弃墓地上进行建筑的过程中,他们一致强调墓地尸体腐烂时释放的气体有害生者的健康,但又主张把墓地改造成供公众休闲的公园。这种“矛盾”使许多人不由地产生了疑惑:“如果墓地不利于健康而不适合作为建筑用地,那么它们又如何能被用作公园或游乐场所?”
墓地公园化活动受到了威斯敏斯特公爵的高度颂扬,他说:“没有什么比当前把废弃墓地转化为愉快公园的运动更令人欣喜,保护公园之外的城市绿地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情和伦敦的荣耀。”这一言论很快受到了质疑,1884年6月4日《泰晤士报》刊登的埃利斯·利弗(Ellis Lever)的信件表达了他对墓地公园化的担心和反对。利弗认为把墓地转化为供公众休闲的公园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以来自纽约的牧师本利斯(Rev.J.D.Bengless)在通信中列举的纽约墓地公园化所造成的健康危害例子为证。
这一观点随即引起了布拉巴宗勋爵的反驳,他首先指出了本利斯牧师所列举的例子并不是纽约墓地公园化的普遍现象,其中一定另有原因;随后,他以卫生科学为依据,坚信混乱不堪的废弃墓地经过良好排水、覆盖土壤、植树栽花,能成为城市污浊环境中新鲜空气的提供者,并扮演着部分清道夫的角色。利弗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引用亨利·汤普森(Sir Henry Thompson)的话说:“所有放置在土壤的尸体都会污染该地上面和其中的土地、空气和水”,由此重申墓地最不适合作为健康的休闲地,进而他认为墓地可以得到美化,但不应向公众开放为休闲场所。利弗的反对论调很快得到了响应,他收到了贝斯纳尔格林的牧师塞普蒂默斯·汉萨德(Septimus Hansard)反对墓地公园化的信件。

这一事件引起了另一场争论。汉萨德认为布满尸体的墓地仍然存在病菌,所以这样的地方不该被打扰,如果打扰古老的墓地可能导致伤寒成为伦敦永久的瘟疫。国家健康协会主席兼首都运动场协会副主席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Hart)认为,汉萨德等人的恐惧完全是荒诞的,因为在废弃墓地上仿照自然界指示的方法覆盖花园土、种草、铺路和植树绿化,科学证明这些方法能消除那些他们所担心的可能性危害,这就是自然的真正魔力。没有什么消毒方法比在墓地表面铺上数吨大地母亲的泥土更加有效;没有什么化学药剂比将埋藏在地下的无生命有机物转化为有生命且有益健康(草木可吸收氮和二氧化碳)的植物组织更有潜力。它们把这些元素建构成健康的植物组织并向大气释放生命所必需的气体。它们是流行说法所言的地球之“肺”。
针对批判,汉萨德很快进行了回应,他特别指出:不适合转化为公园的是那些尸体密布的旧教区墓地,而不是坟墓稀少的新教区墓地,因为前者只要动土便会翻出尸骨而且容易造成地面下陷,这既有害健康又存在安全隐患。此外,针对汉萨德的担心,还有人从科学的角度提供建议,认为应在墓地种植多刺的紫草科植物(prickly comfrey),它们的根能有力地向四面八方延伸;通过自然的化学过程,存活的细菌至少要通过一个很长的过程才能袭击人类。最终,相对于利弗和汉萨德的观点,通过“自然之力”可变墓地为一个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空间的科学学说逐渐占据上风,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
在墓地公园化的进程中,除了回应公众的卫生质疑之外,还需要顾及作为社会文化风俗的伦理观念,以及与墓地中的逝者存在情感联系的人们的心理感受。譬如,1885年,詹姆士·W.兰伯特(James W.Lambert)写信给《泰晤士报》,对墓地公园化表示强烈不满。兰伯特因为担心他叔叔的家族墓地会被转化成游乐场供儿童进行骑马嬉戏,故而斥责了这种打扰自己亲人安静的世俗行为,他甚至认为社会改革者主导的墓地公园化慈善活动是以牺牲中产阶级的情感为代价的,他表示深感无助和遭到了掠夺。
这一言论很快被首都公园协会的秘书巴兹尔·霍姆斯(Basil Holms)称为在“误导公众的观念”,他指出未得到墓地所有者同意的转化是违法的,并且公园化之后的墓地不会被允许用作骑马等娱乐场所。同时,伊萨贝拉·M.格拉德斯通(Isabella M.Gladstone)也进一步强调说,1881年的《首都空地法》规定,要“恰当地和虔诚地使用那些被转化的墓地,并永久地维持其为不允许进行游戏和体育运动的绿地”。故而,公园化的墓地在功能上对“宁静”的预设,缓解了与墓地逝者有关的人们的情感压力,为该运动的顺利展开消除了另一阻力。
纪念、秩序与净化:墓地公园化的指导思想与创新实践
伦敦废弃墓地的转化工作主要是在克尔协会和首都公园协会的指导下完成的,废弃墓地转化为公园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负责机构的确定、墓碑迁移、碑文保存、花园设计中的植物选择、个性化改造方案等。

当负责设计的权力机构(伦敦法团、地方当局或环境组织)确定后,它便委派一个专业团体对需要迁移墓碑的墓地进行文物保存工作,这一工作需要在墓碑开始迁移的至少前三个月开始。他们要尽可能记录下墓碑和纪念物上的名字与时间,这些内容还要通过报刊媒介公之于众。其中有两点特别规定:一是墓地中埋葬着自己亲属的人有权阻止移动他们的墓碑;二是墓碑上的碑文将永久保存在教区的登记处。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墓碑被迁移到墙边集中安置,或者在不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下保留在原地不动。此外,如果墓地中有著名人物的墓碑,这块墓碑会被保留,并将成为改造方案中的一个历史特色。
完成墓碑、碑文的保存工作后,墓地的设计通常由精通园艺的人士来执行。早在1843年,英国园艺家、植物学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顿(John Claudius Loudon,1783-1843)在其专著《关于墓地的设计、绿化和管理以及教堂墓地的改善》中论述了相关问题,其中,他指出墓地决不能有乔木、灌木等绿带或绿丛,因为这不利于空气流通和阳光照晒。伦敦墓地转化为公园的设计实践虽然没有一个主导模型,但存在几个共同的步骤与方式:首先是在墓地上覆盖新土,以发挥土壤的净化能力;其次是修建碎石小径;再次是对地面进行排水;最后是选择既能在伦敦煤烟环境下生存的抗逆性强的树种或植物(如悬铃木、杨树),又有利于净化墓地这个特殊环境的植物(如多刺的紫草科植物)。
至19世纪末期,伦敦近百个废弃墓地被成功转化为公园。其中,伦敦东区转化最好的墓地之一是牧师哈里·琼斯较先提议改造的圣乔治墓地。关于墓碑的处理,除少部分原地不动外,大部分被安置到公园围墙边,而在中央屹立着该教区恩人雷恩夫人(Mrs.Raine,1725年逝世)的墓碑,这种设计既错落有致又具有纪念意义。该墓地被绿化和改建之后,鲜花盛放,夏季香石竹芳香四溢,既有专为花坛装饰提供所需花卉的小型花房,还建有自然学习博物馆,馆外尚有一个专设的实践空间供学生进行自然学习之用,这种自然教育的创新成为该墓地改造成公园后最引人注目之处。
可以说,经过19世纪晚期的改造活动,伦敦的废弃墓地“从沉闷和凌乱变得有序,也从不卫生和不雅观的地方变成了街道与房屋海洋中引人注目的避风港”。这些被转化成公园的城区墓地使用情况甚好,不但便于造访,而且受到了人们的喜爱。1884年,《每日电报》的编辑在《废墟中绽放》一文中,详述了伦敦被转化墓地的使用情况,并列举了牧师劳伦斯(Rev.C.Lawrence)的证词:“公园里有很多人,许多病患和体弱者在好天气的日子里在公园坐一整天,这场运动的成功甚至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本文选自国内唯一的城市史学术刊物《城市史研究》第40辑,刊发时有删节,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严玉芳(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