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琐碎时光都被短视频、微博、公号朋友圈占据的今日,偶尔读读散文也不错。苏童这样写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言语。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
如果说苏童的小说当年以先锋、细腻、绵长而使人记忆,那么他的散文则以异常的松弛、平静和寡淡而使人忘怀,像呼吸一样不去刻意彰显自身的存在。
撰文 | 董牧孜
在我小时候,那种现当代名家散文集很受欢迎,经常在城镇书店里塞满一整排,中小学生提高作文往往靠学习他们的文笔与气韵。如今不再是那些质朴简白小散文流行的时代了,生活节奏快得很,这类书看起来往往有些不轻不重,不咸不淡,略有滋味,又稍嫌寡淡。
《活着,不着急》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苏童的散文精选集,收录了50余篇40年来的散文。1963年出生的苏童,在书里自嘲“半老文人”。这本书是苏童的首部插图散文作品集,搭配的摄影作品很有中老年画风。散文主题无非是童年回忆,江南之美,市井百态之类,行文、节奏与话题也有些时代感了,比如21世纪初面对追星族的不解,男性文人对美丽女子的诗意美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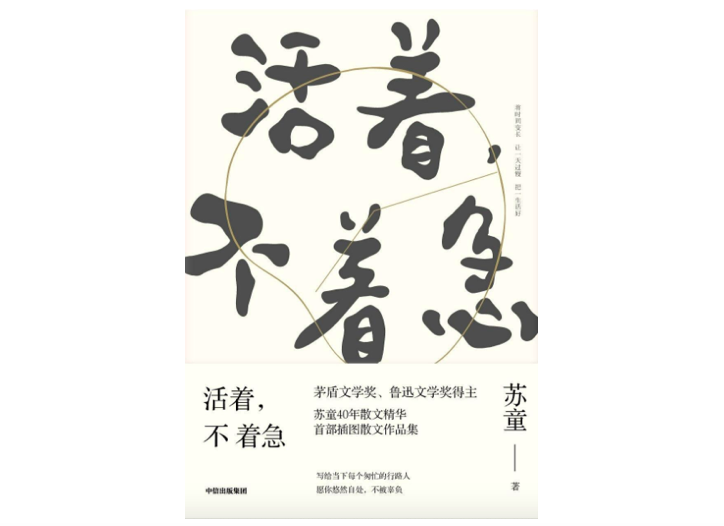
《活着,不着急》,苏童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在琐碎时光都被短视频、微博、公号朋友圈占据的今日,我翻了下这书,突然觉得读读散文也不错,没有过于丰富的挑逗与刺激,也没什么重得拎不清的理论,三言两语都简单熨帖,说的尽是日常道理。
苏童这样写自己的生活,“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言语。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一个中年人所拥有的时间里,妻子和女儿分割去了一半,但“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这样的中年状态,趋于平静与宽容,而没有置身瓶颈的局促与困顿,也能从容地折返回童年与记忆,这大概是种不错的生命体验。在《童年生活的利用》一篇小文里,苏童说,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孩子们不知道,未来生活的困境从他们幼时的游戏中就开始了,离群的孤独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命运,恐惧和抗争将成为未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使命。一个作家往往意识到,“也许我们都将利用童年记录一些最成熟的思想”。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都会回到童年。
苏童在《九岁的病榻》里写道,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始于9岁。那时候,肾脏出了毛病,休学卧床半年,离群索居。在九岁的病榻前,时光变得异常滞重冗长,南方的梅雨滴滴嗒嗒下个不停,小便也像梅雨一样解个不停,“我恨室外的雨,更恨自己的出了毛病的肾脏,我恨煤炉上那只飘着苦腥味的药锅,也恨身子底下咯吱咯吱乱响的藤条躺椅,生病的感觉就这样一天坏于一天。”而一旦病愈,离开了九岁的病榻,苏童说,“从此自以为比别人更懂得健康的意义。”
追溯童年让人觉得宁静。成年之后,人则变得沉默。《沉默的人》这一篇,苏童追忆了自己如何从寡言者变成健谈之人的。曾经,“在许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而后来,因为不得已需要说话,于是开始大量地说话了,渐渐地需要变成了习惯。不管是谁与谁交谈,他总是争取比对方多说一些话。苏童写道,“奇怪的是我在不停地说话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乐,这快乐从前是与我无缘的,这快乐的感觉有点朦胧,有点像拧开水龙头后喷涌而出的快乐,也有点像铁树开花聋哑人歌唱的快乐。”
这种感觉,诉说的是一个心灵向内的人,如何与社会生活磨合至圆融的状态。学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会生活。苏童还写道,“生活当然不仅是说话,生活也包括沉默,沉默的人以沉默对待生活,但沉默是一把锁,总会有一把钥匙来打开这把锁,这也是生活。”
苏童的散文最终趋于一种平凡的安详。《苍老的爱情》这篇里有金句,说“有时候爱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但他针对的不是爱情的缠绵、疯狂、诞生与灭亡,不是那些吸引世人目光的浓词艳篇,而是老朽的夫妇之间的“白发爱情”。这是一种平淡、老迈的爱情。苏童讲了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妻子亡故那日,老人也无疾而终。苏童说,老人是被爱情夺去了剩余的生命。“爱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针对的是非常苍老的、有年轮的爱情,“它不具备什么美感,也没有悬念和冲突,被唯恐天下不乱的文人墨客有意无意地疏漏了,但我肯定这样一种爱情随处可见,而且接近于人们说的永恒。”
一名作家要保存永久的魅力似乎很难,只有成为某种形式感的化身的作家才能让人长存于心。如果说苏童的小说当年以先锋、细腻、绵长而使人记忆,那么他的散文则以异常的松弛、平静和寡淡而使人忘怀,像呼吸一样不去刻意彰显自身的存在。
作者:董牧孜
编辑:徐悦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