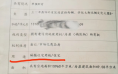作家与读者这两个身份都以书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书的存在又以作家的写作作为前提。当作家停止写作,还能称呼他们为”作家“吗?当作家停止写作,读者还有称其为”读者“的依据吗?
探讨作家为何写作看起来是个理所当然的命题,可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从反面提问”作家为何停止写作“,似乎这个想当然的命题增加了许多哲学意味。不管是信文学信仰的动摇、自身情感陷入困境还是看透了写作的本质抑或单纯地想停笔休息,在对”不写“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与写作间更为深广的纠葛与联系,获得对人世更清晰的辨认。
尽管作家有时停止不写,但对于自己所写的作品,很少有作家矢口否认自己的创作。但对于有些读者来说,明明自己读过很多书,却不愿承认自己是个虔诚的读者。读书在大众眼中,似乎与某些”身份“相隔甚远,像是废纸收购站的打包工。不过,书并带着歧视的眼光看待读者,哪怕身份低微的读者羞于启齿、压力重重,阅读好书也会带给他心灵的安稳与隽永。
书与作家 他们为什么停止写作?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好莱坞往事》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过气动作片演员里克·达尔顿(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在房车里,被自己气得满脸通红、暴跳如雷,他指着镜子里的那个人不断咒骂,骂自己竟然在片场忘记了台词——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耻辱。往日风光不再,达尔顿陷入对表演的焦虑,以至在那场与主角狭路相逢的戏中几乎无法完成表演,导演不得不冲他吼叫,刺激他继续下去。如果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巴托比症候群》中的概念去定义达尔顿彼时的遭遇,他遭遇到的正是表演上的“巴托比症状”。

《巴托比症候群》,作者:恩里克·比拉-马塔斯 ,译者:蔡琬梅,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3月
巴托比是梅尔维尔在短篇小说《书记员巴托比》中创造的文学中最迷人的人物之一。他脸色苍白、形销骨立,当律师事务所老板让他工作时,他温柔、平和又坚定地说:“我宁愿不。”他一路拒绝下去,对所有事情的态度就是一句“我宁愿不”,最终他拒绝了食物,结局也正如你所料。在《巴托比症候群》中,比拉-马塔斯进入文学里“不”的迷宫,收集了众多染上巴托比病症的作家的奇闻逸事,其中的作家大部分实有其人,也偶有杜撰。
这本书的出现,本身就是个小小的悖论。写“不写”,也可以达成写。对此,比拉-马塔斯早有戒备,因此在开篇他就说:“罗伯特·瓦尔泽早就知道,写无法写作这件事,同样也是写作。”比拉-马塔斯和罗伯特·瓦尔泽的角色就像莱昂纳多,在上文提到的那场戏里,莱昂纳多表演了“无法演”而达成了表演。
《巴托比症候群》临近结尾时,比拉-马塔斯告诉我们:“事实上,这本日记不可能有一个中心主旨,就好像在文学里也找不到一个中心思想一样。因为每篇创作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得以逃脱任何一种被设定、被定义或是被归类的可能性。”这本书是日记体,或者说脚注式小说,作者的大部分工作是从其海量的阅读中找出哪些作家曾患上巴托比病症。这让有些人觉得作者在掉书袋,客观上来说,如果比拉-马塔斯没有书袋,这本书也就无从写就,但这并不是这篇文章要关注的内容。
此外,既然比拉-马塔斯说这本书没有中心主旨,本文也就不好违背作者意愿,像学生做试卷似的去分析中心主旨了,而只是从表面来看看,这本书到底写的是什么。
无疑,写的是患有巴托比病症的作家们。如果把这些作家的名字列出来,其光辉程度绝不比近十年的诺奖作家群暗淡丝毫:罗伯特·瓦尔泽、胡安·鲁尔福、塞林格、兰波、卡夫卡、维特根斯坦、梅尔维尔、德·昆西、王尔德、马拉美……事实上,这些伟大的名字背后都有杰作竖立,几乎不受时间之河流的侵蚀。
然而,他们在某个人生阶段(或长或短),陷入了“写作之不可能”的泥淖,也就是说,阶段性地患上巴托比病症,个中原因各有不同。有人是觉得自己太过渺小,对文学的畏惧让他/她无法下笔;有人是因为拒绝苦思,不想再耗费心神;有人是因为早早自杀;有人是因为觉得“艺术只不过是胡说八道”;有人是因为更高灵魂的追寻;有人是因为自己已经不朽,无需再写……
比拉-马塔斯就这样收集并向我们展示了“不写”的万花筒,展示了作家与书籍(写作)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也是人与书之间关系中极为特殊的一种。毕竟我们从作家口中最常听到的,是“我为什么写作”。就像不写的原因一样,写作的原因千奇百怪。寻求真理、表达情感、获得拯救、有写作天赋、写作外无事可做、吃饱饭、避免自杀……这些理由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表现作家和写作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还可以给正在准备开始写作的人以契机和鼓励,但也许,在对“不写”的思考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和写作之间更为复杂、指向更为深远的纠葛,获得对人世更清晰的辨认:文字是否足以表现这个世界,名誉与荣耀是否是荒谬的,如何实现对更为高尚的灵魂的追寻,以及沉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最后这个问题可用加缪评论尚福这位“绝望中的圣徒”时所说的话作答:“他的态度是如此极端而激烈,驱使他走向永不妥协的反抗之路,而最终,走向永远的沉默。”沉默有时是“不妥协”,正如鲁尔福、兰波这样的巴托比作家。说到这里,有个问题似乎不可避免——那些不断出版的无聊书籍,是怎么回事?
书与读者 汉嘉们的孤独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杨司奇
所有的读者都期待在一种强烈的阅读震颤中遇到自己喜爱的书。这种喜爱使人沉醉,使人发狂,使人想要占有。于是有了更多的书,有了更多的占有,有了书房。每个爱读书的人都期待着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在这个隐秘的世界里,他们得以卸除面具和伪装,纯粹用一颗心去生活。
尤其对于精神世界广阔但肉身却孤独地处在世界边缘的人来说,书房成为一个通往无限与可能性的洞,《刺猬的优雅》里的女门房,《何时是读书天》里的送奶女工,《天空中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里的邻居老伯,都有这样一个抚慰孤独的隐秘的洞。在他们的洞里,几乎都有一本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但是在洞外,他们都心照不宣、小心翼翼地伪装成目不识丁、庸俗无知的人。为什么要伪装?为什么爱读书之人要伪装成不会读书之人?
因为“不合身份”。《过于喧嚣的孤独》里,废纸收购站的打包工汉嘉在工作之余,总是喜欢和来淘书的高度近视的美学教授玩身份伪装的游戏,他戴上帽子又摘下帽子,一会儿是可怜兮兮的被老打包工欺负的年轻工人,一会儿又是古怪的、像恶狗一样对待年轻人的老打包工。他没有家庭,没有朋友,当他到酒吧喝啤酒的时候,额上粘着打死了的苍蝇,口袋里掉出臭烘烘的老鼠。这种形象的汉嘉,被认为是不读书的、被抛弃在“时代垃圾堆”上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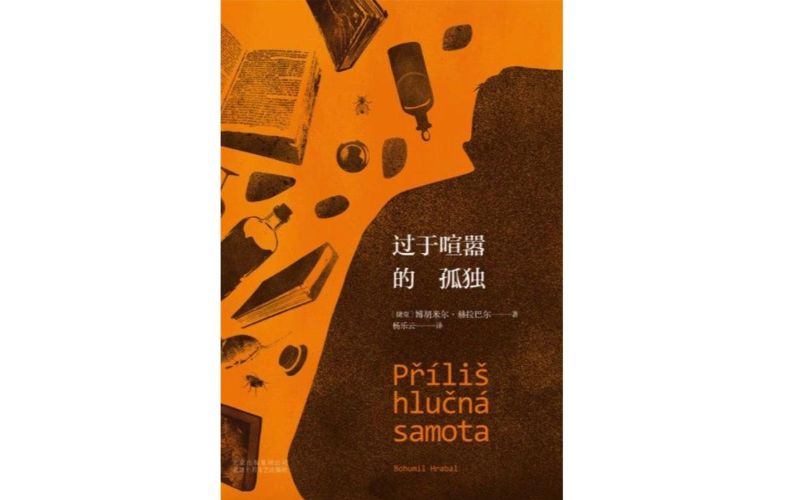
《过于喧嚣的孤独》,作者:(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译者:杨乐云,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年10月
但没有人知道的是,汉嘉懂得每一本书的价值,懂得如何找到那些珍贵的书籍,羊皮面的歌德和席勒、藏在中心的荷尔德林和尼采。他像制作艺术品一样制作废纸包,用名画仿作来为这些注定赴死的书籍包装。在三十五年的废纸处理工作中,他的身上蹭满了文字,无意中获得了百科全书的学识。
他的住所里到处都是书,厕所里留下的空间仅够坐在马桶上,那些书直堆到天花板,坐下起身只要稍不注意,半吨重的书就会翻滚下来。但是运到废纸站里的珍贵书籍是如此之多,为了存下更多的书,他在卧室里两张并拢的床铺上架了隔板。三十五年来,汉嘉带回了两吨重的书,他的书房是由大大小小的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穹。
汉嘉曾预想的一种结局是,被这些书所埋葬。他毁灭了这么多书,理应遭到报复。但是当他去布勃内见识了“大得跟威尔逊火车”似的巨型压力机后,他受到震动,进而绝望。汉嘉意识到,因为这个巨型机器的出现,世上的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成批成批的新书会被直接运去纸浆厂,不再会有人往这些书的身上瞧上一眼,因为毁灭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工人们停不下来。汉嘉的压力机,是属于过去的压力机,他也是属于过去的打包工。他将被调去印刷厂捆白纸,捆那些没有斑点、没有人性的白纸。他再也捞不出一本珍贵书籍。
在让-保尔·迪迪耶洛朗的小说《6点27分的朗读者》里,汉嘉曾见到的巨型压力机有了一个惊悚的名字“碎霸 500”,再精美的书脊,再结实的装订,几秒内就会粉身碎骨,成千上万的书籍都消失在这个家伙的胃里。当一个名叫朱塞佩的工人在清理这台碎霸时,双腿被吞噬,随纸张一起被碾碎、捣烂,融进千万张新纸张里,最后印成一本名为《从前的花园与菜园》的书。朱塞佩的形象与汉嘉的形象形成了某种重叠。
汉嘉选择了留在过去。他拒绝被赶出他的天堂,拒绝离开他的地下室。就像《海上钢琴师》里,1900选择留在废弃的邮轮上,没有踏上陆地。他像塞内加尔跨进浴盆一样跨进他的老旧压力机的机槽里,在废纸和几本书的中间,躺了下去。此刻在他的哲学中,他想要将regressus ad originem(朝着未来后退)和progressus ad futurum(向着本源前进)重合在一起的梦想正在加速靠近。他的手里牢牢攥着一本诺瓦利斯的作品,手指按在向来使他激动不已的那一句上,与书一起消失了。
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这一影像在汉嘉身上,在被书所埋葬的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身上,似乎成为了一种命运,一种深沉的隐喻。那个无限与可能性的洞在这幅影像中,似乎也玩起了形象伪装的游戏。
撰文 | 张进 杨司齐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