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丨宫照华
在这个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诗人很容易困惑。一方面,身为人类的心灵要求他们关注现实,感知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们还要与语言的暴力对抗,甄别虚伪的语言、粗暴的语言和本真的语言。另外,诗人最终的工作,是要求艺术家坚守内心的世界与艺术自身的规律,任何应景之作都有滑向失败与媚俗的可能。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了诗人王炜。自疫情发生后,他对语言和写作不断产生新的思考。一个成熟诗人,在此刻应该如何选择?在那句被曲解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激发的情境误读背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语言的功能?在这次采访中,王炜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王炜,诗人,作品有《灭点时代的诗》和《诗剧三种》等,也撰写与诗学、思想史和历史哲学三者相关问题的文章。
每一场灾难,都是人类文明遭受的灾难
新京报:这期间在读哪些书,或者在看什么电影?
王炜:谢林的一篇文章《论哲学视角下的但丁》,朋霍费尔的长文《谁是今在与昔在的耶稣基督?》,弗朗西斯·哈斯卡尔(Francis Haskell)《历史及其图像》的几个章节。雨果两部诗集《凶年集》和《惩罚集》,开始读他的史诗《历代传说》。陆陆续续看了一年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几种关于伊斯坦布尔城市历史的书。看了很多画,很少看电影。
新京报:在这个特殊时期,阅读卡尔维诺或昆德拉,会不会比阅读福山与加缪显得更加冷漠?如何看待这个特殊时期的个人阅读选择?
王炜:对这几个作家的这种区分,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愿意对现代文学稍加了解的话,就会对此有所改变。把卡尔维诺(且不论他早年的左派经验)放在与公共事件所标示的现实相对立的位置去认识,这是很错误的。昆德拉作品的政治性众所周知。对《鼠疫》的及时使用,有陈词滥调和市场欲望的性质,即使是反应性的使用,也说明文学的生命力。如果人们真的就此去读那本书,仍然是有意义的。还可举例的是,布鲁诺·舒尔茨不会被认为是现实主义作家,但如果我们因此去评判他的文学生命,我们就和那些枪决他的刽子手是一样的。
每一场灾难,同时都是人类文明遭受的灾难。如果我们作为读书写作者,还自视为一个文明的“人”,首先就要摒弃这种对文学家的肤浅和错误区分。
福山出现在这个名单里,显然是因为那个意外——并非每个偶然现象都需要专门解释。看到豆瓣和朋友圈里许多人都在转福山那本书的封面时,我想起一个来源虽待考、但挺有意思的故事。《存在与虚无》出版后大卖,出乎出版者与作者的意料。后来知道,当时金属原料紧缺,人们没砝码可用,一个家庭主妇意外发现《存在与虚无》(首印版)刚好重一公斤,购物时可代替等重的砝码来称重,价格也比砝码便宜。经验传开,书被抢购。
看到方舱中那个读书人的照片时,我不禁想,如果福山看到他的书在当下那个陷入灾难的城市中出现,且以这种方式被关注,不知道会是怎样的心情。随后,福山本人也在推特上转发了那条新闻。这件事里的福山和面对偶然性的萨特,好像有一种相似性。这种意外的带货效果的发生,和前阵子看到一篇关于公共参与的“儿童化”的文章所谈现象,或有一致性。表达从一个困境中的读书人那里感受到的安慰激励,不在于都去读那本福山的书,而是可以因此提醒自己,也一样别放弃自己的阅读。

在武汉方舱医院阅读福山作品的患者。
听从内心的声音,并非自绝于现实
新京报:在这个特殊时期,如何看待诗歌的职责?它是否一定要对现实作出回应?目前,大众对于诗歌的功能是否存在误解?假如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继续写超现实诗歌;一个画家,继续临摹桌子上的静物瓶罐,他是否会显得有点麻木不仁?
王炜:并不存在被总称为一个类别的“超现实诗歌”。仍需了解的常识是,超现实主义本身有非常鲜明的政治性,甚至是把创作者推向未来政治的动力。布勒东,堪称政治活动家。被纳粹枪杀的德斯诺斯是超现实诗人,也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战士。勒内·夏尔和超现实主义关系密切,在二战期间是一位游击队领导人。在《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评介》的一文中,尤瑟纳尔写道:“政治之诗,即命运之诗。”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彼此不同的诗人在“责任”这一命题下的表现:叶芝,奥登,写下《艰难时期的弥撒》的R·S·托马斯,等等。
越是文学初习者,越难辨析一种模模糊糊,却又被认为是一种经典方式的“诗与现实”的距离感。这是一种在“诗与真”这一问题上的不成熟。创作与社会议题无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当然绝不等于“麻木不仁”。
“麻木不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始终把“诗与现实”的模糊而又自我经典化的距离意识所固化下来的思维方式。如今更应讨论的,不是写作者与社会议题的这种陈词滥调的文人化距离感,而是要意识到:时代在剧变。诗人应当有这种敏感。我们正处在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剧变时期。
这个问题,也显示了每个时代创作者的内在焦虑。这虽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仍然有其积极性:至少,它还会引起焦虑。创作者是否能够,坚持把“时代的喧嚣”与“走自己的路”(这是但丁在他的黑暗时代中对自己、也对未来之人的要求)区分开来呢?我们都知道,创作者不应听从政治的意见,而是内心的声音。
听从内心的声音,并不是自我隔绝于现实,而是在政治意见扭曲自己的工作时,始终服役于内在创作使命的真实性,把那种不可被收割、不可被驯化的使命的真实性保留下来: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
以“大众的误解”为理由的人,常常只是暴露了自己的误解。一个严肃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者,不应视“大众的误解”为自己的逻辑前提,这会导致失职。诗人不能因“大众的误解”,而自感失败或者荣耀。
批评因当下的现实而愤怒的人,又是怎样理解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处境与位置的呢?在那篇《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评介》中,尤瑟纳尔还写道:“我怀疑现代读者(以及我)在这类流露真情实感的作品面前的恼怒是否构成一种同样危险的装腔作势。”这话用来说“作品”之外的事,也是一样的。陈词滥调最泛滥的一种——如“防疫诗”和认为自己能够与之区别的士大夫应景之作——已不用批评。还有另一种陈词滥调——根据阿多诺的话,指责继续读书写作的人们,这同样野蛮。
公共事件中的语言问题:捍卫抑或断裂?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在你印象里,是否还有其他类似的、被人为曲解或挪用的论述?
王炜:阿多诺这句话的重现,是因为那个众所周知的愚蠢误用,这确实很荒诞。用一个写作同行的话来说,其荒诞性“不亚于戈培尔部长本人说出这句话”。这句话在此之前就经常被提到,例如在“防疫诗”粉墨登场的时候。随后,这句话也被用于对整个文学领域,对于被总称为“作家诗人们”这一群体的攻讦。这些现象,我想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值一驳的。
E·沃格林提到过一种人,叫“意见分子”,这种人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知识领域的意见,常常反映出社会的知性衰退程度。福山大卖,阿多诺那句话人人顺口就来,是同一种现象。重理轻文和狭隘实用主义的教育,以及人文领域退化的后果,是精神层面的普遍不成熟。但是,需要看到的是,从事文学的人们不仅不能豁免于这种不成熟,往往更是把这种不成熟内化了。
阿多诺这句诤言仍然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思想领域里已不乏回应。最近,一些写诗的同行,还对这句话的原文语境做了普及性的解说,有助于还愿意继续关心这个话题的人在引用时,用得比那个评论员对一些。一方面,这句话的再现,恰好也说明我们并没有摆脱历史;另一方面,这句话的一种内在提醒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是与荷尔德林那句著名提问“诗人何为”之间,有前后关系的一个激进否定。也许,每个诗人都应该在对这两句话的内在关系的认识中,认识自己写作的位置。
阿多诺的话语,指出了一种无法被简化、无法抹去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是被死亡所标示的。由于奥斯维辛的发生,这种不可能性,伴随着每一个既作为人类一员,也作为表达与创作者的人。“绘画还存在吗”、“电影死了”、“哲学的终结”等现代思想,和其他各个创作领域,都是在这种被死亡所标示的不可能性的激发中产生的。文学在一种不同以往的新的语言中被创造,哲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其说阿多诺的话是一句终结,不如说是一个标示,不断指给人看那些人们以为构成了文化生活,却参与构成了奥斯维辛的东西。如果,我们还在“奥斯维辛之前”(这一“之前”并不是线性历史时间意义上的“之前”)的文化语言或“文学场”之中写作,那么阿多诺的话就是有效的。而且,我们——写诗的人——完全不用反对阿多诺的话,反倒是更有责任保存这些激进否定的诤言,将它们一直保持在思考之中。
每个重要的公共事件,都会伴随着语言问题的争论。文学写作者和思想者,都有责任把语言争论引往并保持在应有的问题重心上,以免沦为漩涡的花边。前几天,大家也看到了一些修辞家对汉语的贫瘠粗鄙化表示惋惜的文章。只要坏语言的环境继续存在,修辞家就会不无道理。
但是,修辞家并不是语言捍卫者,还会因为有机会参与对权力语言的优化而自喜。捍卫语言,诚实是初步的,从诚实带来的“粗糙”(例如布朗肖说荷尔德林的那种“伟大的生硬”)中走向语言裂缝,比修辞带来的美化更有价值。那种“粗糙”,是与写作者的原创性和在文体上的精湛并行不悖的,而修辞带来的美化是一种关闭。然后,保罗·利科说,诗人乃是修辞家的对立面。并且,诗人要率先显现并帮助语言走向这种对立面。
除了文字语言的陈词滥调,也有图像的陈词滥调。可以常常看到的是,图像创作者不仅对文字语言的陈词滥调,乃至从总体上对文字语言的蔑视。但是,图像创作者也可以注意自身领域对“美化”的需要;在提纯、标举公共事件中显现的“美”时,也可以想一想,它与我们都不陌生的那种图像对典型性的需要(如典型人物与典型情境构成的样板戏美学)是否一体两面。以及,图像创作者是否也可以尝试,径直以戈雅在“黑色壁画”中表现的那种“坏图像”为尺度,反观自己。
事情总是这样:一方面,越附庸风雅者,越会以现实灾难为“硬道理”贬评人文领域;另一方面,则如我们的现代汉语前人在剧变中失语——这种失语不是沉默,而是顺从于一般化,因为与旧的修辞断裂,又未形成成熟的现代知识,早期的艺术探索性在经历国家与个人生活的剧变,并充分体会了个人的微弱渺小后,不得不让位给令人同情的语言一般化,所以不尽是政治打断的结果。这种一般化,也会降临于我们。
如今,说过的常识不得不再说一遍,做过的事不得不再做一遍。同时,光阴匆匆,一代人消逝,消逝于一般化或一般化的专业理论化形式之中。一种不断的批评是,在艰难时世提出艺术主体性,不仅是虚幻的,且是不道德的。听到这样的话时,我脑海里有时就会浮现出,戈雅在自己的帽沿上点一圈蜡烛作为照明,绘制“黑色壁画”时的形象。这是一个在死结时代面前的非理论的形象。

戈雅画作《巨人》。
如今,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死结,同时也处于世界剧变之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也许是比我们通过一点点知识,比目前所能估量到的程度,波及影响面更为巨大的人类命运转折。谁也不能够自以为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人道主义,平等主义,人性光辉,对“热点事件”的那种诗人之审慎沉默,等等。
这些陈词滥调的一切,长久以来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着恶得以通行的贫乏性。一个三角形是:其一,恶的程度,会比我们认为的更加匪夷所思;其二,与此同时,无数人在死去,死亡也盯视着每个活着的人;其三,自命为还将继续创作和思想者如果能活下去,应就此工作于心灵结构的转变。这三者,构成一个简单的并且越来越清楚的三角形,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绝对命令。奥登在《诗解释》中说,“总体战”,“在死者与未生者之间进行”。
需要以福柯式的耐心,进行精神性的追问
新京报:现在,自己在写作诗歌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王炜:我曾一度认为——有点模仿维特根斯坦的意思——“一般的诗”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却又发现想要去做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诗人的困难,应当放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去认识。对我来说,主要困难就是对抗中文写作内在的失败性。
迄今仍然匮乏的,是三十年以来一系列公共事件,作为精神事件的认识。精神事件,常常退化为运动史。在每次公共事件中,口述史、新闻报道所代表的现场记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想要进一步追问并给出精神性回应的人们,至少有两点需要自律:
其一,不把现场记录仅仅理解和利用为还原论的工具,以此,将其他可能性规定在一种平庸现实主义中。平庸现实主义易被认同,但也易于被收割。其二,不应把苦难中的讲述当作自己失控抑郁的燃料,于是想要戒断时,就会屏蔽那些本该继续聆听的讲述。第二种情况,是对苦难之声的一种私欲,是对苦难之声所打开的那种本应被珍视、应被不断保护的公共性的扭曲。
对于苦难中产生的讲述,文学写作者们有古老的倾听责任。亡灵的人体旋风,因为来到地狱的但丁而悬空暂停,对后者讲述自己的惨事,后者仔细聆听,尽管会因此晕厥。对苦难之声的耐心,不仅是“不评判”——我看到也有文学爱好者对当下事件中的口述和文字记录的抵触性评判——而且,需要一种福柯式的耐心。福柯的言论常常被引用,但是,我们具备福柯那种档案员的耐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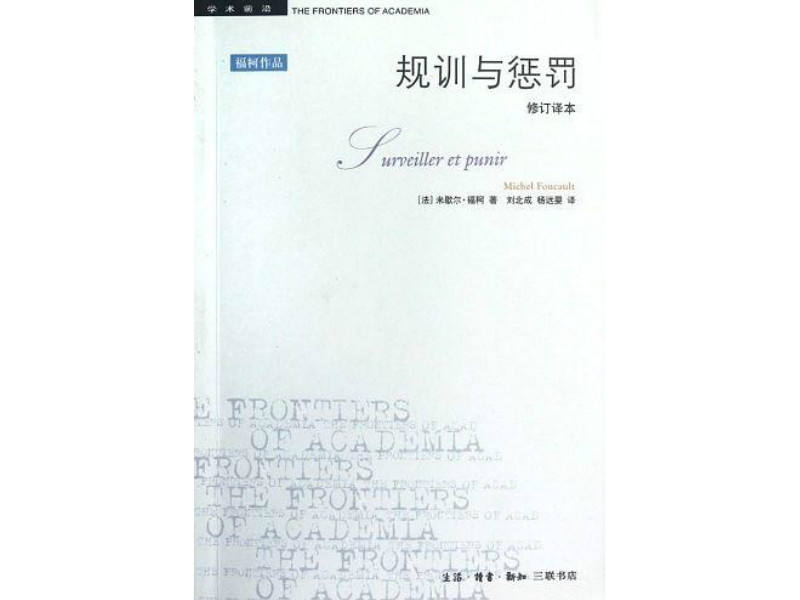
《规训与惩罚》,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
面对苦难中产生的讲述,写作者的责任,首先不是去迅速转化写出点什么,而是在于,始终帮助其真实性能够区别于可被收割的现实主义材料,帮助它显现在与后者分裂是必要前提条件的真实性之中。如果,试图理解和思考一桩划时代的、意味着经验之巨大分裂的事件的人们,只是将其锚定在还原论和某种固化的情绪中,这不仅是它最失败的部分,而且,他们也参与造成并巩固了这种失败。1980年代末以来,我们作为写作者的失败,也是从那些已成往事的事件的失败那一刻开始。失败,延续至今。
席勒为“三十年战争”给出了《华伦斯坦》。这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写作者通过把问题经典化,从而规避现实的借口。促使席勒产生《华伦斯坦》的那种心灵动力,是写作者唯一可以在中文写作的内在失败中自我救赎的途径。
认为自己和坏语言有区别的写作者们,也可不急着写出什么;不妨在此时期,省思自己使用的语言(以及同这种语言相依附的思维方式)与这场溃败的关系是什么,与中国死结的关系是什么。中文写作的内在溃败,极为深重。这种历史性的溃败,若以较晚近的时间点为例,可以从1980年代末的失败开始,延续到我们身上。以如今这场灾难为分界,和以往的“文学场”断绝,这个瘫痪于地狱中的领域也许还可以“有所作为”。
新京报:疫情期间,对你冲击力最大的事件是哪一件?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什么反思?
王炜: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无法用“最”来排序,不能计算,不能用来比赛谁的见识更加高明的共同哀痛。对我的“冲击力”是和每个人一样的,比如,我们都在这场灾难中看到的现实生活真相对每个人的冲击,而且是一种死亡冲击。尽管,其实都是已知之物:一方面,应被反思之事其实都已经在现代智识中被反思过了;另一方面,已知而不能改变,就还是不知。2012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哲学家柄谷行人的一次反核演讲在今天仍具有直接的意义:
“当局和媒体都做出一副好像已经解决了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他们从一开始就隐瞒事实,装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成功了,很多人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希望相信这是真的……即使我们想要忘记,或者即使真的忘记了,核电站的阴影仍旧会执拗地保留,永远地持续。这正是核电站的可怕之处。有人也许会说,即使这样,人们还是会顺从地听从政府与企业的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日本人’则客观上,物质上地终结了。”
新京报:最想对诗歌写作者说些什么?
王炜:惟愿写作者们,可以和官方的或间接官方的“文学场”断裂,回到“地下”。不用听“意见爱好者”和外行的训诫,不论柏拉图式的还是阿多诺式的。勿忘“知性乃道德职责”,以及——最重要的——勇敢去写。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
王炜:我相信,凡是读书写作者,都会继续读和写着他们在人生中一直读和写着的那些东西。
采写丨宫照华
编辑丨徐伟 安也
校对丨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