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马克·里德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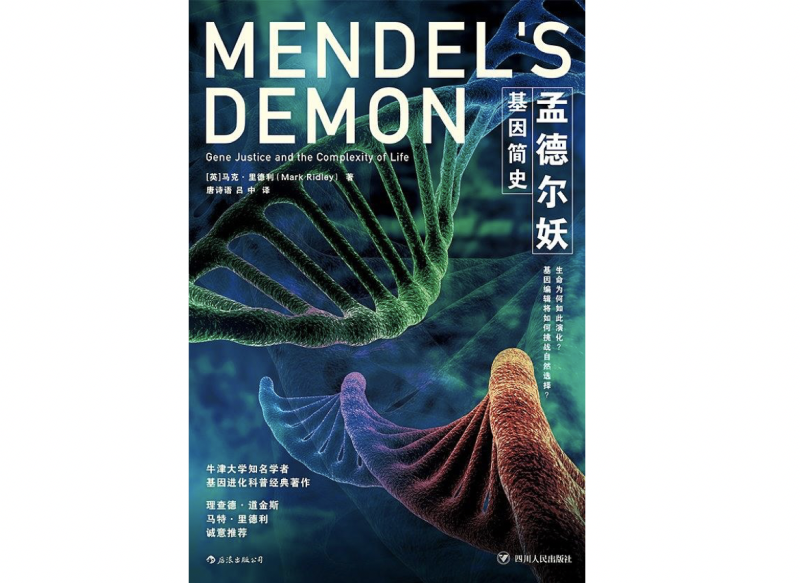
《孟德尔妖:基因简史》,[英] 马克·里德利 著,唐诗语、吕中 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
自然选择如何对抗人类的不良基因?
文明的进步,或者财富的增长,已经削弱了自然选择对抗基因错误的两种方法。医学技术和在富裕型社会中整体而言较高的生活水准,意味着携带有基因突变的人相较以前更不容易因此丧命。富裕型社会中,家庭规模的差异比传统型社会要小,这使得携带突变的父母和不携带突变的父母生育的后代数目可能一样多。但就算把这两个因素推到极致,即所有的家庭都只有两个孩子,并且每个人活下来的概率都完全相等,自然选择可能依然不会停下来,因为它还有另外两个途径来对抗那些不良基因。
首先,自然选择可以作用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也就是远远早于出生的时候。在一个生命周期中,一个世代会繁育下一个世代,它起始于卵巢和睾丸内那些最终会发育成卵或精子的细胞。这些配子在之后的过程中,精子会使卵细胞受精。接着,受精卵发育成为胚胎,然后是胎儿。在母亲的子宫内发育9个月后,小宝宝就会出生并最终长大成人,开始生育下一代。自然选择可以在这个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清除那些突变的基因。相比之下,医疗主要是在出生之后才会起作用。虽然在胎儿阶段也可以进行治疗(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我们把关注的阶段从出生一直推到刚刚受孕时,医疗所起到的效果大体上是不断减弱的。随着来自医疗的影响不断减弱,自然选择的作用就不断增加;另外,在生命早期阶段,自然选择可以作用的范围更广,因为这个时候有更多潜在的处理对象。
如果我们以一种回顾的姿态审视生命周期,从成人到小孩,最后再到胎儿,会发现个体的数量是不断增加的。每一个发育成小孩的受精卵,背后都对应着大约四个发育失败的同伴。但是,这个数字在进入到配子阶段后就开始飙升。卵细胞在受精前的最后一刻可以在一众候选的精子中进行选择。卵细胞被包裹在一种叫作“透明带(zona pellucida)”的黏胶状物质中。通常情况下,会有好几个精子成功进入到这一区域,但只有一个能成功融入卵细胞的细胞膜并完成最后的受精。每一个成功进入透明带的精子背后,都有数亿个精子在女性的生殖道中被降解或被排出体外。此外,还有数以亿计的精子甚至都没能走到这一步。在雌性配子中,虽然自然选择的作用范围没有雄性配子这么广,但依然不可小觑。女性最多时可以携带五六百万个卵母细胞(oocyte,正好处于最后一次减数分裂前的细胞),但其中只有数百个发育成了卵细胞,其中至多十个左右可以最终成为小孩子。一百万个卵母细胞中,只有一个可以“修成正果”,其他的999999个都是失败的。
不用怀疑,在生命早期很多基因的灭亡都是非选择性的,和这些失败的早期胚胎、卵细胞或精子的基因构成无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选择在这些阶段中软弱无力。在之后的生命周期中(如孩童时期或成年时期)出现的死亡现象,非选择性死亡所占的比例可能更大。然而,虽然选择性死亡在生命早期占的比重较小,但是自然选择在生命早期起到的作用依然比晚期时更大。
怀疑论者可能会认为自然选择无法作用于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原因是在这些阶段只有极少数基因被开启。在自然选择能够挑出这些有缺陷的基因版本之前,这些基因必须被开启并且对细胞或机体产生影响。自然选择移除错误的方式,就好像一个人通过观察经文读者的行为而非查看经文本身评价这段经文的准确性。要想找到经文中的错误,你可以逐字逐句地通读这一段经文,并把它和原来的版本比较。在DNA中,这就是校对酶和修复酶在这些基因被用来构筑机体之前所做的工作。另一种方法是,你可以看一看这些经文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你不需要去读它,只需要看看经文对它的读者有什么影响就行,然后销毁掉那些产生破坏性后果的经文版本。这其实就是自然选择所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方法只对你进行观察时正好被表达的那一部分经文手稿有用。如果手稿中有一部分指令是有关周一的行为规范,另一部分是有关周二的行为规范,那么你在周二的观察就不可能用来检测前一部分指令中的错误。如果卵细胞中大部分的DNA指令都处于静默状态,那么你就不可能通过观察卵细胞来找到突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有多少基因已经被投入使用了。

我们对胚胎中基因表达的比例有一定了解。在胚胎和胎儿的某些阶段中,大约60%的基因很可能已经得到了表达。这其中包括了编码细胞基本运行的全部基因,以及负责机体总体运转、协调的基因和指导发育过程的基因。胎儿在其中任何一个基因上出现突变都更有可能夭折。受孕成功后,大约有80%会在出生前流产,这部分反映了自然选择的作用。在胚胎中被表达的这一部分基因,是自然选择可以进行详细盘查的上限。比如说,许多控制视力的基因在胚胎阶段就必须要表达了,因为在出生的时候眼睛是已经构建好了的。但是,我觉得携带有视力缺陷基因的胚胎并不会比拥有完美视力的胚胎更容易流产。这些基因只有在出生后才能被检测到,尽管它们在那之前就已经被表达了。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自然选择被削弱的例子中,里面的基因都能影响某种在出生后才显现的技能,想来这也是挺有趣的。总的来说,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自然选择可能会作用于相当一部分(但不会是全部)基因。
随着我们把关注点往前推移到精子和卵细胞身上,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越来越少。我们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在那些发育成卵的细胞中,有的突变被剔除掉了:早期细胞中的突变比最终受精卵的要多。我们还不清楚卵巢到底是如何探测到这些突变细胞的。此外,我们还有证据表明携带有突变的精子成功率更低,我们同样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淘汰掉的。我们的头号怀疑对象包括女性生殖系统的某些特殊构造。这个系统以对精子不友好著称,总想着用各种手段捉弄这些历尽艰险的拜访者—拌网、陷阱以及放在门顶上的水桶—所有这些,其目的都是令人费解的,有待于生物家进一步研究。它们很可能是在测试这些精子的基因质量,当然也可能不是。
在睾丸和卵巢中带有缺陷的精子或卵细胞,可能在没有被直接检查DNA或基因根本就没有表达的情况下被清理出去。让我们回到那个经文比喻中来。你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升华,因此来到当地卖《圣经》的商店购买几本经书。店家给你提供了不同的版本,但你碰巧知道其中某些手抄本是在和往常一样静谧的修道院中完成的,而另一些手抄本在制作时,抄写员可以听到外面走道上高跟鞋发出的“嗒嗒”声。也许你可以在不亲自试验,或者不拿去和原版对比的情况下猜出这本经书是属于哪一种类型:书上可能写有日期,而你恰好又知道修女拜访修道院的时间;或者,书页边缘上的涂鸦可能给你提供了线索。你会让你不朽的灵魂相信这一本经书吗?我相信你会去买另一本。我的意思是,卵巢也许有能力分辨出哪些卵母细胞经历了容易分心或者感到紧张的环境。对于那些从事“护理”的细胞来说,它们有很多的细胞可以选择,因此只要对某个卵母细胞有“一丁点”的怀疑,把它们扼杀掉就是合理的。这种类型的自然选择因此可以作用于那些和平均水平相比更有可能携带错误的配子前体,进而让那些最后沿着输卵管落下的卵细胞携带上比原来数百万个细胞准确度更高的DNA。
医学的进步对作用于生命早期阶段的自然选择几乎没有影响。新的生殖技术可能在未来会对此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我在本章中只考虑现在已有且广泛传播的医疗手段。我想要说的是,虽然部分生殖治疗技术可以让有缺陷的早期细胞成功繁衍,但在实践中一般还是倾向于选择“好”的胚胎。未来的生殖技术更可能是去协助而非削弱对抗基因错误的自然选择。不管未来到底如何,文明发展到现在还是几乎没有削弱在生命早期起作用的自然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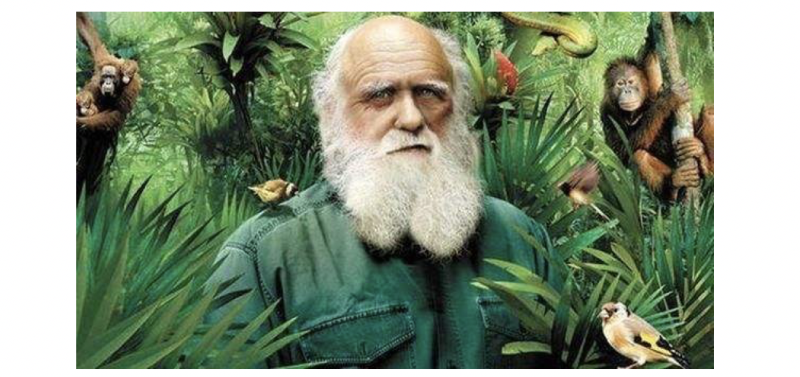
基因的质量,如何影响人类的婚配决策?
自然选择对付不良基因的第四种方式是影响它们是否能够成功结婚并组成家庭。(“结婚”一词在这里应当以一种更广义的方式理解,也许会给人感觉有点老套。它在这里指的是配对,有没有结婚仪式都行。同时,它还意味着生育:结婚的就生,不结婚就不生。“已婚”在这里指的是“配对的繁衍者”。)这和我们在第五章中提到的性选择是一种类型。在有性生殖的物种中,如果基因质量高的个体更容易被选为配偶,那么针对不良基因的自然选择就可以得到加强。在那一章中,我们提到了青蛙的例子。青蛙实行的是多配偶制,和人类的一夫一妻制完全不一样。携带有不良基因的雄性青蛙生育的可能性较小,因为雌性青蛙不喜欢它们发出的叫声。类似的过程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可能男性和女性都要面对,因为我们实行的主要还是一夫一妻制。在人类中,男人挑女人,女人同时也挑男人,女性要竞争男神的宠爱,同时男性也要争夺女神的芳心。女性个体身上的坏基因同样可能像男性个体身上的坏基因一样在婚配市场中败北,虽然可能程度会小一些。
指引我想到基因的质量会影响人类婚配决策的并非简单的外向式推理。在这方面,有一些证据确实能给我带来启发。这些证据很早以前就被人发现了,达尔文在1871年就讨论过。不用说,我将要讲的这些观点就来自达尔文。这些证据是单身和已婚人群的死亡率。早在19世纪中叶,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种特征。达尔文引用了在法国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以及在苏格兰进行的一项研究,两项研究都表明,在20岁到30岁之间,单身男性的死亡率约为已婚男性的两倍。在任何一个开展了类似研究的国家中,都发现了这样的特征,并且在所有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中都存在。一项全方位的综述性研究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发现的所有证据,发现单身男性的死亡率是对应已婚男性的1.8倍,单身女性的死亡率是对应已婚女性的1.5倍。在美洲、欧洲和亚洲都发现了类似的效应。这个效应现在可能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因为人类的婚姻和生育习惯已经改变了。但是,我没有找到更新一些的证据。就目前我们已经有的证据来说,单身是对人类寿命影响最大的一个风险因素。如果你去看这些风险因素的列表,排在前面的就是高龄、贫困、男性和单身。单身几乎和性别为男性或贫穷一样糟糕,在精算学上等价于每天吸一包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中可能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婚姻本身很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健康。结婚后,照顾你的就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此外,你也不需要进行那些在婚前用来吸引异性的行为,它们有些其实很危险。你还可以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享受到合作带来的好处。如此一来,你的状态可能会越来越好。这也意味着,你有两个人需要照顾,因为结婚的人就是那些进行生育的人。对人类来说—其实别的物种也一样,生育会增加死亡的概率。生的孩子越多,你的寿命就越短。尽管生育会增加已婚人士的死亡率,单身人士的死亡率依然达到了已婚人士的1.5到2倍。总之,婚姻是否真的有利健康还是个未知数,但相比较而言它确实有这个效果。

电视剧《性爱自修室》(Sex Education Season)第一季(2019)剧照。
另一个因素是,健康状况不好的人在婚配市场上是被歧视的,而那些单身的人就是这些不够健康的“剩男剩女”。(这里我要讲一个民族主义的段子,这个段子在世界上许多邻国之间都有流行。这个段子我最早是从一个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那里听来的:“当一个苏格兰人穿过边境到达英格兰,两个国家的平均智商都升高了。”这就好比说,每当有一个单身人士结婚,已婚人群和未婚人群的平均健康水平都下降了。)影响人类性伴侣选择的因素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一个被大书特书的因素是“身体的对称性”。身体和面部更对称,也就是左半身是右半身完美镜像的人,被认为更漂亮,在性吸引上也更成功。身体的对称性同样也和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关。“爱美之心”可能就是身体健康的人在婚配市场中得以成功的部分原因。
现在,我们对单身人士较高的死亡率有了两种解释:一是婚姻有助健康,二是健康提高了步入婚姻殿堂的能力。专家们对两种解释既有支持意见又有反对意见,但任何试图排除其中一种因素的研究都没有取得确定性的结果。两个因素都足够有说服力,而且都可以解释全部的观察结果。我觉得这两种因素其实都有作用,但其中只有一个因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相关,即在婚姻上对健康配偶的青睐。我们同时还需要另一条论据,即基因是影响健康的部分因素。有的人失去健康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偶然的环境因素,比如在小时候不小心染上了某种疾病然后一直没有彻底康复:当异性离他们而去时,其实并不是要选择性地针对哪一个不良基因。但是,有些人身体不好可能就有部分基因上的原因,他们的生活选择或者说在婚姻市场上的失败就是自然选择对付不良基因的一种手段。在人身上证明基因的效应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可以说世人皆知。但是,存在影响健康的基因是大概率事件:我们已经知道,基因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健康是一个相当粗略的变量,它可以被很多因素所作用。其实,我们并不缺少证明“基因会对疾病产生影响”的证据。因此,我认为针对不健康伴侣的婚配歧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抗不良基因的自然选择。也就是说,人类的择偶行为也会歧视不良基因,就像青蛙、蝴蝶、突眼蝇和其他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楚的物种一样。
医学,以及它所带来的妙手回春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的光辉成就。在讨论对抗人类不良基因的自然选择时,医学很自然地就成了话题的主宰。但是发生在出生之后,也就是童年时期和成年时期的自然选择,其清除的人类突变可能只占到一小部分。发生在出生后的死亡比出生前的要少得多,而且大部分的基因突变在早期可能就通过降低胚胎质量的方式显现出来了。人口转型同样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大事,但它所带来的进化上的结果却可能具有迷惑性。家庭的规模可能会缩减并逐渐趋同,但我们同时还要考虑那些根本不结婚的人。在现代中产社会中,自然选择可能无法通过制造家庭规模上的差异来实现优胜劣汰,但当我们考虑到是哪些人可以成功生育下一代而哪些人不能时,自然选择的力度可能和原来一样大。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未婚、未育的群体已经大了很多,并且还在持续扩大。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很可能部分、间接、无意识地被基因质量所影响。虽然人口的转型在一个方面削弱了自然选择,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它,而且可能在另一个方面给予了加强。对于人类DNA中大多数的有害突变而言,它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艰难:它们在配子里被杀,在胚胎里被杀,在婚姻市场上还会遭到冷落。文明的发展削弱了某些自然选择,从而让我们身上的部分基因开始走下坡路。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对付最糟糕的那些基因时,自然选择的强度和过去相比基本一样。在财富不断积累的地方,大多数基因并没有往坏的方向发展。
本文摘编自《孟德尔妖》第九章“是时候来说说人类了”,有删节,由后浪出版公司授权转载。
原作者丨马克·里德利
整合丨董牧孜
编辑丨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