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亚光
三年前的今天,2017年4月27日,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因为不堪抑郁症的折磨在家中自缢身亡,留下一部日后引发巨大社会关注的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为此书写的推荐语中称,阅读这本书可能是阅读一份“记录”,也可能是阅读一份“遗嘱”。林奕含年少时持续受到补习老师的性侵,身心始终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数次尝试自杀,在她离世后,她的父母也披露,书中被补习教师李国华侵犯的花季少女房思琪,正是林奕含本人的镜像。她用最精心雕琢的句式,最生动考究的修辞,书写了一段被恶魔摧毁的青春,字字灵动,却字字泣血。

林奕含(1991—2017),台湾作家。梦想是一面写小说,一面像大江健三郎所说的:从书呆子变成读书人,再从读书人变成知识分子。
林奕含离世后,她的经历随着这本小说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台湾,群情激愤的人们声称要为林奕含讨伐“狼师”。在大陆,房思琪的故事也不断激起有关性侵犯的社会反思。然而,除了童年时期的惨痛回忆,用文学写作来记录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本身也给林奕含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似乎成为了另一种堪称自戕的心灵创伤。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心中本应“思无邪”的文学老师居然能犯下“人间最大的暴行”,她痛苦于自己认定为只与美和善相关联的文学居然在性侵害中成为引诱和迷惑少女的工具,她更困惑于自己用文学的方式对这片黑暗的记录,是否也同样沦为这片黑暗的帮凶?在那段于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生前采访视频中,林奕含带着哽咽发问:“文学是否只是一种巧言令色?”
文学曾被陷入痛苦泥淖的林奕含视作救命绳索,却最终让她把自己的命运绑缚。林奕含之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痛苦?承载着这份痛苦,房思琪的故事在当下的社会,依然能引发怎样的回响?在林奕含离世正满三周年之际,我们希望通过走近和体味这份痛苦,怀念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借此反思社会上依然猖獗的性侵现象。
林奕含之问:文学是一种“巧言令色”吗?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阅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并去试着感受林奕含生前所经历的悲痛,必须建立在对“林奕含之问”的理解之上。对房思琪的故事的理解,不应仅仅止于对书中情节的理解,还应该包括对林奕含整个的写作过程:她并非只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记录创痛,更是用文学的方式在拷问文学,并向每一位读者发出一种略带绝望的邀请,邀请阅读者共同去思索困扰她直至生命终点的对文学的困惑。
“文学是否是一种巧言令色?”林奕含之问背后的痛苦是复杂的。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对文学之美居然背叛了真和善的震惊和不解,体现在书中,则是作为语文补习教师的李国华,满腹经纶却能频频侵犯年少的学生,夺走她们生活中的光亮。林奕含的文学天赋和对文学虔诚的信仰,在那段生前的采访中显露无疑。而她的化身房思琪,喜欢“读波德莱尔而不是《波德莱尔大冒险》”,“第一次遇到砒霜是因为包法利夫人而不是九品芝麻官”,同样对文学有着超出同龄人的敏感,也深深沉浸于文学的美。这种对文学之美极致的憧憬,被“李国华们”在暗无天日的性暴力,以及暴力发生现场对诗词歌赋、文坛典故的使用击得粉碎。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著,磨铁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老师看上去是很喜欢她的模样的意思,微笑起来的皱纹也像马路上的水洼。李国华说:“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的中国人物画历史吧,你现在是曹衣出水,我就是吴带当风。”
他只答了四个字:“娇喘微微。”思琪很惊诧。知道是《红楼梦》里形容黛玉初登场的句子。她几乎要哭了, 问他:“《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他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 (摘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在强行与房思琪发生关系后,这样的对话常常出现。文质彬彬、华美绮丽的辞藻与性侵的连接,文学之美与恶行的并置,撕裂了房思琪和林奕含对于文学的憧憬,也成为林奕含之问背后的痛苦最重要的根源。
除此之外,这份痛苦还指向林奕含的一种自我怀疑。在采访中,林奕含曾经哽咽地向记者提到,房思琪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少女遭到性暴力的故事,也是一个少女“爱上了”她的补习老师的故事。这显然并非承受着性侵阴影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的林奕含真心所要表达的意思,而是透露出她内心中深深的矛盾。《新京报书评周刊》曾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林奕含在描写李国华性侵场景中使用的大量细致的比喻反而使得李国华的欲望和房思琪的抗争变得“暧昧而难以分明”。
林奕含说:“我已经知道,联想、象征和隐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这句话并不仅仅是在形容李国华在进行施暴时对文学词句的挪用,也是对她自己写作的反思。正是在这些精美而又引人浮想联翩的文学化修辞中,施暴者似乎被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而被美化,粗暴的侵犯与“你情我愿”变得难解难分。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后记中,林奕含也痛苦地自述:“我怕消费任何一个房思琪,我不愿伤害她们。不愿猎奇,不愿煽情。我每天写八个小时,写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泪流满面。写完以后再看,最可怕的就是:我所写的、最可怕的事,竟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性施暴者的残忍行径在文学的掩饰下变得含蓄而暧昧,他们依然逍遥法外,而阴影中的被侵害者却可能被猎奇、被消费。如果说文学之美和道德的断裂令林奕含深陷信仰崩塌的痛苦之中,那么这种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无力感和罪恶感则将她紧紧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夺走。
文学之美是否必然允诺道德之善?
林奕含指出文学在以上两个层面意义上的“巧言令色”,促使我们思考文学之美与道德之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具有超越于林奕含的遭遇之外的普适性意义,恰恰也因为被视为人类文明之瑰宝的文学似乎在相当多样的人类罪行中,不仅并没有发挥教化的作用,反而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林奕含的发问反映出,在她心中文学的真善美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她才会在看到自己喜爱的作家奈保尔竟然有殴打妻子的行径后,心中泛起一阵巨大的伤痛。然而,从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美”和“文学”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学之“美”从来并不必然允诺道德之善。
当李国华在性侵现场用一些文学化的表达向房思琪“示爱”时,似乎出现了文学形式上的“美”和其所蕴含的内容之“善”的分离。然而,历史上的许多文学理论家,都曾经将文学之美仅仅严格限定在“形式”的层面。例如,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就曾经将“写作方式”视为文学的本体。在他们看来,决定一句表达之为文学的并非人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抽取的意义,而在于话语的组织、节奏和音响。而在美学思想的传统中,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形式”也是相当重要的一脉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就曾经指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或是任何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如果要显得美,就不仅要在各部分的安排上见出秩序,而且还要有一定的体积大小,因为美就在于体积大小和秩序”。在这些有关文学和美的形式主义观点看来,文学的美似乎与它们本身表达的内容并不相关,和其内容是否道德更是不同的范畴。
除此之外,也有论者认为,衡量一篇文学作品、一首歌曲、一幅画的美,应该诉诸人的感官快感。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思想家们认为,主张艺术品的美在于形式其实假定了某些先天的形式存在,而只有经验才是一切认识的根据。伯克就声称:“我所谓美,是指物体中能引起爱或类似爱的情欲的某一性质。我把这个定义只局限于事物纯然感性的部分”。这种“美即快感”的观点,林奕含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赞成的,这种对美的认知也成为她困扰的一部分。
不论是“美即形式”,抑或“美即快感”,似乎在这两个对于文学的理解中,文学完全可以是全然“巧言令色”的,从不允诺任何内容的道德性。然而,亦有许多对文学的理解并没有站在林奕含之问的对立面,而是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紧密相连。这种观点的思想内核可以概括为美学上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主张的“美即完善”。英国的新柏拉图派美学家夏夫兹博里就认为,人们拥有一种“内在感官”,可以“从行动、性情、精神中见出美丑”,也可以从“形状、声音和颜色中见出美和丑”,这暗含着一种美丑与善恶勾连的观点。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这种思想在对待文学上的态度中体现较为明显的例子有许多。例如,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就认为,文学应当用来“培养一种丰富的、复杂的、成熟的、有辨别力的、在道德上严肃的反应”。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也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指出,在利维斯等人活跃的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剑桥大学从事文学研究,就意味着“要被卷入此种对工业资本主义最使人平庸化的种种特征所发动的斗志昂扬的、论战性的猛烈攻击”。利维斯等人建立的标准,区隔了“文学”和“非文学”,只有具备“根本的英文性”(essential Englishness)的英文,才配称作文学,这种对于文学的道德功用的看重,与中国自古以来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有着相似的关切。
然而,常识似乎也告诉我们,人们心目中大多数优秀的文学,并非是处于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道德教化两个极端。例如,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之一席勒就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人身上同时具有让感性内容获得理性形式的“形式冲动”和让理性形式获得感性内容“感性冲动”,而二者的统一会唤起与审美活动关联的“游戏冲动”,强调审美活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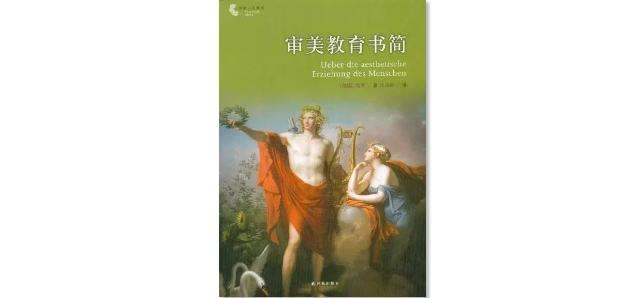
《审美教育书简》,(德)席勒著,张玉能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7月
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中,列出了四个他研究美学史最为关切的核心问题,其中,“美的本质”便首当其冲,他的梳理也向我们呈现,强调美更在于形式、在于快感的观点,和强调美更在于内容的“完善”的观点,两种观点的张力贯穿了几乎所有古往今来人们对艺术作品进行的美学思考。时至今日,这种观点的碰撞也时常发生。引发人们对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思索的作品不只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在书中曾经致敬的作品——纳博科夫的名作《洛丽塔》亦曾经引发许多争议。许多人认为,小说体现出的对主人公——恋童癖亨伯特的理解和同情有违基本的社会道德伦理,对他所造成的伤害视而不见。亦有论者认为,在阅读《洛丽塔》时,应当悬置道德判断,全然用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它。
由此可见,从本体论的层面看,文学的美与道德的善之间的连接非常任意和偶然,从文学中获取审美体验,也就自然不能保证一定能同时获得道德的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可能才是林奕含在追问“文学是否巧言令色”时真正感到困惑的——为什么受过文学熏陶的人,并没有向善?她的困惑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脑中,斯坦纳曾经惊异于纳粹的士兵们读着里尔克和歌德,却丝毫不减施虐的冲动。种种事例都表明,文学之美不仅不能允诺道德之善,同样不能允诺它的读者之善。文学从属性上无所谓“本身”是“巧言令色”的,但是阅读和运用文学的人却可以是虚伪而别有用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林奕含进行的追问是一种我们不忍苛责的“误伤”:她可能“错怪了”她深爱的文学,但这种“错怪”却根源于“李国华们”对文学的扭曲。性侵者不仅伤害了林奕含和房思琪,也伤害了“文学”。
关注性之耻多于伤之痛?
房思琪故事的现实回响
不难发现,林奕含之问背后,是她对文学本身“完美无瑕”的认定。林奕含在生前访谈中表示,自己的书写是一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原本在她心目中完美无瑕的文学却被用来呈现比“大屠杀还要惨烈的罪行”,这使得她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巨大的罪恶感。《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林奕含的这种对文学的极致憧憬与她本人追求自身极致完美的性格相关。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对文学的极致憧憬使得她会不断使用“变态”“不雅”“屈辱”等词汇来形容自己的这次书写行为,最终让这场文学的自救成为了痛苦的深渊。也有许多文章因此痛惜于林奕含不堪重负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认为她如果放下这种对“完美”的苛求或许能够让自己免于一场悲剧。
然而,这种对林奕含因写作房思琪的故事而感到痛苦的归因,过于强调林奕含个体的性格因素,却忽视了在社会结构和文化脉络中性侵危害的特殊性。对遭遇性侵、谈论自己被侵害的遭遇而感到“变态”“屈辱”“不雅”,绝不仅仅是一种林奕含个人因为对文学或是道德的洁癖而引发的“特异性”反应,而可能是广泛存在于每一个遭遇类似不幸的人中。
在《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一书中,学者龙迪通过对一些遭遇家外性侵的孩子们的家庭开展的实证调研,系统研究了性侵害对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伤害。书中呈现的诸多实证研究,都显示出遭遇性侵害的儿童之后往往会罹患PTSD,焦虑、抑郁,不恰当性行为(例如性滥交等)或者性功能障碍。遭遇性侵犯也会导致受害者形成稳定、泛化的内归因,从而产生强烈的负面自我评价和羞耻情绪,进而形成持续的耻辱感。
在尚未对性和爱产生较为成熟的认知的未成年时期遭到性侵害,不仅意味着持续忍受强烈的耻辱感,更意味着可能难以再次面对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林奕含通过房思琪的故事,鲜明地传递出这样的绝望:“她不知道谈恋爱要先暧昧,在校门口收饮料,饮料袋里夹着小纸条。暧昧之后要告白,相约出来, 男生像日本电影里演的那样,把腰折成九十度。告白之后可以牵手,草地上的食指试探食指,被红色跑道围起来的绿色操场就是一个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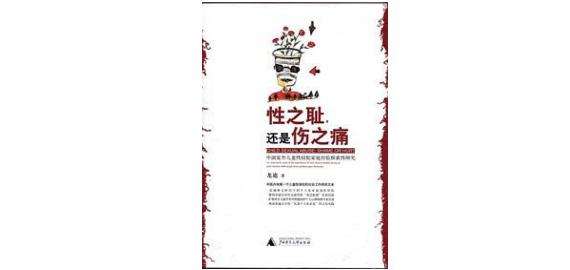
《性之耻,还是伤之痛》,龙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在许多当代有关未成年性侵害的讨论中,人们总是存在对始终坚持反抗且挣扎的“完美受害者”的苛求,未能达到此种要求的受害者经历往往会被合理化为一种“你情我愿”。然而,如上述研究和房思琪的故事所揭示的,这种苛求对未成年人显得极不恰当。在近期引发舆论关注的高管性侵女童案件中,《财新》的报道引发的争议和批评也正与此相关。正如《澎湃思想市场》近日的一场圆桌讨论中指出,即使未成年人也可能对施害者存有欲望,但这种欲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在尚未形成对性欲的至少是社会话语意义上的成熟、自觉的理解前,这种经历也会在日后成为对未成年人深刻的创伤。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因性侵带来的持久羞辱和自我嫌恶,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例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曾经在专著中提及的广泛存在于以日本为例的各个国家社会中的“厌女”文化,同样深深影响着性侵害过程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
上野千鹤子认为,男性之间存在的相互亲近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使得他们必须将自己确立为具有男子气概的主体,而将女性视为被操控和被凝视的客体。体现在性暴力犯身上,则是他们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的他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依赖、长久持续控制对方,摧毁对方的自尊心、对他人的信赖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且还希望对方能够产生主观上的情愿。性暴力中呈现的欲望并不是对任何一个具体女性的“爱”,而是对女性作为符号的占有与操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中李国华和其他老师的谈话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房思琪之外,李国华还强行与“饼干”、“晓奇”等多个女学生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在这些老师们看来,只不过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征服”。
而“厌女”文化对性侵受害者产生的影响则更为隐秘和深重。在上野千鹤子看来,厌女文化同样会导致女性的自我嫌恶,根据男性的主体凝视去规训自身,这并不仅仅体现在性侵犯之中,而是深入到种种社会关系的面向里,房思琪的故事中的另外一名重要的人物许伊纹所承受的家庭暴力即可以被视为一例。这种自我规训与为许多学者所讨论的东亚文化圈中普遍存在的包括“贞洁”等在内的许多传统观念相连接,深化了遭遇性侵害后受害者所背负的耻感。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遭遇性侵害时常被社会舆论评价为足以“毁掉人一生”的“耻辱”。龙迪在调研中就发现,在她调查的家庭中,父母得知孩子遭遇性侵后,表现出的愤怒和采取的行动多指向对家族“面子”的维护,时常担心自己的家人今后“没脸见人”。她借用学者杨中芳对“应有之情”与“真有之情”概念的划分,认为这些父母对孩子遭遇性侵的应对更多是表现出某种“应有之情”,即基于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下一家人相互扶持的先赋性义务,但这种“应有之情”的履行却阻碍了许多“真有之情”的流露,过于看重家庭名声受到的影响甚至使得家庭总是忽略受害的孩子所需要的情感陪伴。而我们已经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看到,这种对“性之耻”的强调和对“伤之痛”的忽视,并不仅仅存在于龙迪研究的这些个案中。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上野千鹤子著,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
诚然,文化仅仅只是我们考虑性侵害所带来的伤害时应该纳入的一个维度,经济、政治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抵御性侵伤害不仅需要文化观念的转变,同样需要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在日本记者伊藤诗织与侵犯她的新闻业名流山口敬之漫长的斗争中,她就发现反抗性侵犯在日本之所以如此艰难,除了普遍存在的对女性的不尊重,为受到性侵犯提供社会支持的救助机构、法律救济同样十分缺乏。相比之下,如瑞士等北欧国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性侵害救助中心,许多中心设置有两处紧急救助中心的入口;其中一个入口不需要经过等候室,可以不和任何人打照面,直接抵达挂号台;中心的内部,为了保护来访者 的隐私,非常细致地设置了隔断。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及心理辅导,待一系列救助措施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
在救助制度的庇护下,遭遇强奸的人不必再为没能立即报警而百般自责,或承受来自周遭的质疑,也不会被警方以证据不充分、无法定罪为由,推脱责任不作为。制度和社会支持的完善,为降低性侵犯造成的身体伤害和受害者心理上的耻感提供了更多的保证。
由此,应该明确的是,林奕含在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罪恶感和耻感,固然受到她对文学的极致憧憬的影响,但却根源于性侵伤害本身以及她对性侵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被赋予的意义的感知。林奕含对文学的完美想象本没有任何过错,让林奕含的悲剧不要重演的关键,也并不在于让被侵犯的少年努力克服内心的完美主义或者劝说他们接纳自己,而在于包括文化观念、社会支持系统在内的社会环境的改善。

《黑箱: 日本之耻》,(日)伊藤诗织著,匡匡译,中信出版集团·雅众文化,2019年4月
林奕含书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希望世间再无房思琪。然而时至今日,房思琪式的悲剧却依然在反复上演。房思琪的故事堪称一面现实的镜像,映射出许许多多与未成年性侵相关的社会症候。林奕含去世的这三年间,她围绕这本书所展开的追问,也持续激起社会各界对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未成年人性侵害等多个层面议题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林奕含对自己写作的困惑可以得到回答:房思琪的故事,绝非“巧言令色”,而是真正印证了林奕含在后记中提到的那句友人的话:“你的文章里有一种密码。只有处在这样处境中的女孩才能解读出的密码。就算只有一个人,千百个人中有一个人看到,她也不再是孤单的了。”
撰文 刘亚光
编辑 走走 徐伟
校对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