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搅得天地翻覆,环宇震荡。人类面临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无疑是经济和人口全球化的“副产品”——人们在享受前所未有的流通便利的同时,却也制造了不堪重负的世界性灾难。
如今,全球累计确诊人数已逼近500万,死亡人数超过30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影响。而未来危机的彻底解除,也有赖于全球科学界、医疗界等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在此危急存亡关头,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或许有了更深切的体悟。
早在四百年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就写下那著名的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整体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环球同此时刻,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自立于这场灾异之外。
因此,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当下,我们依然关注海外疫情的发展变化,并准备采访一批海外学者和作家,请他们讲述自己的亲身观察和疫期思考。这是一份特殊时期的日常记录和知识共享,也希望他们能为疫情的控制和人们压力的缓解提供智慧与力量。我们以“同此时刻”命名这些采访,第一批将由书评周刊联合中信大方和新思文化推出。
第一期,我们推出的是对马丁·普克纳的采访,他的代表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在2019年被引进中国,获得良好的口碑。这部著作是他在哈佛大学的世界文学通识课的讲稿结集,解读了16部改变世界的经典作品,他关注文字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疫情之前,他原本打算来成都待一个月,但疫情的暴发,让计划搁浅了。对于眼前的疫情,他最担心的是世界的撕裂和对立,也许此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类的团结互助,他希望文学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合世界、增进理解与互信的作用。
采写|徐伟

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美国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戏剧教授。在冷战年代,普克纳出生于德国纽伦堡,先后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和欧文分校就读,在哈佛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他的研究与写作主要集中于世界文学、戏剧与哲学领域,在戏剧、哲学领域的代表作有《怯场》《反对剧场》《思想与戏剧》《革命之诗》等,在世界文学领域的代表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于2019年被引进中文版。
美国疫情大暴发,部分源于虚妄的优越感
新京报:目前,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150万,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美军在越战期间的死亡人数。你认为疫情在美国严重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普克纳:毫无疑问,美国在此次疫情中受到沉重打击。不过,目前世界各地的实际感染和死亡数字颇值得怀疑,因为检测能力有限,以及在死因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所以,在掌握更多信息之前,我不想在国家之间进行太多比较。新冠病毒给所有社会都带来压力,它们揭示了各国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在美国,我们的问题是中央政府过于弱势,我指的是权力结构所导致的弱势,而不仅仅是现任总统的原因。在我们的制度中,中央政府的弱势几乎是必然的,这反映在民众对政府的高度不信任,许多人希望政府尽可能少地去干预他们的生活。这种政治体制自有其优势,但在这样的危机中却是可怕的。
新京报:特朗普总统多次与纽约州州长科莫“打嘴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不能协调一致,是否也耽误了疫情的防控?你如何评价美国各级政府、医疗机构和NGO组织的防控与救治措施?
普克纳:在这套制度体系之下,美国各州州长比许多其他国家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它们能更独立于中央政府,各州是各种防控实验的独立实验室。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系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能很好地运行。
回想起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当然应该早点采取行动,但之所以耽误,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人类倾向于不去相信破坏性的新闻,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文化优越感。当新冠病毒在中国很严重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中国男人吸烟太多,而且空气污染严重,我们这里的死亡率要低得多。不久之后,意大利疫情暴发,他们又说,那是由于意大利人口老龄化,而且,意大利人喜欢在脸颊上互相“残杀”,而我们这里会有所不同。好了,现在我们为这种虚妄的优越感付出了代价。

《文字的力量: 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美)马丁·普克纳著,陈芳代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7月。
应以此为契机,思考人类的共同命运
新京报:在此次疫情中,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社会,都存在大量针对特定种族或地域的歧视,以及相互指责和推诿,疫情引发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空前高涨,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疫情期间的隔离和封锁,使许多全球性的产业链被迫打断,这是否会导致逆全球化?
普克纳:是的,这对我来说是整个危机中最痛苦的一面,在压力之下,人们倾向于责怪他人。我担心这场危机会加深中美之间的隔阂,比如,我的一个德国兄弟,几个星期前,他在阿根廷的一个电影拍摄现场,就遭受了很多歧视,因为当时德国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很高,人们担心会被他感染,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寓楼的人希望他搬出去。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不过,我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会帮助我们再次把人类视作一个单一的物种。我的意思是,无论是通过感染,还是通过免疫,它在生物学层面确实改变了我们。也许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更认真地思考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共同命运。
新京报:你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确诊人数排名全美第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的师生是否已经返校?还是继续实行远程授课?大家能适应这种新的授课形式吗?
普克纳:我们都从三月中旬开始进行网上教学,我昨天在网上上了最后两节课,现在学期结束了。我们在观察疫情的变化,以评估是否需要在秋季继续进行网络授课。因为在学校,学生们住得很近,共用浴室、宿舍、讲堂,大学校园是病毒传播的理想场所。
我做了很多在线教学工作,总的来说进展很顺利,但这只是说课程本身。学生们的生活失去了很多东西,包括课外活动、社交礼仪、课前和课后的闲聊,离家出走的兴奋。因此,即使这些课程可以在网上进行,没有太多困难,但他们的大学经验却少了很多。
新京报:如今,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对周围生活的变化有哪些感受?
普克纳:我已经在家里待了六个星期,只出去过几次。当我沉浸在写作中时,经常可以很多天不出门,所以从表面上看,这对我似乎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大的影响。而且,我很幸运,住在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里,只有我和妻子阿曼达,这里比平时更安静。我们经常做饭,我还开始烤面包,但是这种近乎正常的感觉是有欺骗性的。
我们会通过上网和看电视,来了解外面的情况,这会影响我的感受。我现在会感到害怕,会为我爱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担心,我也害怕失去我所热爱的生活,包括旅行。我原本计划去成都待一个月,但现在恐怕去不了了,甚至可能明年也去不了。对我来说,这一切就像过山车一样,时而沮丧,时而又充满希望。
 《中国姑娘》电影剧照。
《中国姑娘》电影剧照。
新京报:这段时间看了什么书和电影?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
普克纳:我在哈佛大学教世界文学的课程,三月初,我谈了很多薄伽丘和其他关于瘟疫的文本,但随着情况的恶化,我开始有些逃避。我重读了P.G.沃德豪斯的作品,他是20世纪初的一位英国小说家,他以英国寄宿学校和上层社会为背景,写出了一些极好的小说。这些作品里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只有一些非常温和的讽刺,小说用精致唯美的句子写成,它们是令人愉快的创作。我还看了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电影,包括让·吕克·戈达尔的《中国姑娘》,说实话,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位导演还活着。
所有伟大的作品中,都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新京报:在瘟疫蔓延的时刻,许多文学作品被人们反复谈起,比如《瘟疫年纪事》《鼠疫》《十日谈》《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等,你如何看待文学与灾难之间的关系?那些关于灾难的文学或纪实作品,对人们认识和应对灾难有何帮助?
普克纳:是的,文学在帮助我们处理灾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其实这两者经常难以划清界限)都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我们是通过讲故事来理解世界的。这无疑会再次发生。不过,我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些文本,都是在真正的灾难发生很久之后才写的。同样,我认为我们也需要时间,才能讲述好这场危机的故事,无论是通过集体的方式,还是个人的方式。
新京报:你的《文字的力量》谈到许多经典文本对历史的塑造作用,但并没有选择关于灾难的文学作品,如果此书再版,是否会加上一部相关著作?
普克纳:的确,我的书中没有谈到经典的灾难小说。但有趣的是,当我在疫情之下重读这本书时,不禁注意到我所谈论的文本中隐藏着多少灾难。我们可以从吉尔伽美什史诗开始看,这是洪水故事的起源,洪水也发生在《旧约》之中。所以可以说,在《文字的力量》开篇,就写到所有灾难小说的起源。在个人层面,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也是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
事实证明,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包括我为这本书选择的那些文本(这可能也是P.G.沃德豪斯的作品不能算作伟大文学的原因)。如果我现在来写《文字的力量》,我可能仍然会选择相同的文本进行解读,但我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它们,我会更加关注洪水、冰冻、瘟疫、战争,以及这些文本中的所有其他灾难。
新京报:疫情期间,你有做一些日常记录或者写作什么作品吗?特殊时刻的写作,是否有一种无力感或沉重感?
普克纳:我一直幻想着写日记,但从来没有实施过,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不够自律,到现在也没有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当然,有很多类似日记的关于隔离和封锁的叙述,随处可见,我很惊讶它们是如此的相似。相反,我想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正常的写作上,但很难集中精力,我也试着在自己身上“封锁新闻”,但经常很快就打破了。我确实常常感到无力和沉重。
新京报:瘟疫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往往伴随着谣言、恐慌和阴谋论,非理性的言论大有市场,你如何看待瘟疫期间的这种社会心理和言论?
普克纳: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恐惧滋生阴谋。但问题在往更深层次发展,我注意到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如何像专家一样行事,去阅读新闻报道、统计数据、关于最新药物试验的报告,等等。这让我想起一战和二战期间人们的所作所为,把地图挂在起居室的墙上,移动大头针来调整不断变化的前线,收听最新的新闻战报,似乎要变成对战争发号施令的将军。同样,如今我们都在成为业余的病毒学家,那可能不太理想,但似乎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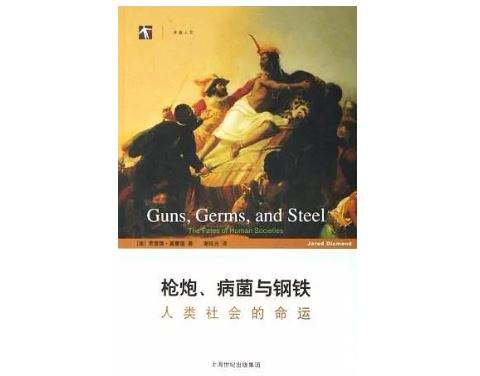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美)贾雷德·戴蒙德,译者:谢延光,版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
瘟疫如何重塑世界结构和社会人心?
新京报: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作品,都在谈论人类与瘟疫之间的关系,这是过去被人们忽视的领域,你如何看待瘟疫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你认为此次疫情会对世界格局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普克纳:是的,我非常欣赏那些书。这场危机的深层根源是我们的农业、久坐的生活方式,使驯养的动物和人类接近。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病毒就是这样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这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几千年前的一个选择的后果。
瘟疫总是带来结构性的变化,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加强了对犹太人的控诉,犹太人被选为替罪羊。由于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瘟疫也带来了新的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改变了世界。从视频会议到在线教学,我们已经瞥见后新冠病毒时代的影子,未来还会有更多变化发生。
新京报:人类面对全球性的疫情危机,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被迫打乱,无数家庭陷入死亡和病痛的阴影之中。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有哪些需要着重反思的问题?
普克纳:从我个人来说,疫情让我觉得死亡比以前想象的要近得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死于其他原因,例如,我父亲在50多岁时死于一次航海事故。但疫情使死亡更接近了,这改变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我不太清楚后果会是什么,但我觉得有些事情在发生,只是现在还不能意识到。事实上,你的问题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新京报:疫情的最终结束,必然要依靠全世界的精诚合作,但目前的国际合作遇到很多阻力,你认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能做些什么?
普克纳:显然,它们需要加强合作,但这很困难。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应该做什么事情上,而是去思考我能做什么。我希望通过教授世界文学,以及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对话,来为加强国际合作发挥一点点作用。
人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人类通过故事来理解世界。我关注故事是如何被建构的,并试着去想,我们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场新冠病毒的故事。这是我对文学的理解,文学或许会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引导人们看到其他的文明,尽管有时候力量微弱。所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找寻书写故事的方式,来讲述此刻的巨大灾难和人们的焦虑。
作者 | 徐伟
编辑 | 走走 罗东
校对 | 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