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德]尼克拉斯·卢曼 译者 | 孙一洲
摘编 | 徐悦东
不言而喻,人类一直以来都要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打交道。然而人们主要仰仗预言的实现,这种实现虽然不能达到可靠的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它都保证了自身的决定不会惹恼神明或其他超然力量,从而确保了与神秘命运之间的联系。当用罪来解释灾祸如何发生时,罪的语义学复合体(对违背行为的宗教指令)在很多面向上都提供了一种功能性等价物。
早在古代东方的航海贸易中,就存在类似的风险意识及其对应的司法机构,这些机构虽然一开始就很难与占卜、呼唤保护神等区分开来,但它们在法律上,特别是在出资人与航海家的角色分工上,仍然直接充当了保险功能,直到中世纪都以此相对持续地发挥着航海贸易与航海保险法规的作用,甚至在非基督的古典时代都缺乏一个完全发育的决定意识。因此,直到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漫长过渡时期,人们才开始言说“风险”。
这个词的词源已然不可考,许多人猜测源自阿拉伯语。人们在欧洲的中世纪契据中找到了这个词,但这个词被印刷出来,似乎首先见于意大利与西班牙。目前尚且缺乏对这个词更详细的词源学与概念史研究,而相对明确地是,首先这个词相对罕见,并出现在迥异的专业范围内。重要的应用领域是航海与贸易。

《风险社会学》,[德]卢克拉斯·卢曼著,孙一洲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
航海保险是有计划的风险控制的一个早期案例,但不仅如此,人们也在合同中发现了诸如“风险与运气”(ad risicum et fortunam...)、“为了安全与风险”(pro secǔritate et risico...)或“如遇风险,一切归主” (ad omnem risicǔm, pericǔlǔm et fortǔnam Dei)等表达,以此协调谁在案件中承担损失。也许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风险这个词并未局限在这些领域,而是在1500 年左右有所扩展。比如西庇奥·阿米拉托(Scipio Ammirato)便写到,谁传播谣言,就冒着被质问其源头的风险(rischio)。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则写道:“没有风险就没有收入”(Chi non risica non guadagna),并遵循古老传统将这一格言与自负、鲁莽的计划划清界限。安尼巴东·罗梅伊(Annibale Romei)则指责道:“不想为他的宗教冒风险(non voler arrischiar la sua vita per Ja sua religione)。”
而在 1545年9月15日卢卡·康提勒(Luca Contile)给克劳迪娅·托洛梅伊(Claudia Tolomei)的信中,人们找到了这样的表达:“去信赖那些异国人甚至野蛮人是有风险的(vivere in risico di mettersi in mano di gente forestiere e forse barbare)。”因为现存语言存有用以表达危险、冒险、偶然、幸运、勇气、恐惧、探险(aventure)等的词汇,人们相信,需要使用一个新的词汇,以说明现有词汇不足以准确表达的问题情况。此外,这个词溢出了其原始语境,比如在引文“不想为他的宗教冒风险”中,因而要根据这些清一色的偶然发现为这个新概念重新奠基并不容易。
在这些限制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眼前的问题在于,只有当人们拿什么下注时,很多收益才会被满足。因而这不涉及成本问题,人们能够提前计算成本,并有可能因失算而损失利益。相反,这涉及决定——当人们希望能够避免损失发生时,人们就像事先能预料那样,事后会追悔莫及。自从忏悔被制度化以来,宗教便试图以各种手段把罪孽变成追悔。
很明显,风险计算关系到忏悔最小化程序的世俗对应物。无论如何,这都关系到在时间过程中不稳定的态度:先如何如何,接着如何如何。那么,这也无论如何都关系到用时间来计算。而在宗教与世俗视角的区别中,也存在着由帕斯卡提出的知名的信仰计算(Glaubenskalkül)这一张力:无神论者的风险无论如何都太高了,因为灵魂拯救被摆上了赌桌。而与此相比,信徒的风险仅是完全多余的屈膝,似乎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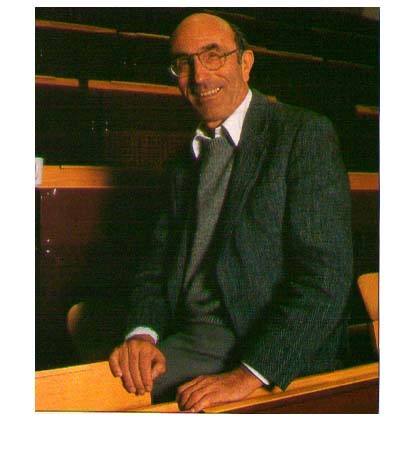
这条扼要的线索给人留下一个初步印象,在背景中驱动着概念发明的复杂问题,仅仅用概念发明并不足以说明。这不仅关系到根据保险的预估进行单纯的成本计算,这也关系到在所有追求有价值事物时所付出的努力中的节制(modestas, mediocritas)与正义(iustitia)这些经典伦理准则。这不关涉理性那似乎永恒的形式,一个理智的静止社会才以这些形式运算,让生命维系在优点与缺点、完满与败坏的混合中,过多的好事也可能会招致恶果。
这不只关系到一种以元规则(Metaregel)表达理性的尝试,要么是优化的规则,要么是折中的规则,即尝试以一致性来理解好与坏的区别,而这些一致性又反过来被表达为好的(适当的)。这也无关于当应用好与坏的公式时,人们用以解决矛盾的烦恼故事。这也不只关系到一个临界的修辞游戏,去发现好的负面和坏的正面。
因此,也要拒斥老派的道德说教,这些说教都只教导我们在各种生活情况下应该如何应对,可在这些情况中时间变迁(varietas temporum)总是与人际间的好坏品质相混合并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当使用风险这一术语时,所有这些老派的方式又一次被强化了,比如在王侯及其顾问的训导或在国家理性(Staatsräson)的概念中。但与此同时,在这一语义学形式的戏剧化中,人们认识到问题点已然与他们渐行渐远。在此引用黎塞留的座右铭:“一件被推测为应该不会发生的坏事,很难不发生。
原则上说,如果想要避免这件坏事,人们就会遭遇更多不可避免的坏事和更为严重的后果(Un mal qui ne peut arriver que rarement doit être présumé n’arriver point. Principalement, si, pour l’éviter, on s’expose à beaucoup d’autre qui sont inévitable et de plus grand consequence)。”其理由可能在于,事情能够出于太多理由而以不可能的方式被搁置,人们无法用一个理性计算全盘加以考虑。这一座右铭在现代技术与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所引发的各种后果上,切入了当代政治争论的中心。尽管黎塞留完全没有使用风险概念,但这还是给予这一概念完全不同的价值。但又是哪些价值呢?
仅靠词源学无法得出进一步的信息。但它也给出了一些线索,首要的便是理性要求陷入了与时间之间日益棘手的关系中。两者都表明,这关系到决定,尽管人们不能充分地认识未来,人们是以决定与时间相连,虽然未来也一次都不是人们通过自身决定所创造的。自培根、洛克与维柯以来,在关系的可行性中,信任的权重日益增加;而人们广泛地接受了知识与可生产性(Herstellbarkeit)相关。
这一非分之想一定程度上以风险概念来自我修正,一如其以另一种方式并用新发明的可能性计算来自我修正那样。看起来这两个概念似乎都能保证当事情被搁置时,人们能够正确地行事。只要人们学会避免错误,这两个概念都能让决定免遭失败。

尼克拉斯·卢曼
相应地,安全(securitas)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当拉丁传统以此表达一个主观上忧虑自由的心境或者特别是在灵魂救赎(acedia)上漫不经心的负面价值时,法语中 sûrete 这一概念的意义则是客观的安全(接着又补充了具有主观含义的securite):仿佛在面对一直不确定的未来时,必须找到确定的决定基础。这一切让能力的领域与要求都大大延展了,而传统上宇宙论的限制、存在的恒定与自然的神秘,都被新的区别所取代,可这些区别又陷入合理计算的领域。迄今为止,人们对风险的理解都诉诸于此。
如果人们质疑这一对理性化传统的理解,便会得到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尽可能地避免损失。因为这一最大化受到行动可能性的强烈约束,人们必须容忍行动,而这就意味着“冒险”,只要对损失可能性的计算与可能发生的损失值看起来有理有据,冒险便会造成原则上可以避免的损失。
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还会通过损失值与损失可能性的乘法来弄清风险。换言之,这关系到理性行动领域的控制伸展,这也非常类似于在经济中,那种没有充分利用理性行动的机会,只用自有资本工作并从不借贷的经济行为。出于这些目的,便足以根据不同决定的结果采取不同的利用功能与可能性分配,而决定自身则根据其结果的不同被描述为冒险的。一个从这一点出发的风险概念是可有可无的,并在这一理论计划中完全无处安放。
那么理性化的传统也有足够的根据,而在这个层次上去反驳它也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在如今的条件下,避免风险便意味着避免理性。尽管如此,还留有一丝隐忧。人们普遍指责理性化传统,并未看到其所未见之物:“……未能考虑到在表述问题的方式中固有的盲目(failing to take account of the blindness inherent in the way problems are formulated)。”
但如果人们想要观察理性化传统如何观察的话,则必须摈弃其对问题的理解。人们必须保留这个问题,却要尝试理解其不能看到其所不能见之物。人们必须把理论转移到二阶观察的层次。然而,这便提出了概念建构的要求,而无论跨学科的讨论语境还是词源学或概念史都不足以引出一个充分的表达。
作者 | [德]尼克拉斯·卢曼 译者 | 孙一洲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丨董牧孜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