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孙佳雯
1985年,被誉为“燕园三剑客”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名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论文,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挑战曾经依附于政治史的文学史叙述,要求把文学史重新还给文学。上世纪九十年代,黄子平转向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系统性研究和重读工作,在香港内地两地辗转,他著名的《革命·历史·小说》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版。之后这本书几经改版,从繁体字版到洪子诚作序版再到简体字版,一本书变成了四本,《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才得以与我们相见。
 《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黄子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
《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黄子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月版
近日,黄子平携新书《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与洪子诚、刘欣玥、李超宇、李浴洋共话当代文学的形式与历史。
灰阑中的呐喊
在地上用石灰画一个圆圈,古代称之为“灰阑”。包公断案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案子,两个母亲争夺一个孩子,找包拯要一个裁决,于是包拯在地上画了一个灰阑,将孩子置于其中,让两个“母亲”各拉住孩子一个胳膊,谁先将孩子拉出灰阑这个孩子就归谁。争夺开始后,亲生母亲不忍看自己的孩子因被拉扯啼哭,撒了手,于是英明的包大人将孩子判给了放手的母亲。这个故事后来被布莱希特、莫言等著名作家都重新讲述过,而黄子平这本书的标题,其实来源于西西改编版《肥土镇灰阑记》。在这个作品中,那个在灰阑当中任人摆布和撕扯的孩子,突然要开口说话了,他滔滔不绝的心中所想让包大人自以为聪明的断案方法瞬间变得愚蠢而可笑。

《灰阑记》
黄子平对这个情节十分赞赏,也很快敏锐意识到,这个灰阑当中,这个微弱的声音能够改变灰阑外的世界吗?或者它能够帮助这个弱小者挣出灰阑吗?由此推而广之,黄子平发现灰阑无处不在,我们所有的叙述都囊括在这样的语境中,灰阑中的孩子说话,可以解释为对权威言论的一种反注释,一种消解权威言论的尝试。但即便是如此英勇的反注释,也会被纳入无边的大注释圈中消失得无声无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写作者,其叙述似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突破第一层的小的包围圈,但无法突破更大的包围圈,正如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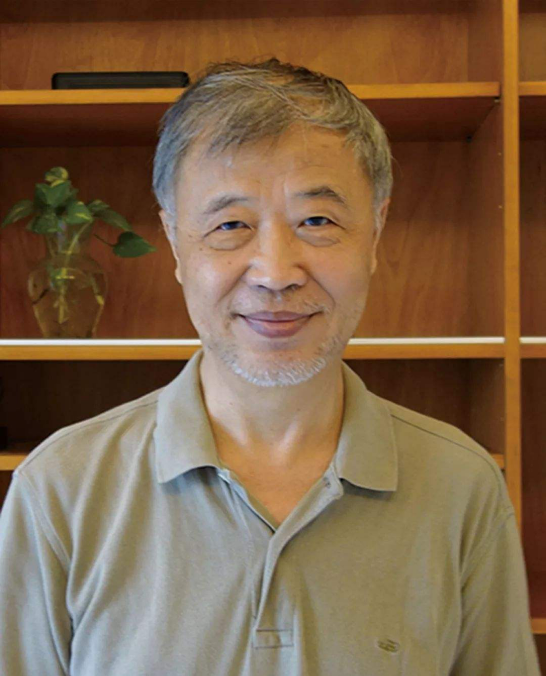
黄子平,广东梅县人。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中山大学(珠海)讲座教授,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著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幸存者的文学》《害怕写作》《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远去的文学时代》等。
如此看来,黄子平的叙述观似乎有些悲观,但李超宇认为黄子平并未因此放弃叙述。在解读鲁迅《故事新编》时,黄子平将有一节题为“叙述以反抗‘绝望’”,可视为他的自况。黄子平说鲁迅“比别人都更充分地把这一‘叙述使命’跟个人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从而借此在语言异化和历史困厄的双重危机中,探询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生存的境况。叙述成为静夜中的一种挣扎,成为‘明知前路是坟而仍是走’的写作实践,鲁迅的写作正是对这一个大叙述圈的反抗。在《补天》中鲁迅写下了杀到女娲尸体旁的一支军队,他们恬不知耻地自称是女娲的嫡派,试图掌握对女娲的阐释权,但是这群人却被鲁迅在小说里先行嘲讽了一通。”
黄子平感慨道:“一旦故事的阐释行为被事先编入故事时,后世的故事阐释者便无法逃脱故事对他的永恒嘲讽。”这也是黄子平写这本书时采用的方法,把20世纪50到70年代的长篇小说对历史的建构和阐释行为,都一一暴露在读者面前,用作者的创作谈结构其创作,为作品改写、遮蔽、删削的复杂历史图景作出注释,扯宽文本缝隙,让读者看到性、宗教、江湖等概念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微妙体现。
《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反复提及从灰阑中突围的渴望。这种突围遍布二十世纪文学的各个节点。茅盾未完成的著作,与那些表面上结构完整的文本相比,“反而更铭记了我们在这天翻地覆的年代里安身立命的悲剧性挣扎”。而以莫言为代表的颠覆性叙述,则让“‘土匪’从意识形态的兵营里反出江湖,一时间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刘欣玥看来,人生无往而不在灰阑之中。与鲁迅“铁屋中的呐喊”涉及到的先觉者如何发声,唤醒沉睡在铁屋中的旧中国儿女这一命题相比,黄子平所创作的“灰阑中的叙述”的概念虽同样也是发出声音,姿态却变得更加温和,亦不失清醒和坚守,因为当下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渠道,但我们很容易被更强势的声音所魅惑,进而放弃思考。就像流传千百年的《灰阑记》的故事一样,大家往往只看到断案的包青天,只看到两个争夺子女的母亲的申诉,却很少看到那个被争夺的孩子也可以自己发声。所以如何找到一个全新的框架,可以让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发出声音,也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从文本中找寻证据
几经改版的书和洪子诚的序都源于巧合。1997年,黄子平在一个聚会上见到了洪子诚,赠他两本书,一本是《边缘阅读》,一本便是《革命·历史·小说》,后者对洪子诚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引用、延续了黄子平书里的观点,他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认识,也是受到黄子平的启发。
洪子诚将这种影响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中讨论的,革命战争从19世纪末到现在是如何影响到文学,和人们的心理、情感和语言的;其二是在文学研究和批评方面,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文学文本里说了什么,更要关注怎么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将形式和内容沟通起来,使得内容是一种有形式的内容,形式也是一种有内容的形式。这两点也奠定了《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作为文学研究批评重要的参考书的地位。在洪子诚眼中,和黄子平、戴锦华这一批年轻人的交流能给他无限启发,如果说王濛这一代作家学者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句号,那么年轻一代学者留下的则是一个能引起他思考的问号。
而对于黄子平来说,洪子诚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他曾回忆自己1982年至1984年间在北大中文系跟随谢冕先生攻读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上过洪子诚的当代诗歌专题课。黄子平激动地发现,在北大中文系这样一个俗称“老夫子系”的地方,居然也有老师带着大家读那个时代最先锋、最前卫的诗歌,北岛、多多、舒婷、顾城这些先锋诗人,都在他们的阅读名单里。

洪子诚,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人合著有《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两意集》等。
洪子诚的第一本书《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和《灰阑中的叙述》都讨论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的研究,前者有一章“对历史的叙述”,专门处理革命历史小说,虽然沿用了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概念,但具体的分析方式却是将这种小说类型与它的写作实践事件化,而非像黄子平一样从文本或形式层面分析来展开讨论。他对话的文本十分具体,一个是革命叙事下的文学史,包括朱寨先生主编的思潮史,另一个是上海的“重写文学史”讨论里与当代文学有关的部分。对此,洪子诚表示这是因为他亲历过五六十年代,许多书中探讨的问题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因此他希望给这段亲身经历过的的历史一个解释。
黄子平曾说,“所有的证据都在文本里面”,他对文本的态度是既信任又不信任,与同代学者直接用历史的材料和批评的材料不同,他更倾向于反复阅读,窥探出文本的秘密。对此,黄子平自嘲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鼻敏感问题,让他无法去图书馆翻阅那些堆满了灰尘的书籍,只好退到文本里,抓住文本不放,从而获得一种对语言的敏感。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界还缺乏对文本细腻解读的意识,研究者们过早地放弃了“新批评派”的细读方法,忽略了只有反复阅读文本才会有心得体验。但他也强调,不能对文本解读过于自信,一旦文本离开了语境,离开了它产生的文学生态机制,就有可能把它孤立起来,变成一种一厢情愿式的解读。
写作是一场自我精神治疗
关于“疾病的隐喻”不止一次出现在黄子平这本书里,包括那篇影响巨大的《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和对鲁迅的《故事新编》的讨论。在2001年版的后记里,黄子平把这本书称为是一个自我精神治疗的产物,是对少年时期积累的阅读积淀的自我清理,这同样也隐喻了疾病。黄子平曾道,2001年版出来后发现有许多和他有同样迫切需求的同病者。他至今记得1971年的某天,在大片的胶林里,全团人一起听文件的传达,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人们甚至可以听到橡胶树的叶子掉到地上的声音。他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自明性世界的丧失”,原来所有事情都是不用证明的,这个世界因为过于明白而在这一刻丧失了。
对他而言,这个自明性世界的形成跟少年时期对革命历史小说等的阅读有关。他曾以为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历史是什么,现实是什么,世界是什么,也能借此判断自己的存在。但是在这样一个自明性世界丧失的时候,“自我”和客观存在的世界都被打上了引号,两者之间恍惚失去了联系,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开始出现,于是精神分裂者成了一个天然的现象学家。但跟现象学家不同的是,现象学家会摘掉引号,这样他又就可以回到自明性的世界里,而精神分裂者不知道,也没法摘掉那个引号,所以变成了模模糊糊的、浑浑噩噩的状态。
黄子平说概括他们那一代人最后的一个总结性的经验就是北岛的那首诗《回答》。人们渴望一个肯定、积极的答案,但北岛说“我—不—相—信”,他怀疑的并非某个特定的东西,而是自己所处的世界的全景,这种怀疑正是黄子平常言的“病”。在他看来,笛卡尔是最早的一个精神分裂者,“我思故我在”本质是怀疑一切,怀疑到最后只剩下一样东西不能怀疑,即“我正在怀疑这件事”。每个精神分裂者都需要找办法去寻回自明性的世界,把引号摘掉,这便是用哲学的说法来讨论精神治疗,也是为什么黄子平将自己的写作称为一种精神治疗。
对于这种自我精神治疗,李超宇也有自己的困惑。革命历史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阅读热潮,他好奇这种小说情感动员的方式究竟产生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而当下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是否也和情感动员能力的匮乏有关?对此,黄子平回忆起《红岩》刚出版时引发大家排队购买的热潮,这本讲述了黑暗与光明搏斗的故事的书在当时引发的讨论可说是盛况空前,而当他做研究时,他才发现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像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讲的,是“生产”或“制作”出来的。而黄子平重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后,他开始将“生产”与“分配”联系起来,开始思考情感动员起来后该如何分配。用法国思想家朗西埃的说法,这是一种“可感性的分配”。也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可以感知的,什么是不可以感知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句子、文本,什么是噪音、杂音。李超宇所提到的文学边缘化现象,正是新的分配形态出现带来的问题,在当代的艺术、文学或者其他媒介中,这种分配状态是怎样操纵、怎样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都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
黄子平每次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读,都是对当下焦虑的回应。《灰阑中的叙述(增订本)》原版诞生的20世纪90年代,黄子平在讨论革命、土匪和英雄传奇,他提到了科层组织化日益普泛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打工群体的涌入,还有他们在城乡之间的身份和归属的难以定位。黄子平一直将历史看作一个有主体的历史,将现在的思考视为与过去的“他者”和未来的“他者”的对话,他反复重读历史,感受到一些不变的主题如语言暴力是如何像幽灵一样在各个时代都向人们袭来。对过去的探寻,实际上就是在为我们现在的困惑寻求解法。历史从来不是一个僵死的对象,也从未远离我们,它因为我们的思考而流动,永远保持新鲜。
作者丨孙佳雯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