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特约撰稿人 郝汉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颠覆性地改变世界,而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兴奋地对“世界要向何处去”发表高见,关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及左派与右派之间陈腐、过激的对抗,借着积蓄已久的社会矛盾与撕裂,名正言顺地在舆论场里再次亮相。
这一切,似乎都验证着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保罗·科利尔教授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的论断:“人们很快用各种旧意识形态来解答新的焦虑,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诱人的组合,简单的道德确定性和无所不能的分析,能够为任何问题提供自信的答案。”
保罗·科利尔对现行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作出诊断,他认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存在于地理、教育和伦理等因素中。“各地区皆在反叛大都市,英格兰北部在反叛伦敦,内地在反叛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反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辛苦拼搏的劳动者,在反叛不劳而获者和寻租者。”他进一步指出,“受教育程度较低、艰辛工作的乡下人和小镇居民已经取代劳工阶层,成为社会的革命力量。”
比尔·盖茨自诩为保罗·科利尔的超级粉丝,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但凡要有未来,就必须做出改变。其中,通过务实的政策,以道德方式重建家庭、企业和国家,打造由互惠义务构建起来的有归属的政治是核心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意识形态的极端派。
保罗·科利尔的立场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他生于1949年,在西欧战后30年黄金岁月中长大成人。他说那一时期的发展,便是讲求社群互惠义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坚实胜利。但自从撒切尔夫人提出:“没有社会这件事情,只有一个个男人女人,一个个家庭。”“理性经济人”再次强势地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上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基于二战共同记忆上的社群主义理念早被淡忘并抛之脑后,关于归属的政治被进一步瓦解,他认为资本主义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道德上的堕落,并将此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第三次脱轨”。
对此,保罗·科利尔没有重复那些陈词滥调,而是通过细致分析社会病症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理念提出了尖锐质疑,并开出治理之策。比如,有人对“爱国主义”进行无限度的批判和警惕,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世界主义者们,正在放弃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不对任何具体地方感到负有切实责任与义务。但科利尔提出,“对大多数政治实体而言,最切实可行的单位是国家。”为了弥合社会撕裂与公共政策的有效运行,我们“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重建空间性纽带。”
“爱国主义”和归属感,对于治愈资本主义为何重要?大城市的教育精英如何挑战了传统的劳动价值感,被边缘化的低教育水准人群和小城市,又造成了怎样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以及社会撕裂?什么叫作道德资本主义?道德缺位的金融业,如何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资本主义真的有未来吗?我们带着如上问题,采访了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难民》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大城市和小城市的鸿沟
导致社会撕裂
新京报:你提到如今存在许多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地域分化、教育分化和伦理分化,有一个新的阶级正在成长起来,他们具备高级技能,坐拥“文化资本”,在全球大都会中处于某种统治地位。他们正在挑战或者已经成功改变了传统的“工作伦理”,使得低技术水平的劳工阶层不再像从前那样被人尊重。你所描述的新社会阶层具体来说有哪些特点?这种现象造成了哪些经济与社会后果?
保罗·科利尔:没错!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严重分化,正成为横扫几乎全球所有发达国家的现实。实际上,这在许多社会中,一部分是经济上的现实,一部分是心理上的现实。
从经济层面来说,那些全球大都会、体量最大的城市,都经历了40余年的高速发展,并将其他城市远远抛在后面,这是市场全球化的后果。有少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赢家,其中极少数城市成为最大赢家,成为全球意义上的赢家,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领先者。
如今,生产力取决于生产流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要求多维复杂技能。这些多维复杂的技能,建立在良好的高等教育背景基础之上。所以,那些有着知名大学教育背景的人,能够获得那些高层次的技能。因而,他们能去大都会谋生,在那里他们的教育背景才会十分有价值。他们借此挣了不少钱,且认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理应得到的。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这么有生产力,是因为他们很特别,所以对既得的一切感到理所当然。
这也就是我们常常用“精英主义”这一概念所表达的含义,并且借助媒体在这些城市新贵与教育精英心中变得根深蒂固。他们看不上那些和自己大相径庭的群体,并与那些和他们不属于一个团体的人不共有任何的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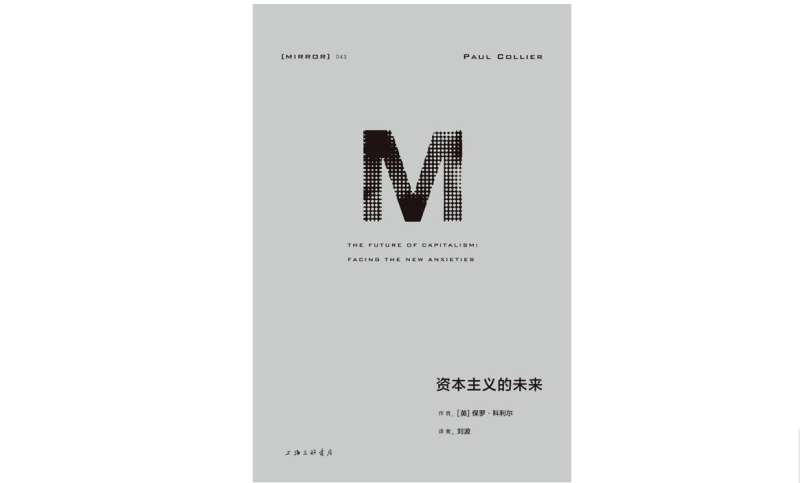
《资本主义的未来》,(英)保罗·科利尔著,刘波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精英主义”这个词在1950年代才出现,当时这个词的出现是出于批评的需要,那些发明这个词汇的人们,将此看作一个非常糟糕的社会运行手段。因为这造成的社会分化实在太严重了。而如今,人们自豪于取得精英式的成功。城市精英们将其他人拒之于千里之外,由此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后果。
城市里如今出现一批在过去40余年里乘着直梯进行跃升的人,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都会人;与此同时,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小城市人,坐了将近40年的下行电梯。那些小城市中聪明的年轻人,但凡受过良好的教育,都前往国际大都会,比如像我所做的一样。如此一来,小城市不断地失去他们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并导致严重的年龄结构失调。
举例来说,伦敦几乎是年轻人的天下,并正在甩掉那些较不富裕的和老龄人口。小城市却有着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通常来说,他们也没有在工作状态。人口变化让小城市的经济基础被进一步腐蚀。当下这一政治后果将要耗费我们数年之久来进行消化。更重要的在于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小城市人开始感到被边缘化,变得愤怒起来,而且他们不再沉默。我们可以从英国的脱欧中一窥这一现象。
除了伦敦之外,英格兰各个地方都投票支持脱欧。在美国,特朗普被选上当了总统。法国的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便是由反叛大都会巴黎的其他小城市组织。我们在德国选举中也看到,东德人认为自己彻底被西德经济上成功的大城市边缘化了。所以,这是一个十分广泛的现象,并且由于这些政治不满,愤怒化的表达变得十分具有破坏性,因为在情绪宣泄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寻求一个解决之道。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地尝试和考虑如何治愈这些伤痛。我认为关键不只在于将此转化为单纯金钱的资助,而在于提高那些小城市的生产力。那些不去上大学的小城市人需要变得有生产力,我们公共政策上的努力需要以此为导向。这绝非易事,但是能够做到的。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我主张对此进行有决心地政治承诺。我们不知道这将带我们去到何处,但想要治愈伤痛,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表现的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场景。
新京报:你的书关注西欧与北美的情形,而相似的病症同样袭击了世界其他地区。
保罗·科利尔:大都会和城市教育精英的崛起背后的力量是全球性的。这些力量在任何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经济体中都会发生作用。
实际上,今天晚上我将飞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商业论坛讲述你所问到的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现象在哥伦比亚也正在发生。正如你所说,这些问题并非西欧或北美所特有。我在书中之所以将英国作为例证,是因为我生活于此,这些问题发生在我的个人生活之中。并且,英国有着严重的社会分化,可以说英国算得上最坏的情形。这本书既关注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的家庭横跨在这种分化撕裂之间,也结合了这个国家的经验。但如你所说,这仍然是一个全球现象,这本书由一半以上都在讲我们对此的解决之道,我认为这些办法同样不仅仅针对欧洲和北美,它们相当程度上是通用的。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
为何公司需要对社群
负有道德义务?
新京报:面对资本主义导致的分化与撕裂,你认为最关键的解决方法是建立一种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的“道德资本主义”。你关于“道德资本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什么?你为什么将此视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出路?
保罗·科利尔:公司与家庭是塑造我们生活的关键组织,这两者都要承载道德上的义务,但并非说去规制公司或家庭,使它们行动上必须考虑所有人的利益。他们自身需要为富有道德地行事负起责任来。有一点幸运的地方在于,我们从进化的历史中发现人类其实预先具有着做一个“社会人”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顾及他人利益、知道要互惠地协作。
在亿万年的进化之中,人类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懂得团体合作。一旦某个人尝试单枪匹马地生存,他就会死掉。所以,人类是迄今为止所有物种之中最具有“社会性”的物种。基因编程决定了我们注定要承载道德的义务,这并不是在说我们是圣人,而只是意味着人类并非自私的混账。这便是家庭与公司这两个组织对我们的生活如此重要的真相。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40来年里,公司与家庭的道德角色萎缩,它们开始承担越来越少的道德义务。社会正在不断地以国家与个人的直接对应关系被组织起来。而国家往往太过巨大和遥不可及,以至于不能够有针对性地指导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又太渺小,国家没有办法触及并履行道德义务。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赋予公司和家庭在道德上的角色。
如今公司的功能仅仅是促进生产力、提供就业岗位、发挥盈利能力。这一现象在西方社会明确地在发生,英国尤甚,可以说成为了最极端的例证。公司被要求为了股东和顶层管理者的短期利益最大化而运营。这将公司从更广泛的对其所在社区、社群和雇员的责任中割裂出来。
比如说,公司会倾向于放弃会产生损失的计划,而非在社群中进行投资,使其具有工作价值创造的可能。对于公司的雇员而言,公司不再会对年轻雇员进行足够的培训,即使他们需要。他们也将雇佣合同变成非常短期的合同,如此一来,市场风险便由股东转移到劳动者自身。这些都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的发展变化。我们需要回到那个企业对其所在社群、雇员、劳动培训承担着更多社会责任的系统中去。
一些社会尝试矫正这一现象,比如在培训下一代劳动者这一方面。依据我的经验,瑞士是做得最好的社会。今天的瑞士是全世界最富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但它仍然成功地做到了让公司在职业培训上负责任地行事。所以,这证明如此做法与资本主义并行不悖。如果能发生在瑞士,它将可以发生在任何市场经济体之中。但它目前肯定还没发生在英国。在与社群的关系上,德国公司和当地社群的联系要比英国紧密得多。
所以,将公司的行为社群化、地方化是完全可能的,一是对社群负有道德义务,二是对劳动力负有道德义务。资本主义不必像今时今日这般模样,我们将那些好榜样作为学习的对象,汲取经验,我们可以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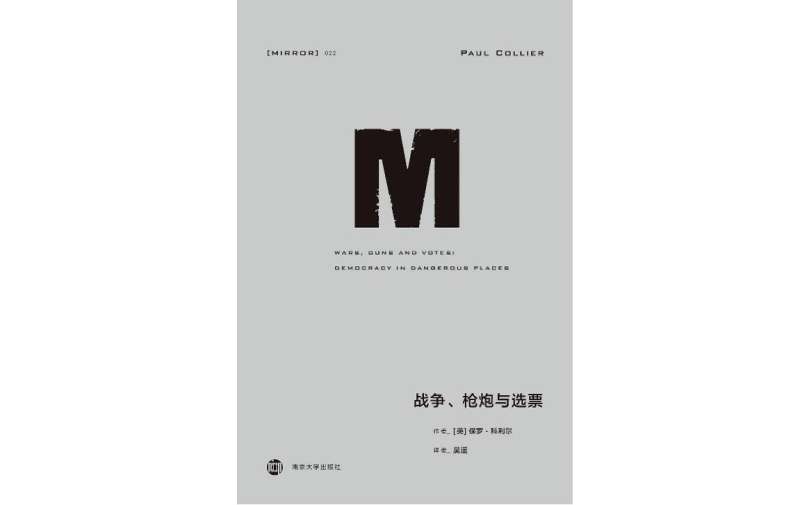
《战争、枪炮与选票》(英)保罗·科利尔著,吴遥译,理想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新京报:许多批评者大致上同意你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但对你提出来的补救措施并不买账。比如说,一旦企业负责人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严重忽视公共利益,那么就可以依法将其控制起来。你的超级粉丝比尔·盖茨认为,通过改变私人公司的股权结构,或许是更为有效的方法,这样可以促进达成其他社会目标。你对此如何回应?
保罗·科利尔: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不同的结构实验。我们知道,当今企业的行事方式必须被改变,但我们永远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好的。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尝试不同的事情,看哪一个最有效果,再进行改善和推广。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公众政策方面发挥的道德作用,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强。所以,这种通过来自最顶层的政治承诺或许有效,我们可以尝试它。我不想与比尔·盖茨争论,我们都同意需达成某种目标,而关于如何达成,我们有各自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在实践中去看,哪种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许我们都错了,还另有他法。
但我对过分依赖股权结构调整的效果有一些怀疑,我认为,与其如此,不如改变权力结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应该在决策过程中都有代表权。过分依赖股权的做法,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证明失败了。正如我所表示的,我愿意尝试各种方式,再看其效果如何。没有什么比实验更能启发人的了,这叫“社会化学习”。中国在过去40余年里十分擅长“社会化学习”,对于许多决定进行去中心化的实验,在不同的地域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

《被掠夺的星球: 我们为何及怎样为全球繁荣而管理自然》(英)保罗·科利尔著,姜智芹、王佳存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把所有人都集中在大都会,
将会十分糟糕
新京报:有人说,我们应该专心用市场力量发展基础设施,帮助更多人与大都会地区建立紧密的交互联系,这样才可以将大城市集聚效应带来的好处最大化。你对此有什么回应?
保罗·科利尔:在我看来,那种认为只有在国家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集中发展才能够成功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它会导致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可以拿英国来举例,英国如今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中最大的经济体,但它的所有资源都集中于伦敦,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极大的生产力鸿沟。
伦敦如今是全国有着最高收入水平的地方。与此同时,如果你将英国分地区进行快乐和幸福感的排名,伦敦人将排在最后一名。这么看来,伦敦在将生产力转化为快乐和幸福感上做得令人不可置信地低效。所以,那种认为应该将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到伦敦这样的大都会的想法,听起来十分糟糕。伦敦没有办法生产出太多快乐和对生活心满意足的人。在大城市,亿万人的身份认同已经被撕扯得支离破碎,而他们除了离开从小长大成人、具有很深归属感的小地方,去到国际大都会谋生,别无他法。当然那些亿万富翁除外,他们着迷于大都会顶层奢华生活,而普通人面对的只有脏乱差和局促的生活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将生产力设法转移回到那些人们能找到归属感和幸福感的地方。

伦敦大本钟。
在这些大城市中,许多客观的生活质量指标,比如空气质量、交通等等都十分糟糕。当他们填写生活幸福度调查问卷,考察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有多满意时,他们会自然地回想起那些阴郁的遭遇。所以,大城市真的不应该是我们要去鼓励的事物。
我们需要在各个地区都有成功的城市作为支撑,这时候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其赋能显得十分重要,比如便宜的电力和便利的交通,这些在物理上和经济上都极其重要,这些打下了城市生产力的基础,但许多小城市并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在英国,伦敦花费着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其他郡市的七八倍之多。这太荒唐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指出,随着社交网络的国际化,我们的身份认同也在全球化,但主导公共政策的力量却有着必然的地域性,这成为时下的关键困境。你认为,爱国主义与找回地方归属感,才是再次凝聚人心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的办法。而在如今的情形下,我们有可能让那些发展出全球意识的世界主义者们重新回到“想象的共同体”中吗?
保罗·科利尔:首先,人当然可以有多重身份认同,几乎人人如此,而问题在于今天许多人拒绝包容性的身份认同,因为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要在某个特定地域范围内被执行。所以,我们发展出超越私人的亲密关系并对于某个地方有社群归属感非常重要,而这个地方往往意味着是你所居住的地方,比如某个小镇或城市、国家。大多数政策都是在国家层面来主导的,因此,和你的国家的其他人发展出共有的身份认同,对于公共政策施行的有效性来说至关重要。
人们需要依据对某一社群的责任感来产生共同的尊重意识,这种意识最终构建了国家。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产生超越国家界限的全球意识,但现实在于公共政策是有地域性的,并且大部分人的生活被地理条件所限制。人们住在哪里,将家安在哪里,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与地理位置联结的一幢客观的大楼,这和家的意识紧密相连。人们通常会尽量在住处的周遭位置工作,人们的孩子会在这些地方长大,并且形成对这些地方的身份认同,所以,基于地理的自我认同的诞生是必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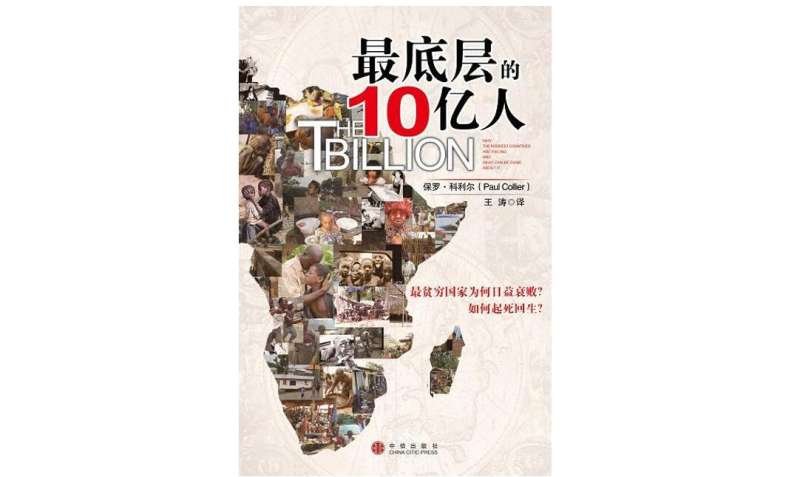
《最底层的10亿人》(英)保罗·科利尔著,王涛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7月
道德资本主义
会有实现的可能吗?
新京报:如今有一种新型的金融创新技术正在被提及,该项技术旨在创造一种肩负社会任务而非单纯利益攸关的投资模式。借助这项技术,人们可以知晓自己的投资正被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并由此真正掌控自己的钱。比如,一个约克郡的居民可以明确他的资金在约克郡运作,并为当地创造效益。有人预测说,这将最终实现“资本的民主化”。你认为,这会不会是一个达成你所说的“道德资本主义”的有效尝试?
保罗·科利尔:我完全同意这项技术创新。我认为,妥善的金融运作是我们能够做出改变的基础性动作。金融需要变得越来越本土化。金融业是一个终端的工业,它要依赖许多知识。因为金融的核心挑战在于它得搞明白哪些企业应该获得投资,而哪些不应该。为了达成这一点,需要了解关于企业的许多在地性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金融业最早都是地方性运作的结果。
金融机构都依赖于一些城市,并且要在这些城市变得有影响力。在城市银行向全球银行的转变过程之中,它们尝试着将金融知识的在地性部分进行剥离。这在决策过程中造成了真正的灾难性后果。所以,重新回到注重在地性的金融业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交易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2008年的金融危机,便揭示出全球金融业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做得极为糟糕,而且是一点道德都没有。他们离间了储户和资本使用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房贷业务中,金融从业者们仅仅出于获取佣金的考虑,故意隐藏借贷人没有能力偿还的事实,这实在丧尽天良。

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剧照,反映资本主义体制下工人沦为螺丝钉。
新京报:所以,问题在于储户不知道自己的钱在干什么。
保罗·科利尔:没错。储户没有任何办法知道这件事情,但这恰恰是金融业应该扮演好的桥梁角色。只有金融从业者坚守道德信条且花费时间获取投资企业的详尽的在地性知识,储户才能够真正重新相信金融行业。
新京报:西方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冷战”的代价,才发展出真正务实的互惠原则(如建立欧盟、经合组织),并开启了从1945年到1970年的黄金发展期。你曾经引述乔纳森·谭普曼(Jonathan Tepperman)的观察,认为根本性的变革只会发生于存在性的危机之后。你认为,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准备好改变的节点上了吗?
保罗·科利尔:我主要有两点想说。第一,资本主义确实有未来可言;第二,如今实行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导致了某种存在性危机,我们不知道政府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社会已经如此严重地被撕裂了。所以,我的确认为,显著的改变必将伴随着巨大的推进力量,而危险不在于这一体制会不会有所不同,而在于是由民粹还是改革所推动,这是我们真正面临的选择。
我们要不然就前功尽弃地扎进疯狂的政策之中,这些政策便是民粹主义政治的结果;要不然我们就得严肃地对待,并回溯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并承诺要有所作为,有所改变,汲取做得好的地方经验,花费一二十年时间去弥合和治愈现行资本主义体制造成的撕裂与伤痛。
资本主义周期性地脱轨运行,到如今已经有250年之久,历史上曾经有三次严重的脱轨。第一次在19世纪40年代,那时候城市变成了健康杀手,出现了霍乱和雾霾。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巨大数量人口的失业。这两次脱轨都被解决好了。然后,第三次脱轨到来了,如今我们社会致命的伤口有能力被妥善治愈,也必须被解决好。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会不会前功尽弃,世界又重新变成一块充斥着疯狂的土地,我但愿不会。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你的专业经济学因为过度强调全球化的积极性,极少关注其对负面分配效应的影响,因而欠世界一个道歉。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应该是政治家该操心的事情,而非他们。如今,你认为这个看法有在你的同僚中形成广泛的共识吗?
保罗·科利尔:我愿意坦然承认经济学专业的局限所在,这个专业固执地抵抗改变的程度,可以说令人吃惊。其他专业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通行原则,但只有经济学家们仍然在“Solo”着。
所以,我认为,这个专业要成为一个引入伦理学、社会学,并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的崭新社会科学,仍然有着很长的路要走。在行为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但它仍然十分专注于个体偏好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我们需要将视角移到群体中的准则,以及这些准则如何在行为中起作用。所以,经济学专业依然有着漫长的发展道路。
采写 郝汉
编辑 徐伟 徐悦东 张进
校对 吴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