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 徐悦东
两个多月来,因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而引发的街头抗议运动,在持续发酵。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越临近选举日,美国各派的对垒也越发白热化。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愿屈服于抗议运动。美国左派阵营也出现了分裂,激进左派所推行的政治正确,引起自由派与温和左派的割席。乔姆斯基、J·K·罗琳、史蒂芬·平克和福山等名人联名签署公开信,呼吁对抵抗运动中的一些极端行为进行纠正和反思,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这些街头运动闹得沸沸扬扬,究其根源,还是美国的种族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源自美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也和美国许多其他的社会问题深刻关联在一起——比如贫富差距、南北差异、去工业化、城市化变迁和全球化等。

许倬云,1930年生于江苏无锡,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校讲座教授。1986年荣任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代表著作有《西周史》《汉代农业》《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说中国》《中国文化的精神》等。
历史学家许倬云自1957年赴美留学,到现在已经客居美国六十余载。他经历过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以及新世纪的金融危机。他刚进入美国时满怀兴奋,很想看看这个以崇高理想立国的新国家是否能落实人类的梦想,但如今他心情沉重,对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扼腕叹息。
虽然许倬云主要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但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新近出版的《许倬云说美国》(他自称是个人“最后一本书”)中,他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眼光,将美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包括种族问题、经济问题、特朗普现象等——重新放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追溯这些问题背后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源流,试图为当前的迷局寻找到答案。
在书中,许倬云对美国观察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他念念不忘的中国。他认为,美国遇到的问题和走过的道路,都可以为我们提供镜鉴。近日,新京报对许倬云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论了当下美国的社会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西方文明危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新京报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视频导引:
00:49——福利制度和受教育程度是美国种族问题的关键
00:57——黑人缺乏参加各层次民权运动的“管道”
03:28——知识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亚裔应作为带头羊,与黑人和西语系结成联盟
05:10——应该用亚裔、黑人和西语系三个集团的选票,来决定美国政治的许多问题
06:09——美国农业地带的中小型农庄缺乏人手,亚裔可以“打进去”
07:53——特朗普用古希腊柏拉图的政权分类来说,是“tyrant”
10:34——二战以前,最大的危机就是国家主义作为最后的、最终极和最有权力的大群体
11:41——中国人不以神作为一切智慧、理想和文明的来源
13:59——西方人总认为历史发展有个终点站
17:14——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家庭、朋友圈,都是互相套连在一起的
美国的亚非拉裔应联合起来,
通过合法方式争取权益
新京报:近期,由于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美国多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你在新著《许倬云说美国》中分析了美国各个种族的历史情况和发展机遇,认为在黑奴解放后,一次次旨在提高黑人地位的民权运动成效并不大,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使得黑人缺乏上进的动机,另一方面是历史原因造就了黑人不重视家庭和教育。但也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还是美国的社会资源向黑人倾斜得不够,种族问题本质上是阶层固化问题,黑人没有足够的机会实现阶层跃迁。你怎么看待这次黑人抗议运动,以及美国种族问题和阶层固化问题的关联?美国该如何打破种族问题的僵局?
许倬云:这个问题关系到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权运动,但到现在,一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这个僵局是从解放黑奴开始的,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那只是在法律上,黑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下。美国政府也不是不懂黑人社会地位低下的后果,自由派以及民主党内的民权运动者,都在不断设法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提高黑人本身的自觉性,以求降低种族间的对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人们对这个问题依然无可奈何。
福利制度和教育问题让黑人无法提高自己的境遇,其社会地位一直在原地踏步。无论自由派如何着急,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由种族和阶级混合起来的难题,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黑人群体没有足够的民意表达“管道”,可以让他们参加各层次的民权运动,甚至在各层次的民主制度下,让黑人选择自己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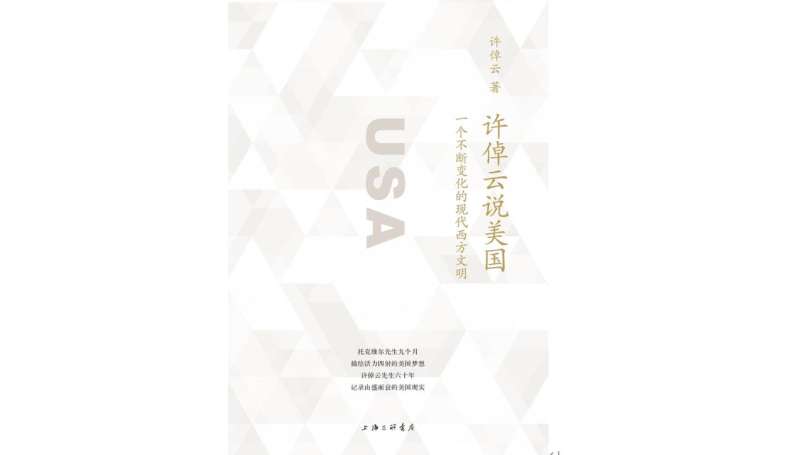
《许倬云说美国》,许倬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
黑人本身被几个影响因素所支配。南方黑人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还受到教会的控制,这使得他们的境界无法得到提高。北方城市的黑人,大多也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如果他们没有工作,就会得到国家的补助,但他们只吃“皇粮”也不是解决办法。
我个人认为,我们亚裔在美国是处在中等阶级上下的族群,有高于中等阶级的,也有低于中等阶级的。最劳苦的亚裔包括在唐人街餐饮业里打工的那些人,比如在后厨洗碗的人,在前台送饭、送菜的人,他们的待遇是很差的。但是,大多数亚裔都处在中等阶层。华人的受教育程度基本上不差。华人的社会地位无法得到提升,是因为华人的人数不足。在美国,华人只有几百万人,这是没有办法通过集体运作共同努力,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我的构想是,要有一个能够使得亚裔、拉丁裔以及非裔三个族群一起合作的“管道”。华裔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拉丁裔中下阶层都有,非裔大多都处在社会下层。处于社会上层的非裔是罕见的。这三个族群合在一块,由知识程度比较高、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亚裔来做领头羊,并跟非裔和拉丁裔结为联盟。这样,这个联盟在人口构成上,就能超过全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族群间的合作不容易做到。谁来做“头儿”,都需要有一批人将自己整块的时间奉献出来,帮助自己和其他的族群。现在,华裔基本都知道,亚裔要联合起来。以前的美国华人组织(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简称OCA)早已并入亚裔协会之类的组织,已成为Asian Pacific American Advocates。其实,这种工作还能够扩大到包括非裔和拉丁裔在内的族群。
华裔结合越南裔、泰裔、韩裔和日裔,能够构成一个有机的、能发挥领头羊作用的亚裔群体。然后,亚裔再帮助非裔和拉丁裔一起,用三个集团的选票,来决定美国政治的许多问题。这样就可以使得许多诉求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实现。

当地时间6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联合广场,集会人群高举弗洛伊德照片与 “黑人命也是命”标语。摄影/新京报拍者 Bobo

一位参与示威的白人女性戴着写有“JUSTICE”(公正)字样的口罩。摄影/新京报拍者 Bobo
但是,未来的局势不知道会如何发展,我猜想特朗普大概率不会再当选。如果他再当选,我们会受不了。等换了政权以后,拥有一定资金和能力的华裔,其实有个薄弱的地方可以打入——那就是美国农业地带的中小型农庄。中小型农庄缺乏人手经营,农业州的人口一直在减少,基本上没有美国人的孩子会回到农村。这一大片空着的土地有生产能力,但缺乏劳动力。如果华裔能在这些地方有所进展,以农庄为基地,带进来第二拨、甚至第三拨华人作为管理干部,并雇用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做工人,给他们公平的薪资待遇和上升机会,并让他们拥有股份,就能很快除去族裔之间的差异,黑人地位上不来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此解决之后,许多政治上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力量。如果这样,白人对抗所有人,中产阶级对抗整个底层,白人的富有者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情况,就可以有相当大的改变。

《许倬云问学记》许倬云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特朗普现象是“异象”,
他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总统
新京报: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在《许倬云说美国》里,你认为美国已经出现了柏拉图所说的“僭主政治”,并认为美国政治以富人政治为主、寡头政治为用,这使得美国原本出于善意的立国理念陷入了扭曲的困境。你觉得美国该如何处理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度过政治危机?近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等“黑天鹅事件”频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政党正在西方各国崛起。对于西方右翼崛起和汹涌澎湃的民粹主义浪潮,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许倬云:用古希腊柏拉图的政权分类学来说,特朗普是“tyrant”。这种人完全靠个人的声望地位或组织能力,利用城市(古希腊城邦)中知识程度不够的人来取得政权。古希腊人曾把他们最好的人放逐,甚至处死。比如,苏格拉底就被处死,因为他喜欢传播关于民主自由的理论,也传播思考的方法。苏格拉底希望可以借此矫正靠底层、歪曲群众力量和靠暴民取得政权的僭主现象。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总统,这不单是因为他得到政权的过程很奇怪,也是因为在他执政的过程中,他既没有政策,也没有学问,更没有方向,也不触及制度。可他居然被选上了,到今天支持度才慢慢滑下来。

当地时间7月11日,美国马里兰州,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认为这是很怪的异象。这异象是因为其他族群起来了,尤其是非白人族群——亚裔、非裔和拉丁裔崛起,撞击到许多白人的意识,使得那些无知无识的、不知道选票意义的、不知道民主制度内容的底层白人选出了今天这样的总统。
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特质,
可以修补现代文明的问题
新京报: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作比较,一直是你研究的主题,你找出了许多中华文明的特质,并认为这些特质有可能补救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许多文明也都有通过找回自身文明的特质,来应对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但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而且,中国的许多精神传统在当代年轻人身上已经失落,比如,庞大的社会流动使得我们的社会原子化,家庭、宗族或社区很难再发挥从前的那种功能,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信仰也日趋淡薄。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你觉得我们还有可能重新恢复传统的生命力吗?传统精神真的能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吗?
许倬云:我认为中国群体的一些特质,可以弥补现在个体流动和社会疏离带来的一些问题。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中国的群体有着不同层次,从乡党、邻里、家族逐步上升到地区,最后到国家和天下,大家都在这个大群体里面共同存在。分层次的群体,跟国家主义那种笼罩在上面的群体是很不一样的。
二战以前,最大的危机就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主义,国家是最有终极、最有权力且最合理的大群体,但这个想法是不完全对的。在一个国家之内,国家也应该要容忍许多不同群体自己结合,必须容忍个体跟群体之间不同层次地互相对应和回报——人从群体里得到庇护、帮助和温暖,再以更多的温暖和好处回馈这个群体。人对群体做到了尊重,也尽了自己的义务,这才是能互相对应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群体对应着不同的权利和义务。
最后归结到内心,人要对自己负责任。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一样,中国文化最有特色的是不以神作为一切智慧、理想和文明的来源。人是自己创造的。人就是天地之中心,有人间的智慧才能让人结合起来。每个人内心的思想和情感,要不断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像磨刀一样,磨得更光亮、更干净。人的内心修养不仅能使自己得到好处,也能从个人辐射到社会其他部分,让别人也因此得到益处。

许倬云接受《十三邀》节目采访。
见贤而思齐,我们看见好人和合理的作为就去学;见到错误的行为,每个人都拿来当镜子照,时时刻刻捕捉和矫正自己。我们一直在修整、提升、精炼、蜕化,使得个人变好,这样个人所属的群体也变好。个人所属的群体好,就会使个人不寂寞、有安慰、有交流,有滋润的营养,这可以解决现在个体化的问题。
美国的个体化是从白人社会中出现的,雅利安人的社会基本上都是个人主义的。基督教在个人之上加了一个上帝。不然,个人主义以利为主,并不以理想为主。中国可以把利的部分转变为理想。
还有,中国的思想与西方思想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思想总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点站就是理想的实现,就是理想国或乌托邦。中国人不认为如此。中国人认为事物永远有改进的余地,世界在不断变化,变的缘故既有外力的刺激,也有内力成长的刺激,还包括互动作用的刺激——个人与个人之间互相学习、模仿、抵消和矫正,群体与个人之间互相矫正,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矫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状结构。这个网状结构叫“Network”,“Network”本身是在永远变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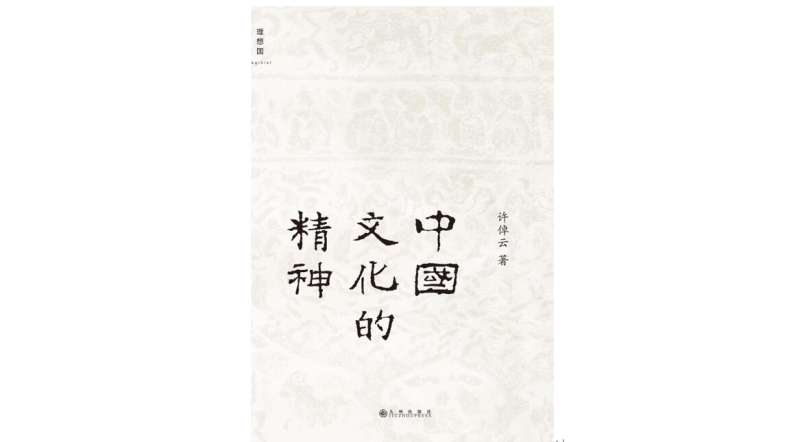
《中国文化的精神》许倬云著,理想国|九州出版社,2018年12月
中国人的精神最要紧的是变化。《易经》就是讲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两个字。这个观念再加上群体之间不断地协调和调整,就可以抵消掉个人主义高涨、国家慢慢萎缩后被人利用和没有权力的人无法对抗国家机器这些现象,也可以抵消掉仰仗着科技、生产工作和管理工作一步步付诸于自动化和更多辅具所产生的现象。
在这些自动化辅具造出来之后,这是人工智能来管理我们,不是我们来管理人工智能。我们人类被自己创造的大型人工智能所捆绑。今天,我们的大型人工智能,因为网与网之间的结合和流通,已经可以在无人操控的情况下,知道我们每天生活的情形怎么样,可以支配我们钱的进出,支配我们的交通,支配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家里的温度。
我强调的中华文化的特色,一个是群己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自己不断提升的责任;在自己提升之外,还要帮助他人提升。现在,全球互相“interlock”(紧密连接),形成互相协调、互相结合的复杂群体结构,这里面有独立的部分,也有联合的部分。联合起来的群体,就是全球的总人类体。分开来一块块的小群体,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家庭和友谊圈,都是被套连在一起的。
因为有这种套连关系,没人能真正完全独立。不同单位之间彼此互动、拉扯和刺激,都会产生新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人类社会一直在改变提升、寻找进一步协调的来源。这样才使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如同流水一样,不断在流动之中更新和改善。
撰文 徐悦东
编辑 徐伟
校对 李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