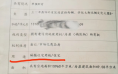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进
“闹城”即是太原城,在作者出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是中国重点工业城市,作者在序言中说:“《闹城》是一部图文对照的个人口述史,它的文化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强国梦和工业化建设。”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作者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和日常琐事,以个人和细节折射历史。

苏丹,1967年生于山西,著名设计师、设计教育家、艺术策展人,北京市政协委员。曾任清华美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清华美院副院长。现任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长、米兰新美术学院和多莫斯设计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特聘教授等。
苏丹从自己的出生开始写起,写到其父亲、母亲、奶妈、哥哥,以及在工业化附属社区的直觉体验,进而写到自己从幼儿园开始的几次“逃亡”。“空间往事”一辑写的是在一个设计师眼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空间”,如集体大澡堂、操场、防空洞、电影院等,对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形态和人的思维、行为模式的深刻影响。最后的“老脸”系列则像一幅幅素描,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司机、崩爆米花的人等进行了短促有力的描写,呈现出的是一个时代之下人的精神面貌。

《闹城》,苏丹著,新经典·琥珀|花城出版社,2020年5月。
1
“家庭教育可以非常直接地应对人类的复杂性”
新京报:作为一部回忆录,《闹城》是你对故乡、对往事的回望。《后记》中提到触发写作本书的缘由是奶妈的去世。《奶妈》一篇中你说,“奶妈……是利他主义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关于这一点,能不能请你延展说一下?
苏丹:奶妈在山西是非常普遍的。我认为她是一个古老的事物,是在乡村社会,或更古老的部落时代就形成的一种习惯,是人们之间的互相接济。但这种接济的方式不是财务,而是情感上的付出和牺牲。牺牲有两个层面:一是哺乳者要付出情感,二是被哺乳者的生母也要付出情感的代价。她不能一直带自己的孩子,要委托一个他者去帮忙抚养。他者又要像对亲生的、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一样用自己的母乳去哺乳他/她。这是人类社会性的一种表现。
社会是人类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一“总和”里,主要的是(人之间的)互相的协助、帮扶,各司其职,维持系统的运行。很多人因为这个系统的存在得以生存,能够克服自然带来的问题、社会和社会之间的问题。奶妈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我认为她具有浓郁的社会性,但又对血缘、伦理提出了挑战。
当时写完《奶妈》这篇文章后,收到了非常多的留言,这是超出我想象的。可见在那个时期,奶妈是非常普遍的。我周围就有很多孩子,跟我一样大的,甚至比我小的,都是有过奶妈的。也(因此)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家庭纠纷和矛盾,在留言里也能看到,真是百感交集。但我们家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比较妥帖,这是由于我父母的开明。
新京报:《父亲》一篇中的几处细节引人深思。父亲有意识地训练你们写日记、书信,而且“‘文革’一结束,父亲便开始训练我们背诵唐诗宋词。”这种家庭教育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如何看待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从父母的角度看,你认为父母应如何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
苏丹:我父亲用唐诗宋词(训练我们)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在父亲教我之前,唐诗对我来说基本上是顺口溜,但当我们真正接触到唐诗宋词时,因此产生的想象,(感受到的)情感表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我非常感激父亲。
家庭教育对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家庭教育依然是对社会教育的一种制衡。社会教育是以科学的名义,让孩子们定期入学,用通用的教材、谈共同的事,我觉得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家庭教育恰恰是一种弥补。家庭教育是父母身体力行地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通用的教育,其实无法应对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但是家庭教育就可以非常直接地应对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家庭教育更具体、更鲜活,跟生活水乳交融,它指导着生活中的所有细节,这是家庭教育伟大之处。家庭教育对塑造人格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也有孩子,我觉得这方面的确是非常重要,我也在不断调整。

《童年》油画,作者:杜宝印。
2
“个体意识的觉醒
是社会变得多元、有创造力的开始”
新京报:《母亲》一篇中写到你对把个体意识融入到集体之中的反思:“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的也就毫无疑问是集体的意识,而事实上集体是‘无意识’的。”从集体的无意识到个体意识的觉醒,在你个人身上表现为一个怎样的过程?个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什么?
苏丹:在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中,集体是权重,而个人是需要消隐的。对于不同的个体,当时的教育也好、氛围也好,产生的影响也有差异。社会并没有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集体无意识,抹杀掉个人,还是有一些先知先觉者。但先知先觉还是要靠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一种反抗去挣脱。我认为我身上有这种东西,我小时候(从幼儿园)逃跑是具体的表现。个体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很多。我觉得个体意识的觉醒,可能是一个社会真正变得强大、多元、丰富、有创造力的开始。没有这一点,(上述这些)都是虚幻的、想象出来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时代与个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个人应如何面对强大的时代风潮?
苏丹:我们没有权利去选择一个时代。一个人出生、睁开眼睛,面对的是一个事实,是具体的一段历史。所以在任何时代,时代都在铸就一个人,但你本身也在铸就自己。对于特殊的一些人来讲,他/她可以规避时代的很多影响,成为自己。这是非常难的,弄不好就是自闭症,但还是有些人独立地存活下来了。
我其实不算特别独立的,而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者,既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在时代铸就的过程中留下了(集体的)痕迹,但这种痕迹并没有把我的个体意识全部泯灭,我有自我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很奇怪,年纪大了以后越来越顽强,开始不断追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谁,我的归属是什么,总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在社会里的定位、在历史中的定位。我真正有个体意识可能还是后来的事,但之前是否有潜意识在影响我的行为?我想是有的。
3
“在工业社会,
好像生命的消失也是匆忙的”
新京报:你幼年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化尚属初始阶段,书中描写了当时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混杂的状态,有一处非常生动的细节是,“这些鸡竟然都学会了上下楼梯”。书中你说:“城市对于我来说,却是一片巨大的沼泽,复杂、阴沉,处处潜藏着危险”。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苏丹:这是一个直觉。我经常回想那时在乡村(的生活),因为我记忆力好,所以乡村的生活记得非常清楚,两岁左右的那些事情。村落里的马、猪、羊、公鸡打鸣,尤其是场院,我觉得特别阳光,因为是晒谷子、麦子的地方,地面经常是一层金灿灿的壳。还有毛驴。劳作一天的牲口回来后,人们就把鞍子去掉,让它们放松一下,我就看到这些牲口在地上打滚的样子。那时环境的开阔,包括走出村落后田野里的远山、云、溪水,阳光明媚,阳光留下的影子非常清晰,我从小对世界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但到了城里以后就不一样了。我渺小的身躯在高大的楼群里,楼群里又种了很多树,所以我们一直处在阴影里。阴影里还有阴影,就是楼门里的那些空间,像楼梯、厨房,完全隐没在阴影里。还有很多菜窖、防空洞。城市社会,因为楼群的增多没那么开阔了,光影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混沌。
同时,在这种环境里,有很多比较残暴的东西,比如各种各样的机械和管道。工业社会那时对我来说很陌生,与乡村社会形态上的反差非常大。味觉也不一样,声音也不一样。小时候我父亲会带我到汾河去玩,抓青蛙、蛇、泥鳅。那时候汾河滩基本上是干涸的,里边的径流都是排污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废水,味道很浓。而且河滩上的声音是很奇特的。后来我想,这奇特的声音应该是从周围的大厂房里发出来的,很怪,很恐怖,像台风嘶吼。这是城市留给我的印象。
所以小时候我对工业文明很排斥,对工业的景观很排斥。还有工业生活带来的危险性。小时候经常有人受工伤,社区后面的火车轧死人,邻居的孩子有时候在公路上就消失了,有孩子到晋阳湖的蓄水池游泳就溺水而亡了。在乡村社会里很少看到这些,乡村社会里的人们告别世界的方式大多是寿终正寝,会有很隆重的仪式,哭丧棒、花圈、画得很好的棺材。丧宴的时候,各家会拿出真的很好看的花馍,大家有这种仪式的送别。在工业社会,好像生命的消失也是匆忙的。
新京报:虽然你出生、成长在太原这样的省会城市,但和当下城市生活的特点不同,你说那时的社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把工业化附属社区塑造成熟人社会的因素有哪些?这样的熟人社会和乡村的熟人社会之间有哪些差别?
苏丹:我的社区的的确确是个熟人社会,因为大家共同生产,在生产线上、不同的车间里大家是连接到一起的,是一个整体。这个社区又是个全能型社区,医院、图书馆、体育场、澡堂、幼儿园什么都有。因此在社区里,比如说幼儿园的阿姨、学校的老师,也都是家属。所以他们在训诫、惩罚孩子的时候,又没有完全按照社会意义上的那种职能去行使规则,因为家长和老师都很熟,家长和保卫处的人也很熟。在某种程度上,这对孩子天性里的野性有一种放纵。

短片《看电影》(2006)剧照。
同时社区有一定的排他性,从一个社区到其他社区本身就感觉是在进入到别人的领域,所以在自己的社区里人就感觉更加熟悉。像在大礼堂俱乐部里看电影,就像今天在意大利的米兰歌剧院看剧一样,是一个固定的族群在那个地方看,大家会打招呼,甚至相亲的时候会把孩子带到那些场所去相亲。
这样的熟人社会和乡村的熟人社会有本质不同。工业的熟人社会相对来讲是克制的,毕竟社会的职能得到了加强。比如说到医院,你要按照医院的规则(行事),保卫处有保卫处的规则,防修处有防修处的规则,每个处的规则和职能非常清楚。但乡村是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当时城里人笑话乡村人最大的一点是,如果你在农村有亲戚,他到城里找你的时候,他认为你家就是他的栖身之地,边界(感)是很薄弱的。
我想不仅仅是山西。我到了北京以后,在中央工艺美院的宿舍里也有这样的事。一位老师的宿舍里经常会有很多老家来的人,后来大家发现他家是个大通铺,早上会数从他家出来多少人。很难想象,一个14平方的房间能出来接近10个人。这是乡村的习惯。乡村的熟人社会好像是更进一步,因为它存在的时间长,甚至说过去就是一个宗族,本身是有血缘关系的。工业社会人口是多元化的,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姓氏,它是一个重新建立熟人社会的过程,所以工业的熟人社会的“度”和乡村社会相比轻一些,但跟今天比,它的熟人社会(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

《少年》水彩画,作者:杜宝印。
4
“乡音的消失是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京报:《闹城》与多数回忆录不同的一点在于你对“空间”的关注和洞察,包括空间结构对社会关系、生活形态乃至人的思维、行为模式的影响。如“工厂的生产区被绵延几公里的高高的围墙环绕着,像个巨大的监狱,它保护的是国家的财产,监禁的是生产的热情”,如“公共空间是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会真正找到主人翁的感觉”。此外你还对集体大澡堂、大操场、防空洞、电影院等空间进行了细致描述。为什么如此关注“空间”给人的思维、生活带来的影响?
苏丹:这和我的专业相关。我是建筑学的底子,后来又学环境设计,这两个专业都是在塑造空间,同时敏锐地感受空间,对空间的条件作出一定的反应。其实我们是在空间之中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到了20世纪以后,中国的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有大量的属于社会学的内容进入,这也和我们了解到的西方的专业现状是相关的。所以我对社会学者们的很多论述、对空间的实验都是感兴趣的。后来我发现,社会空间与具体的社区空间、建筑空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说空间的形态就是应对了我们对空间的设置,政治家对社会的安置会具体表现在空间形态上。我写东西的这一独特性和过去的设计批评、艺术批评有关系,艺术批评里谈公共艺术时会经常谈到空间的关系。
新京报:在《一方之言》中你对方言进行了思考。中国各省、各市乃至相邻的村庄之间,语言都有差异。海德格尔把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乡音越来越淡的背后,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家园”的远去?正如你在书中所说,“乡音越淡乡愁却越浓,距离越远情感却越近。”
苏丹:方言在现代社会之前是普遍存在的,那时候地理的因素对人们的社会形态的塑造有很大作用。由于地理的变化和距离(这是一个空间问题,空间的大小还有空间的形态),对社会的塑造是很强大的,因此每个社会在发育的过程中,因为相互影响的微弱,导致它自己会发展出一些非常特别的形式。但自从有了喇叭、收音机以后,大家都在学普通话,尤其有了电视以后,口音也在变。这种变化虽然很微妙,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现在的方言其实正在淡出,世界变得简单,空间好像在消失。我们看到同样的东西,从电视频道到微信公众号,到抖音、快手这些东西,都在用类似的方式表达。但地域性还是有它的遗产在的,消失的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乡音跟乡愁有关系,乡音的消失是乡愁的重要组成部分。声音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思维形式。民歌的形成是和方言有关系的,它实际上是在方言的语调下,形成的一种唱腔、唱词。今天的书写,我们更多是在普通话的这种朗诵的(语调)引导下去写的,至少我是这么去做的,有呼吸感,有节奏控制,但如果还原到地方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如果)不一样之后,可能在现代性的阅读里也会产生一些障碍,其实是需要引起关注的。
我这两年非常爱听山西民歌,像河曲的、左权的民歌。我听民歌,有的时候唱词已经听不清楚了,但还是觉得那么美好。研究音乐人类学的学者们有这么一句话,说听民谣是不会听唱词的。唱词已经和曲调浑然一体,难舍难分。它就是好听、委婉、动人,它表达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你非要把歌词弄清楚的时候,你就丧失了对纯音乐形式的感受。
新京报:在写幼儿园时期的文章中,你说:“在幼儿园里被剥夺的首先就是时间的支配权:规定的时间入园,规定的时间离开,规定的时间里游戏,规定的时间里睡眠……”你也因此“爱上了逃跑”。这种从孩子时期就开始的对人的规训,你认为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宿命”。面对这一“宿命”你是怎样的心态?
苏丹:写这一段的时候,我对幼儿园非常反感。进去以后,每天被规定去学一些东西,而且我的反应慢,经常挨揍,还要定期睡觉,我不想睡觉的时候让我睡,所以每天就装睡。每一个个体的作息时间还是有差别的,但你都要接受这种规范,通过惩罚(让你)来适应。那时感觉非常难熬,每天像坐监一样,每一分钟对我来讲都是痛苦的,这也促成了我的逃跑。
我非常珍惜放风的时间,放风之后又被阿姨暴揍。幼儿园这个事物也是工业社会的一种产物,是奶妈的另外一种形式,互相帮助,就是说帮着你教育孩子。幼儿园我想可以追溯到欧洲最早的宗教场所,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演变过来的(我也没有经过调研)。到了工业社会它就普遍存在了,因为他们要让壮年人在工厂专注工作,所以造成了骨肉分离,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一种剥离。在这个强制的过程中,孩子第一次进幼儿园,没有快乐的。这是挺残酷的一个过程。有时我的确是有恻隐之心,我送我的孩子去幼儿园时就有这种感觉,看到他要哭的那一瞬间我会赶快跑,否则我会感到一种撕裂。这是我的一种潜在的记忆所造成的表现。

《慰藉之浴》油画,作者:宋永红。
5
“通过书写证明我和那个时代的关系”
新京报:书中也写到你的高考。高考每年都会成为关注话题。结合你个人的经验,你如何看待高考制度?
苏丹:中国的高考制度,尽管在人才的选拔上有一些不合理之处,但从社会角度看,我觉得高考制度是中国社会打乱既有社会规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给所有平民一个希望。高考是一个升迁的非常直接的途径,社会的公平性可能在高考制度上有所体现。我认为高考还是比较客观和公平的,但它可能不科学。我们过于迷信高考。我认识很多高考有辉煌战绩的人,比如高考状元,他一辈子沉湎在这种幸福里,因为他在中国社会中太重要了。人们迷信它,相信它的公正性,甚至很多机构会相信它的科学性,但现在科学性开始受到质疑。
我认为高考因为没有面试,其实对人的选择和判断是有误差的,但是没办法。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族群,只能采用这样一种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又没那么科学的方法。我现在也想不出更科学、更适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高考制度还是对的。一旦高考里出现不公正的情况,出现作弊,社会必须要下大力气问责,让作弊者付出代价,我觉得必须要做,因为这是中国社会公平的一个希望。
新京报:余世存老师在序言中说:“对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回忆是重要的,它是当下极为缺失的参照中重要的镜子之一,作者这本书就是明证。”关于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关系,你是怎么看的?
苏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在远去,正在变得模糊,而七八十年代又是特殊政治格局下的一个社会样板。七十年代是需要记忆和反省的。关于八十年代,我觉得书中描述了一个社会转型期的转变过程,它弥足珍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多样性和单一性之间的一种反差,看到个人命运由过去的被规定到出现变化的可能。
比如说我,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下来,一直到七十年代末这期间,在上山下乡这个制度没有被取缔之前,我已经被规定了未来是个农民,因为家里有俩孩子,老大一定是当工人,老二一定是插队。我也一直照这样一种模式去培养自己,能打能闹能折腾,结果后来突然取缔了上山下乡,开始高考了,我们突然可以有梦想去离开,到另外一个你很好奇的地方,比如去海边,去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这时候人生就开始丰富了。
新京报:回望故乡、回忆往事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说是对“逝去的时间”的追寻,就像普鲁斯特在漫长的回忆过程中确证了自我的“此在”,你对往事的追寻是不是也有对“自我此在”的确证目的?
苏丹:当然是有的。我觉得无论是潜意识也好,还是后来的自觉也好,我在寻求我的存在,在历史中的存在,在逝去的光阴中的存在。通过书写来证明我和那个时代的关系,确认生命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张进
编辑|张婷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