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夏天,刘子超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他在霍尔果斯眺望哈萨克斯坦一侧的天山。当时,刘子超对中亚的了解全都源自书本,他无法想象这些地名背后具体的样子。对于他来说,中亚是一张标满问号的地图。
这激起了刘子超对中亚的向往。2011年,刘子超第一次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他被塔什干的景象震惊了:中亚就像一个时间博物馆,当地的景象仿佛停留在二十年前;中亚群族的多样性也出乎他的意料。
这种震撼激发着刘子超的创作欲。在2016年之后,刘子超曾多次前往中亚,他几乎走遍了中亚所有能去的地方。2019年,刘子超从霍尔果斯入境回国,他回到启程的地方,使得他的中亚之行形成一个回环。当他回望身后的天山,充满问号的中亚地图也明晰了起来,他的人生也渐渐有了答案。
在刘子超漫游中亚的这段时间里,他所从事的媒体行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传统媒体不再是吃香的行业。在刘子超本科毕业刚进入媒体行业时,他经历过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那时整个报业集团一年能盈利四五个亿。2016年下滑的行业趋势使得许多记者选择转行。刘子超也选择了辞职。就像他在中亚看到的游牧民族一样,他开始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即成为自由职业者,用自己的方式旅行,日复一日的写作。

刘子超在《失落的卫星》里提到的地点。
刚开始“游牧”时的那段迷茫心态,和经历过媒体业从辉煌到暗淡的失落经历,让刘子超与中亚年轻人迷茫的心灵得到某种共鸣。在苏联解体后,过去的辉煌已不再,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在全球化的边缘和大国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刘子超的人生境遇,使他特别能体会这种迷茫的失重状态。在探索中亚的过程中,他也在探寻着自己。他尝试去发现中亚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故事来理解这片土地。这也使得他的《失落的卫星》,在气质上与以前的《午夜降临前抵达》和《沿着季风的方向》有所不同,精彩的人物刻画成了此书的重心,以至于有评论夸他为“中国的何伟”。
在《失落的卫星》里,刘子超写了许多被不同方式“困”在中亚的小人物。他们有“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有想渴望出国留学逃离这一切的中亚年轻人,有在中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还有在中亚的朝鲜人。中亚复杂的群族认同,特殊的地缘环境,以及处在被全球化遗忘的角落,使得这些心灵都共享着某种共同的生活状态。刘子超认为,好的旅行文学就是要呈现当地的人心。这本书还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以往异域经验大多是由西方人的视角书写——如今,我们也有了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的旅行文学,从自身的角度观察和反思这个世界。
采写 | 徐悦东

刘子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著有《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曾获“书店文学奖·年度旅行写作奖”。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和《漫长的告别》等。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被译成英文,获评“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作品。
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中亚
新京报:你曾说过,2011年的首次中亚之行给你带来很大震撼,为什么?2016年再去的时候,感觉变化大吗?
刘子超:2011年我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感觉苏联解体就像发生在昨天——街上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和城市的建筑风格,好像还停留在20年前。从一个不断发生巨变的国度,来到一个相对停滞的地方,看到很多似曾相识的东西,那种感觉非常震撼。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中亚人的长相特别丰富——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和鞑靼人的长相都有。我惊讶于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原先并没想到中亚的群族如此混杂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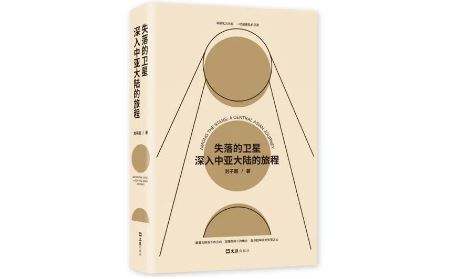
《失落的卫星》,刘子超著,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0年7月。
与中国相比,中亚这些年的变化并不算大,而且各国发展速度也不平均。哈萨克斯坦一直是现代化比较快的国家,其他几个国家相对缓慢。乌兹别克斯坦前两年换了总统,之后发展得也比较快。
中国在中亚有很多工程。乌兹别克斯坦提出过一个想法,他们想修建从乌兹别克斯坦出发经吉尔吉斯斯坦到喀什的铁路(中吉乌铁路)。这条铁路要贯穿天山山脉,施工难度很大。但是一旦通车,乌兹别克斯坦到中国的路程能缩短1400公里,一天之内能抵达太平洋,中亚离全球化又能靠近几步。
新京报:说到全球化,你在书里写到,在中亚,苏联的遗产正在无可奈何地被磨损,渐渐沦为废墟,这废墟并非全球化冲击的结果,而是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整个中亚。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受全球化冲击的影响更大。你能大概阐释一下这个观点吗?对比东南亚和南亚,你觉得这个现象特殊吗?
刘子超:中国和东南亚已经处于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但中亚并没有。它主要还是依赖出口矿产资源和棉花等原材料——这些资源也大都是可替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家雪佛兰工厂,这也许是中亚唯一一个与国际资本有关的加工型工厂。
在消费领域,直到这两年乌兹别克斯坦才开了第一家肯德基。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直到现在都没有这种全球化的连锁店。可能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中亚的市场太小了。而且,中亚的普遍消费能力也达不到开店的标准。因此,这些品牌都没有考虑打入当地市场。

浩罕小巷内的卖馕少年。刘子超摄

浩罕,穿着传统长袍的妇女。刘子超摄
新京报:这就像一处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后,按理说“世界是平的”,信息全球化应该也影响了中亚吧?他们的年轻一代在文化和信息上能够与世界接轨吗?
刘子超:中亚是多面的,跟世界接轨的年轻人也不少,但在文化上,中亚年轻人更多接触的是俄罗斯的流行文化。比如说,一些夜店歌曲在莫斯科火了之后,第二个月就会传到中亚。
新京报:中亚距离新疆很近,新疆会受中亚流行文化的影响吗?中国的流行文化对中亚有影响吗?像在东南亚很火的宫斗剧,他们会看吗?
刘子超:我去新疆时发现,乌鲁木齐夜店也会放一些俄罗斯的流行音乐,这可能是从中亚传过来的。
比如《Papito Chocolata》,这首歌是一名罗马尼亚歌手唱的西班牙语歌,莫名流行于整个中亚,后来在新疆也火起来了。在中国的音乐播放平台上,这首歌的评论大多是维语的评论。在中亚,中国的流行文化影响力比较弱,反而看韩剧的还多一些。中亚与我们在地理距离上很近,心理距离上还是比较远。

塔什干,卖馕的摊主。刘子超摄
媒体行业的下滑,导致对中亚人的迷茫感同身受
新京报:你的书名是《失落的卫星》,为何会起这个名字?你在书里写到,在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自己的轨道。而你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这种迷恋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为何会迷恋这种状态?
刘子超:其实最初想叫《爱的卫星》,来自Lou Reed的一首歌。写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经常冒出这首歌的曲调来。“失落的卫星”是从“爱的卫星”演变过来的。一方面是因为“卫星国”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是在哈萨克斯坦发射的。此外,卫星有一个特点——它的轨道总是被周围更大的行星所左右。
在历史上,中亚给人的感觉就很像一颗卫星。中亚一直处在各大文明体的中间地带。在唐朝时,中亚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国的中间地带。后来,中亚是沙俄和英国的中间地带。“9·11”事件之后,中亚是中、美、俄的中间地带。中亚的命运始终被身边的大国影响。

卡拉卡尔帕克少年。刘子超摄
苏联解体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我们最近常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人的身上就是一座山,那么苏联解体对中亚人来说本身就是一座山的崩塌。中亚各国开始探索自己的命运,在失重坠落中拼命想抓住什么,找到一个方向。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那位吉尔吉斯作家所说:“他们这代吉尔吉斯人,就是在废墟上寻找可以依靠的东西。”
写书的时候,我一方面觉得这种状态很有时代感和文学性,另一方面似乎它也契合了我当时的心境。在那几年,我所在的媒体行业也是分崩离析。记得我刚当记者那会儿,报业集团每年能盈利四五个亿,可到了2016年整个行业开始下滑,之后纷纷倒闭。很多同事离开了媒体行业,开始新的人生探索,我也辞职当了一名自由作家。当时那种迷茫跟中亚人面对苏联解体时的情形相似。我想写中亚的这种状态,因为我自己也处在这种状态中,感同身受。
新京报:中亚的年轻人会怀念苏联那段时光吗?
刘子超:年轻人很少怀念苏联,因为在他们出生时,苏联已经不存在了。经历过苏联时代的老人,还是挺怀念苏联的。因为在苏联,中亚属于边疆地区,会有很多政策倾斜。假如考试考得好,就能去莫斯科发展,还能被当成平等的公民对待。现在,这些中亚人再去俄罗斯打工,只能算“二等公民”了。
现在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学英语的,有学中文的,有的想去美国,有的想来中国,都不行的话再看能不能去俄罗斯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若还是不行,那就只能留在中亚,看看能不能进政府单位。这是很多人的人生选择的顺序。

游牧天山的吉尔吉斯人。刘子超摄
“困住”的状态是一种被迫滞留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了很多在失落的卫星里被“困住”的人物,比如说那个困守在咸海的“咸海王”,滞留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罗斯人,还有那个被困在杜尚别的男孩“幸运”。除了这两个明显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物也给读者呈现出一种生活、地域和政治“困住”的感觉。这是你在中亚观察到的年轻人的普遍生活状态吗?
刘子超:“困住”是被迫滞留在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状态里,又没有办法去改变,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生活在伊塞克湖地区的俄罗斯人,人数本来就少,也不会说吉尔吉斯语或哈萨克语。他们看不起当地人,觉得当地人粗鲁、没文化、只会喝酒。可当地人也同样看不起他们。在苏联时代,可能还有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都在“去俄化”。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把书写文字也改成了拉丁字母。这些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想离开,但又能去哪儿呢?

伊塞克湖,军事疗养院食堂。刘子超摄
真正的俄罗斯人是看不起这些在中亚的俄罗斯族的。以他们的教育程度,去俄罗斯工作也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做做服务员这种比较辛苦的职业。他们不喜欢中亚的环境,但是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给我一种被困住的感觉。像“幸运”这样的男孩,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学汉语,想来中国留学。现在,他已经在中国留学了。他代表了那些想走出去的中亚年轻人。
“咸海王”是在咸海工作的中国人。中国人做生意很能吃苦,去这种艰苦地方的中国人还有很多。除了中亚,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到处都有这样辛劳工作的中国人。“咸海王”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特殊,他只是觉得,生活把他带到那里。他一开始在新疆,后来就顺理成章地被派到咸海。这是他们的职业路径。要搜集那种虫卵,只能在盐度比较高的湖里,而这些湖大都位于比较偏远的地方。
新京报:这很像是一个隐喻,他们来到一片文化不同的异域,很容易产生孤独感。
刘子超:他让我想到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之心》。在康拉德的时代,很多英国人在异文化的环境里工作。现在,这个开拓的角色变成了中国人。

咸海,采集虫卵的工人。刘子超摄
新京报:你在书里有个观察,说在哈萨克斯坦,年轻一代相较于成长于苏联的长辈们反而更加保守和传统。这个现象普遍存在吗?据你的观察,这是为什么呢?
刘子超:苏联解体后的信仰真空,导致中亚国家开始重新拥抱伊斯兰教。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在苏联时代成长,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到年轻一代,政府在国家层面上推崇伊斯兰教,建造清真寺。土耳其和沙特也会给他们捐款修缮清真寺,派遣宗教老师。所以,很多中亚年轻人反而比他们的父辈更虔诚和保守。
当然,不是全部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我刚刚说到那些想出国的年轻人就不是这类人。想出国的年轻人相对而言处于中产阶层,而更保守的年轻人一般生活在相对偏远的小城市和农村里。

布哈拉,刺绣的女人。刘子超摄
中亚的群族冲突与被建构出来的族群认同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中亚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你在书里也很关注群族认同问题。比如说,你提到在哈萨克斯坦的朝鲜人,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的帕米尔人,还有各个国家的民族英雄和真实历史。你如何看待他们的民族建构问题?你为何会特别关注中亚边缘群族的认同?
刘子超:首先,这些民族的名称有些是在1920年代才出现的。当时,苏联将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套在中亚这片还处于前现代的土地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24年以前,苏联人把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称为吉尔吉斯人。之后,他们决定继续细分,才把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称为哈萨克人,把山区的游牧民族称为吉尔吉斯人。
在撒马尔罕、布哈拉这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信仰杂居之地。人们一般只会用突厥人、波斯人来互相区分,或者用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来互相区分,要不就是用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这样的地理概念来区分。不会有人说,“我是乌兹别克人”,“我是塔吉克人”。现在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近一百年来才慢慢被建构起来的。

希瓦,集市里的小贩。刘子超摄
苏联解体后,每个国家都要加强自己的民族认同。这就要从建构自己的民族神话、民族英雄和民族历史开始,所谓建国“三件套”。这就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和冲突,甚至与史实不符的地方。
现在这些国家之间,不时爆发族群间的摩擦冲突,边境线互相缠绕,像一笔糊涂账,还有飞地散落其间。这一点,当你在中亚旅行时,会感觉特别明显。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就发现这是同被建构出来的族群认同和边境线的划分有关的。
新京报:你觉得中亚之行,对你理解历史的潮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子超:这本书写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像失落的卫星一样的寻觅状态。未来这个地区会是什么样子,我在书里有过观察和思考。我觉得中国在中亚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会改变这里的引力。如今,这个进程只是刚刚开始。

瓦罕山谷,兰加尔的瓦罕女孩。刘子超摄
旅行作为一种方法,要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
新京报:从《午夜降临前抵达》到《沿着季风的方向》,再到《失落的卫星》,有评论说你的《失落的卫星》摆脱了之前的游记风,对这个文体的把控更加驾轻就熟。我觉得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对人物的叙述描写部分会更多、更深入。你怎么看待这本书和此前作品的差异?
刘子超:在这本书里,我会有意识地去找人。许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实际上背后付出了艰辛。就像你在溪水里钓鱼,鱼咬钩是随机的,但也跟你在哪里下杆有关系。
我渐渐把旅行变成了一种方法,让人物浮现出来,旅行反而退到后面。我想写的是这些人的生存经验,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要了解历史,你可以在家里看书,而人心只有去了那里才能捕捉。如果旅行文学不能与人相遇,那就是失败的。在前两本书中,会有更多即兴的成分,随机去发现和捕捉。这本书虽然也有很多即兴,但有时为了找到人,也真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布哈拉,老城内的居民。刘子超摄
新京报:有的旅行文学更专注于过去,有的更关注现实;有的更关注风景,有的更关注人物。在《失落的卫星》里,你似乎更关注当下的人物,一窥当地的社会风土。这使得这本书有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色彩,也让这本书更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而你以前的书的“私人性”会多一点。你怎么看待旅行文学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问题?
刘子超:这要看作家的风格。我不能说“私人性”不好而“公共性”好。对我来说,在这本书里面,“公共性”的部分比较重要,是因为这些人的故事太有历史感和现实感了。如果不突出“公共性”,这些人物就被浪费了。
新京报:以前有评论说你会“掉书袋”,知识的堆砌较多。但是,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掉书袋”(比如有关那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学)的地方比以前少了。这是因为大家对中亚的知识相对欧洲等地方较少吗?还是你改变了策略,更关注当地日常生活的缝隙和边缘族群的生活?
刘子超:以前写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炫耀的成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变得更平和了。我看了很多书和资料,它们帮助我去理解中亚,但我不想用一种显眼的方式把它们抖落出来。罗新老师看完这本书后,说我应该多加点注释。因为他能看出来,有些地方来我引了哪些材料,用了哪些典故。
我后来没有加这些注释。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太学术了,容易破坏行文的节奏。另一方面,我认为看不出来并不影响大家的理解。如果有的读者阅读量比较大,在书里发现了什么,会心一笑就可以了。我在书后列的书单也不长,选的都是一些好读的书,像巴托尔德写的非常晦涩的书就没被列进去。

阿拉木图,绿色大巴扎。刘子超摄
要找到有故事的人,每天感官都要处在打开状态
新京报:这本书里前半部分的叙述较多,而后半部分的资料性较多,这是你刻意安排的吗?
刘子超:其实很多时候,我要根据手中的材料来决定怎么写。在前半部分,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时,我遇到很多有趣的人,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本身也没什么好写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遗产就比较丰富了,可以讲述的也更多,因此写乌兹别克斯坦时就会偏重一点历史。
新京报:除了房东、向导之外,你是怎么找到这些有故事的人的?
刘子超:首先,内心要有强烈的愿望。在去中亚之前我就决定,找人是我最重要的工作。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人上。我是一个人去旅行的,感官每天都处在打开状态,就像一个放大镜或者接收器,带着这种敏感度去观察身边的人,看哪些人可能有意思。
其次,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去到中亚,中亚人也会对我有好奇,特别是当你出现在景点之外的地方时。你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住在北京的老小区,这小区从来没有过外国人,有天突然来了个外国人在里面晃荡,你作为居民是不是也会好奇?这时发生交谈的几率是很大的。

苦盏,锡尔河畔。刘子超摄
当然,我也要做判断,找到能和我做有效交流的人。比如,服务员为我端来一杯咖啡,我们会寒暄一下。从这个简单的交流中,我会做出大致判断。我可能会留下她的联系方式,以便日后约出来再聊。我也会用当地的社交软件来找人。比如在杜尚别,我就用“陪你转转”这个app找到了三个人,他们都挺有意思的,但我最后只写了其中一个人。
在这本书里,我大概只写了十分之一我接触过的人。因为很多人在聊过之后,我发现很难进行有效交流。我要找的也并不仅仅是有故事的人,这个人的故事还要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一些侧面。这也要看运气。
与当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搜索不出来的
新京报:在各种旅行资讯、历史资料等都高度发达,交通也十分便利的时代,你觉得旅行文学给读者所带来的独特性是什么?
刘子超:我们现在去哪里都特别容易,资讯也变得发达。但是实际上,我们对那些地方的认知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在古代,旅行比较困难,去一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年准备。玄奘去印度是发了誓的,因为很可能走不到,还把命搭进去。所以,古人虽然没有如今的资讯,但他们的求知欲比现代人更强烈。
过去的旅行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写的事实,是考察记录,是文献资料,是情报。现在的旅行文学就不是这样,因为资讯是很容易在网上搜到的,搜不到的是你与当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一个地方的人心。

通往咸海的道路。刘子超摄
新京报:你说过去只有西方作家才有权利写别的地方的经验,他们往往带着某种西方视角来书写,你会带着中国视角去写其他地方的经验吗?根据你的理解,这种中国视角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或者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视角?
刘子超:我肯定会带着中国的视角,这就是我去旅行和写作的目的。如果说中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那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身体力行地对世界进行观察和反思吧?没有这些观察和反思形成的厚重积累,怎么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呢?
对我来说,中国视角肯定不是民粹的视角、义和团的视角,而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接受教育(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底,也有西方文化的浸润。我希望它是开放的、宽容的、人道的、有共情的,就像历史上经过几百年的融合,中国文化终于将佛教文化内化后的那种焕然一新。
做“当代游牧民族”,要学会“断舍离”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自己是当代的“游牧民族”,请问该怎么理解这个意象?
刘子超:我觉得有固定职业的人就像农耕民族,朝九晚五,旱涝保收,比较稳定,但不自由。而我这几年的生活方式更像是游牧民族,自由但没有保障,自食其力,冷暖自知。为了靠写作活下来,我做过“断舍离”,放弃了很多东西。游牧民族也是如此,他们总在移动,因此不可能带着很多东西,只能带那些最重要的上路。他们的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有方向的,从夏牧场到冬牧场,我的旅行也渐渐变得有目的性。与古代游牧民族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个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能与世界保持连接,所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当代游牧民族”。

荒凉的咸海边。刘子超摄
新京报:在你进入“失重的状态”之前,就已经规划好要写旅行文学了吗?
刘子超:2016年,我决定当自由作家,之前只写过一本书。那本书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并不是有意规划的。但到这本《失落的卫星》时,我就开始比较有自觉了。一开始就规划好要写这本书,然后,带着写书的想法去中亚旅行。
新京报:有评论说你是“中国的何伟”,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刘子超:我觉得大家这么说,肯定是对我的赞扬,但最好别让何伟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代记者或记者出身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何伟的影响。何伟的共情能力、观察力令人钦佩。他写一个地方时,总是写当地的普通人,细致入微地观察他们。这一点我认同而且欣赏。
这个称号可能作为宣传的噱头蛮好的,但我自己不会这么说。成为“中国的何伟”很好,但我也想成为中国的奈保尔、海明威或者布鲁斯·查特文。
新京报:你做记者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子超:我当了将近10年记者,有很多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纯写小说出身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许多年,关注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来打量时代,这些方法论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海明威说,想当作家的话,当几年记者挺好的。我就是听了这话后才当记者的。

帕米尔高原,布伦库里。刘子超摄
新京报:你有想过用其他媒介来呈现你的旅行吗,比如拍vlog、纪录片或旅行节目之类?
刘子超:旅行文学是“单打独斗”的艺术,纪录片则需要一个团队。我对哪种方式并没有执念,只要是精致的表达,我都喜欢。比如做西蒙·里夫那样的节目,我也挺有兴趣的。
作者 | 徐悦东
编辑 | 徐伟 罗东
校对 | 付春












